终结与先行 ——《东方》在当代军旅文学中的位置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韩瑞亭 2019年02月25日0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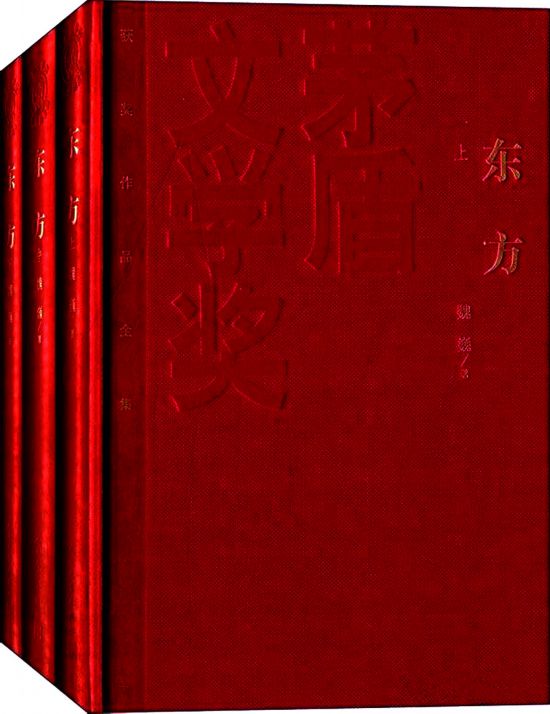
长篇小说《东方》
魏巍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军旅生活的作家。他于抗战烽火初燃之时投身军旅,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斗,也在各个时期留下过文学的足迹。他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写下的长诗《黎明风景》,真实地抒写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战奋斗的生活场景与情怀。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奔赴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采访,写下不少战地通讯、特写和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成了为人民战士的崇高荣耀命名的轰动一时的佳作。《东方》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他在“文革”时代顶着压力,冒着风险,默默地进行艰辛的艺术求索。小说终于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出版,成为进入新时期之前军旅文学复苏的最初标识。
当我从《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选载的《东方》前10章时,立即被吸引住了,仿佛从荒芜已久的田园中蓦然见到一簇油绿的青苗、绚丽的春花。小说前10章中对于冀中平原上民俗风情的描写,如诗如画,声情并茂,似乎很久没有读到带着如此清冽的秋日露珠、泥土气息和青草香味的作品了。
《东方》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好像是从封冻的冷窟挣脱出来的文学新发的芽苗,让人们察觉到文学复苏的先兆,也为沉寂凋零已久的军旅文学带来振兴的最初希望。
老作家孙犁曾在1978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创新的准备》一文。这位复出后的作家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息,体察到被禁锢多年的文学亟待破茧而出的现实需求,他在文中呼唤文学出现创新局面,表达其除旧布新、振兴中国文学的心声。魏巍在同年出版的《东方》,仿佛以探索性实践呼应着孙犁的主张。这两位相识于晋察冀边区的友人,灵犀相通,同气相求,都在表达着冲破旧日的阴霾、迎接文学的春天到来的期盼。而1978年底正式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对这些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急切改变文运、国运的期盼与现实需求的郑重回应。
《东方》是一部全景式地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不同于此前已经发表和出版过的一些长篇小说和纪实作品,多是从局部或某一阶段的战事来展现这场颇具规模的战争。它力图对这场历时三载、艰苦繁难的战争进行全面而有中心的书写,不仅表现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完整过程,也对重大的战役和战斗、战场局势的演变、战略方针的转移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显现。它以邓军、周朴所带领的团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作战部队为中心,通过这个团入朝之后频繁、复杂、艰险的战斗活动,将朝鲜战场上进行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和战事,有机地组织和概括于邓军、周朴团这个中心画面上来,既刻画出了这场战争的轮廓和发展轨迹,也揭示出这场战争的历史特点、正义性质和推动它走向胜利的强劲动力。小说在郭祥、乔大夯、王大发、花正芳、刘大顺等志愿军战士形象的刻画中,着力挖掘如团政委周朴所说的那种“极其深厚的东西”,即非凡的英勇气概与历史主动精神。它是从这些忠诚于祖国的人民战士对于自己庄严使命的理解中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使得他们敢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主体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进行殊死较量,并战而胜之。小说在宏大格局的营造,广阔而有纵深的战争生活描绘,志愿军战士群体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使它对于这场战争的艺术表现,具有一定程度的史诗规模。
《东方》同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保卫延安》《红日》等军旅文学名著相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方式上已有不少拓展和突进。其一,它对于战争和军人生活的描写,不再拘守于战场,而延伸到战场以外的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它创造了志愿军战士郭祥、杨雪的家乡凤凰堡这个特定环境,作为当时国内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将战争时期的国内生活也化为作品的有机构成部分。小说把前线与后方穿插交错起来描写的结构布局,无疑扩展了对这场战争的表现幅度,是由单纯从军事斗争角度表现战争,转换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角度表现战争的新尝试。这种布局开阔的表现方式,有助于深度展示作品的艺术主题。
其二,《东方》在描绘激烈的对敌搏战的严酷环境中,作为一条重要支线,还描写了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军中人物的负面形象。上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军旅文学,还很少有作品直接触及我军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构成尖锐冲突的军队内部矛盾,也鲜见军中人物的负面形象。对于这一类在实际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现象,似乎有一些不能触碰的不成文的禁忌。《东方》的作者则以探索性实践,冲破了此类思想束缚。小说塑造了陆希荣这样一个军中负面人物形象,展现出陆希荣的极端个人主义与人民军队应当持守的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如何构成尖锐的冲突。由于思想意识的霉变,陆希荣从一个军政兼优的营长,蜕变成怯战畏敌、临阵脱逃,使部队付出惨痛代价的罪人,最终成了以自伤的卑劣行为脱队的逃兵。在一个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揭露如此严重的内部矛盾,作品的写法足够大胆,却并未损伤这支英雄部队的整体形象。
其三,《东方》对于郭祥、杨雪的爱情描写,亦有特点和新意,在整个作品中占有相当分量,几乎贯穿于作品的始终。郭祥与杨雪的爱情纠结同战争的发展进程相联系,同尖锐的军队内部矛盾相结合,同人物的生活命运相融汇,于战争生活的错综变幻之中,呈现人物关系的悲欢离合。郭祥与杨雪由青梅竹马的友伴到参军后的战友,本应有建立爱情关系的感情基础,但陆希荣处心积虑的追求,杨雪为表象所蒙蔽的误选,造成郭、杨间爱情关系的波折。在陆希荣卑劣面目暴露和杨雪牺牲后,小说着力描写郭祥在失去杨雪后的内心痛苦,渲染郭祥对杨雪怀恋思念的深情,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有增无减,绵绵不绝。郭祥与杨雪的爱情关系近乎悲剧式的结局,反倒检测着人物感情的质地,呈显出英雄战士郭祥对于爱情的始终不渝、纯真如金。50年代以来的军旅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涉及人民战士爱情描写的并不多,比较出色的也鲜见。而《东方》在这方面的探索,显然有了不小的跨越。
《东方》在诸多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性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于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某些固有观念和写作范式的摆脱和更替,也有对“文革”中畅行的某些极左思潮与僵化思维束缚的冲击。在阴霾四合的年代里坚持此种艺术求索,实属不易。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东方》和其他几部作品大多创作于“文革”期间或“文革”结束之初,大多属于从不同题材领域、不同思想和艺术方位进行突破性探索的实践成果。它们是新时期文学开端之际的最初收获,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发挥了某种引领与启迪之效。
魏巍在开始写作《东方》之时,本有描写彭德怀司令员的计划,因为要全方位地表现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面貌,不能不写到前线的最高指挥者彭总的活动。由于彼时环境不允许,作家原有的构思无法形诸笔墨,只得留下难以避免的缺憾。他在小说获奖之后,怀着补漏救缺的心思,着手书写彭总在前线的相关章节,于1984年初春发表了以《彭总》为题的新增补章节,至1986年全书再版时正式补入。
这些新增补的章节,均以彭总为中心展开对战争全局的开阔描写,表现彭总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上的主要活动。这些章节对于发生在亚洲东方的这场国际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之历史面貌的展现,又超越了原来由一个团队、一个村庄的角度来体认这场战争的有限视野,在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程度上揭示这场战争的时代特征与非凡意义。这些章节对于彭总等高层指挥员运筹帷幄的描写,又是从前线指挥部的视界高屋建瓴地画出战争进程的真实轨迹,使指挥中枢与战斗部队的活动连接、沟通起来,形成统一而有中心的战争全景的艺术描绘。这些章节对于毛主席、彭总等领袖和统帅人物的形象创造,则是在表现这类难度较大的艺术观照对象方面,由片段描写或侧面描写向比较充分的正面描写发展的一种尝试。作家在这些章节里,紧紧把握住彭总这一特定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将统帅者的智慧刚毅和老战士的淳厚质朴融为一体,塑造了一个较为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作家为完成新增补章节所作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预想,也为这个力求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宏阔史实的艺术建构加盖了一个结实的屋顶。
当代军旅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10多年间,曾有过发展和兴盛的年份,产生过一批长篇小说佳作,它们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作出过显著贡献,占有相当的分量。但是它们同整个新中国文学一样,被多年“文革”所阻断。《东方》是在荒圮的废园里奋然耕耘的一道犁铧的印记。它自然接续了“文革”前10多年军旅文学的传统,却也在尽力排除附着其上的某些积垢与流弊,寻求与时代行进相对应的新质。《东方》所描写的依然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战争和军旅生活,不过它在观察与表现生活的视界和范式方面,对于50年代的军旅文学而言,已是一种延伸、突进和翻新。《东方》的探索性实践,对于“文革”前的当代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似乎是一个终结。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而言,则是一次探路者的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