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孙曙 2019年07月29日07:33
石头金属等纪念碑的材质相异,但都“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的某一事件,同时也是对这一事件后果的巩固和合法化──即国家形态意义上的中央权力的实现和实施”(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纪念碑是权力与秩序的昭示宣谕,成为国家、种族、文明、政权、政党等总体性的象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虽有不同提法,但为革命事业、为人民、为英雄、为时代等树碑立传的要求一直是其题中之义,规训着现实主义建造文字的纪念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就是为农民运动、土改、解放战争、合作化运动等树立的纪念碑。“纪念碑性”本指纪念碑的纪念状态和内涵,本文中指现实主义不断演变的历史内涵和功能。由于文学必须经由作家主体创造,文学的独立性和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形成复杂的缠绕,这就使得现实主义的纪念碑模式虽然不变,但其“纪念碑性”一直在发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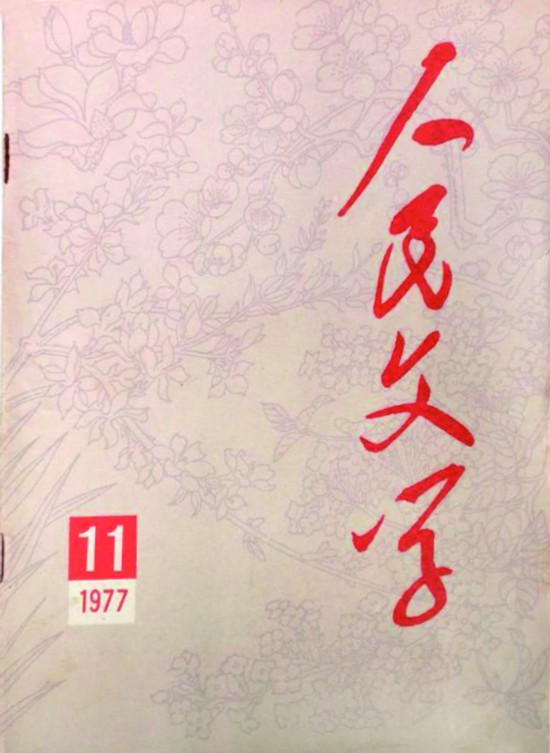
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
1958年在《读书》发表《谈〈第四十一〉》,是刘心武创作的起点。但真正“人尽皆知、朝野轰动”,还是因为1977年其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这一已载入史册的标志性文本被称作“新时期小说的第一声呐喊”,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坐标点。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冯牧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给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范例可以起到开辟道路、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冯牧《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
冲破禁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者、奠基者、领跑者,这是刘心武刻进历史的身影。在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学“否定文革”的共识高度一致的背景下,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文本与伤痕文学的文学文本等协同呼应甚至文体互相渗透一并汇成了“新时期话语”,与正在建构的新的政治体制与文学体制互为表里、协同共进,夯筑了新时期的合法性与总体性。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等作品大都以新旧政治观念与思想观念的矛盾结构情节,解决问题依靠政治方法和政治权力,充满强烈的政治抒情与政治呼告,由是被推为现实主义的标杆与范例。这些作品与现实政治合拍的强烈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表征。刘心武后来称之为自以为真理在握说教式的“真理叙述”(傅小平《刘心武:我写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命历程有关》),这正是那时现实主义的“纪念碑性”。
此后,刘心武又相继创作了《如意》《木变石戒指》《立体交叉桥》等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政治诉求与政策图解,而试图将现实主义的“纪念碑性”转向人性人情、转向底层大众,这一阶段积淀的最高成就是长篇小说《钟鼓楼》。《钟鼓楼》以一天为经,以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为纬,以一场婚礼为主轴,万花筒般转开四合院中9户人家的家世浮沉,编织出相关几十个人物的遭遇,这些人物的活动连接起历史现实、城市乡村、首都外省和机关工厂街区,立体编织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空间。他们上辈是满清贵族、喇嘛、农民、乞丐、民间艺人、妓女等,他们的职业是售货员、司机、厨师、绿化工人、修鞋匠等,虽然也有高干、翻译、编辑、演员、医生等中高层人士,那也不过是为了映衬出底层社会的深广复杂。《钟鼓楼》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的民族志叙事作品之一,接续《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垦殖北京文化的京味小说传统,历史化地塑形城市及城市空间,追溯现代城市的初始印记和混合空间的变迁,又是都市志化的城市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立体交叉桥》发表后,有批评家劝导刘心武,“作家可以刻画小人物,但作品里不能全是小人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应当塑造出先进人物把读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导”(《神会立交桥》)。很明显刘心武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教令。《钟鼓楼》中他只在一个有改革精神的局级干部张奇林身上体现了当时的政治主题改革,整部小说基本还是小人物的小日子,写他们想把自己日子过好的努力,写他们微弱的善念与小小的恶,薛大娘偏心小儿子在大媳妇面前摆婆婆架子、澹台明珠与师姐争戏、海老太太总是瞎编自己家的传奇、新媳妇潘秀娅打算盘一样算计出自己的婚姻、詹丽颖热心却无礼、慕英嫁给残疾英雄才从僻远小镇跳到京城又抛弃了英雄、大混子卢宝桑总犯浑、小厨师路喜纯善软弱因父母出身低贱而自卑、梁福民两口子省到牙缝里又不能吃一点亏……芸芸众生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日常生活,让现实主义也丰沛起来。《钟鼓楼》是一部北京市民生活世态与底层社会的纪念碑,很明显,这部作品中的“纪念碑性”已从政治表征转为社会表征与文化表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授予《钟鼓楼》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现实主义的开放。
《钟鼓楼》前后的刘心武一直在文学体制的中心,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心。茅盾、冰心、巴金、蒋孔阳、冯牧等前辈作家理论家都对他充满期许和信任,王蒙、刘再复等崛起的文学力量也对他极其友好。他曾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又任主编。他的创作也是顺风顺水拓展精进,《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私人照相簿》等纪实小说与个体历史随笔相继引起轰动,引领风气。刘心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创造力依然旺盛,相继创作了《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树与林同在》等四部长篇和《小墩子》等众多中短篇小说和大量随笔,其中最优秀的当属《四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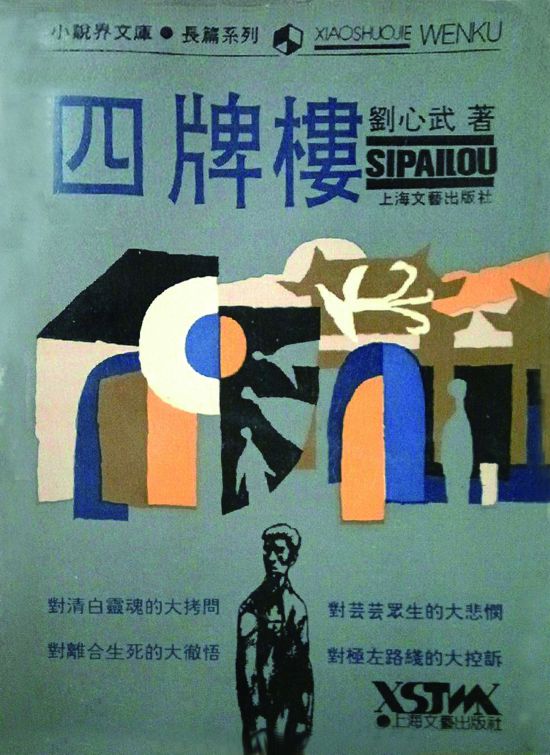
《四牌楼》是刘心武创作中艺术最为纯熟、人性探揭最为深幽、历史感最为厚重的作品,它动用了作家最为隐秘真切刻骨铭心的家族生活资源。小说以作家蒋盈海及其四位哥哥姐姐的人生起落情感流变为主线,穿插进蒋氏家族及其亲好在20世纪百年中国的离散荣衰生死悲欢,在时代与生命个体的相互搏击中叩问人性之实、探求存在之真。蒋家四代人,蒋盈海的爷爷是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北伐,他的七舅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姑父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亲美派将军,后起义投诚;姑母早年随父参加大革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父亲一直在海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海关总署,其后历次运动中蒋家倾覆离散枝叶飘零,为了生活奔走在东西南北,从弄潮时代到飘萍时代,蒋家代有英才却蹭蹬磨灭。《四牌楼》承继了家族小说的传统,既有《红楼梦》的繁华散尽悲雾萦梦,又有《家》《财主的儿女们》等现代小说的国族书写,更有时代惊涛中潮头翻船、瓜果飘零的离散叙事(台湾文学中的离散叙事已是文学史常识概念,大陆文学中叙述时代恶浪、家庭覆巢、亲族分离、背井离乡的作品也可用离散叙事的框架分析)。《四牌楼》的题词之一是《红楼梦》中的“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点明的不但是小说的师承,还有其为女性立传的动机。小说从蒋盈海初三时就有的一个愿望开篇,那愿望就是写一本小说《阿姐》。小说结尾,蒋盈海追溯这部书的缘起,越过写《阿姐》的初愿,他突然想到少年时四牌楼下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的一帧女子照片,他曾多日痴痴凝视。这首尾的呼应,确立了《四牌楼》的叙事更偏重于女性人物。小说的主体内容是蒋盈海的姐姐蒋盈波和她的三位高中同学崩龙珍、鞠琴、田月明命运波折的青春、婚恋、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关联的众多女性的经历,在蒋盈波四位同学之外还刻画了姑妈、八孃、四孃、童二孃、欧妈、香姑、曹叔原配、爷爷最后的恋人女赤卫队长等上辈女性,以及涧表妹、邢静、邢玉、甘福云等平辈,还有蒋唱、飒飒、常嫦等晚辈,揭示大时代碾压下女性的苦难和政权、男权下女性的压抑、牺牲与扭曲,而最小一辈的飒飒、常嫦也显示了新时代女性独立的意志和力量,预示了女性的希望与未来。《四牌楼》是少有的20世纪中国女性画廊和女性生存的心史,这部小说是唱给生命、家族,唱给女性,唱给20世纪的一曲长恨歌。这部小说的成功不单在于众多人物的生动塑造和故事的跌宕起伏,还有像照相一样精微逼真的描写、谙熟的人物群雕、各种叙事人称的自由转换和强烈的抒情风格。刘心武自己也认为《四牌楼》是他最好的作品,“我最满意的是《四牌楼》”(《〈刘心武文粹〉总序》)。
“除非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灾变,北京的钟鼓楼将成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青瓦。钟鼓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这是《钟鼓楼》的结尾。在《钟鼓楼》中,现实主义的总体性还在,钟鼓楼就是一个总体性的象征,象征着神圣的时间,确立一种永恒的秩序。作者把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活动、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统领进钟鼓楼的象征。而《四牌楼》中,四牌楼早已拆毁,成为曾经实有的虚无。
进入21世纪,刘心武赶上了文化传媒变革和大众文学兴起的机遇,在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再次走红,他的创作力不减,长篇小说《飘窗》《无尽的长廊》等相继出版,他依然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