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珉:我们为什么爱读巴尔扎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艾珉 2020年01月20日07:50
2019年是法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诞辰220周年,2020年则是他逝世170周年。这位罕见的天才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作的90多部小说,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世代相传,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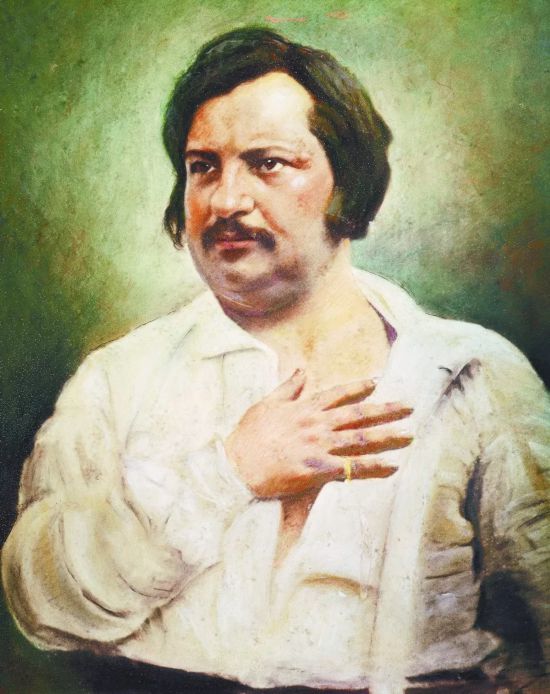
巴尔扎克
以切身经历作为小说素材
巴尔扎克在世的半个世纪,正值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轨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及其百日皇朝、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七月王朝,直至1848年“二月革命”资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既充满罪恶又充满活力,既腐败而又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各阶层的兴衰沉浮、沧海桑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触目惊心。正是这个处于巨变中的时代,吸引了巴尔扎克去研究它、认识它,并萌发了充当法国社会书记的愿望。
他出生于法国中西部城市图尔一个市民家庭,父亲是从农民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当过图尔市副市长和巴黎的粮食局长;母亲是一位呢绒商的女儿。可以说,他的家庭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巴尔扎克最熟悉的就是市民阶层,他之所以对金钱和遗产问题体会那么深,就因为这两个问题永远是市民圈子的主要话题。
少年巴尔扎克思维能力超常,在精神领域相当早熟,经常沉溺于一些玄妙抽象的哲理思考。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他兴趣广泛,一面在法学院学习,一面在文学院听课,同时还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就知识结构而言,他完全可以和恩格斯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媲美。
大学期间,父母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通过几年的实践,他不仅熟知了民事诉讼程序,还见证了社会的不公和司法的黑幕,为其未来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巴尔扎克的一生也像是一出悲壮而辛酸的“喜剧”。正如波德莱尔所说,他是《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最富有诗意的一个”。他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挟带着多次神话般的破产。他先后借钱开办印刷厂和铸字厂,甚至去撒丁岛想开发银矿,每次都以为将财源滚滚,结果却总是负债累累。他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无数发财的手段,自己反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只能靠一支笔来偿还。他时刻受高利贷者和出版商的追逼,永远在为到期的期票发愁,房屋、家具不止一次被查封、拍卖,还经常逃到乡下去躲债……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统治、物质的迫害有过他那样深切的、痛苦的感受,但在生活体验上他比任何人都富有。他正像自己所描写的一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给他提供了无穷尽的创作题材,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以小说形式谱写当代历史
巴尔扎克步入文坛的时候,适逢法国浪漫派向古典主义公开宣战,浪漫主义运动进入高潮。巴尔扎克却游离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独树一帜,决心用笔来完成拿破仑未能用宝剑完成的伟业。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他用人物重复出现的手法,将90余部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具有了文献价值。这种把文学作品系列化、整体化,以反映社会全貌的做法,是巴尔扎克的首创。
在巴尔扎克决定以小说形式来谱写当代历史的时候,便已经立足于对整个社会的研究。与其说他是作为小说家来记述历史,不如说他是以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写小说。恰如恩格斯所说,巴尔扎克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逐年描绘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他描写资产阶级如何发家(《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贵族如何破产(《古物陈列室》),资产者的势力如何深入到每一个城镇、乡村,在一切领域和贵族社会展开政治上、经济上的较量(《老姑娘》《比哀兰特》《图尔的本堂神甫》),贵族的庄园经济如何在资产阶级的进逼下土崩瓦解(《农民》);他揭露资产阶级政客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没收充公的贵族产业变成自己的私产,如何耍弄权术,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使自己的权势节节上升(《一桩神秘案件》),指出银行家、杂货商确实当上了贵族院议员(《邦斯舅舅》),贵族有时却沦落到社会底层(《浪荡王孙》);他记叙巴黎商业从个体商贩、小业主到批发商的历史进程及商业银行、股份公司、证券交易的出现,披露心狠手辣的银行家如何用倒账清理的手段掠夺千家万户的财产(《纽沁根银行》),敦厚的老派商人又如何在金融投机家的算计下被逼破产(《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他考察资产阶级的得势如何导致整个社会风俗的改变,金钱如何成为“无人知晓的国王”、人们“命运的主宰”(《高布赛克》),文学艺术及一切精神产品如何沦为商品,青年一代在拜金主义新时尚的冲击下又面临何等严峻的人生选择(《幻灭》《高老头》);他列举金银珠宝下面隐藏的无数罪恶(《红房子旅馆》《禁治产》《夏倍上校》),刻画人的贪欲会使遗产之争达到何等穷凶极恶的地步(《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邦斯舅舅》)……
作为风俗史家,巴尔扎克和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巴尔扎克关注的则是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艺术的首要贡献。他善于选择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和语言来突出人物的身份与个性,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强化该典型的心理特征。鲍赛昂夫人出身名门,举手投足都有大家风范,即使满心凄苦地向上流社会告别,也能面带微笑,安详从容。伏脱冷闯荡江湖,一言一动都透着绿林气派,《高老头》中被捕一场,写得有声有色,从暴怒到冷静,“仿佛一口锅炉贮满了足以翻江倒海的水汽,一眨眼之间被一滴冷水化得无影无踪”,把这个苦役犯的精明干练、足智多谋,刻画得超群绝伦。
巴尔扎克从不脸谱化地处理人物形象,也从不按一个模式描写同类人物。商人、律师、公证人也好,医生、公务员、艺术家也好,这一个都不同于那一个,连吝啬鬼都是各式各样的:葛朗台的聚财手段和高布赛克的不尽相同,里谷的吝啬和葛朗台的也大异其趣。葛朗台把一切开支看成浪费,尽管是地方上的首富,过日子却和当地的庄稼人一样,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烂果子,连女仆拿侬去店里买一根白烛都会成为当地的新闻;里谷的悭吝却只对付别人,自己则有一套独特的讲究与享受。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机灵善变、青云直上的典型,作者却不是一开始就让他以老奸巨猾的面目出现,而是让他在《高老头》中怀着外省青年的几分童心登场,在巴黎社会中逐步完成他的蜕变。这样的构思,不仅符合生活逻辑,也体现了作家的艺术匠心。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颤抖;中古的人物像玩具铅兵般倒伏在地”。
巴尔扎克在当代毫不过时
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巴尔扎克在法国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就像欧洲古典画派的大师们令其身后的画家感到“绝望”一样,巴尔扎克也让小说家们苦恼,他们不得不设法另辟蹊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派公开宣称要与巴尔扎克决裂,他们干脆取消主题、情节、人物塑造、内心分析、情景描述及一切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其后的新新小说派甚至进而废除了标点和段落。但新小说等流派热闹了一阵之后又销声匿迹。而70年代末法国《快报》的调查报告却表明,即使是现代派艺术声势最盛的这个阶段,在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中,巴尔扎克仍然位居榜首。法国小说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曾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誉为欧洲小说的“两大巅峰”,认为20世纪法国每出一本好小说,“首要的一点在于它比较像巴尔扎克的小说”。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加上美国向全球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都受到当代美国学界的冷落。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其在世界文学史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巴尔扎克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法国作家之一,他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陆续被林纾、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前辈译介到中国,民国时期中国就已出版巴尔扎克作品22种。但20世纪50年代后傅雷先生的译本,才真正使中国读者了解了巴尔扎克。1999年时值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30卷本《巴尔扎克全集》。该版本共计1200万字,除傅雷先生所译220万字外,其他均为80年代以来的新译,袁树仁、张冠尧、王文融、陆秉慧、施康强、罗新璋、黄晋凯等法语文学翻译界人士参与了这一巨制的翻译或审校工作。20年后的今天,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巴尔扎克全集》再次修订出版,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诞辰220周年、逝世170周年。
巴尔扎克的著作好比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无论是它的思想还是艺术都有待进一步开采,后人能从中获得许多宝贵启示。巴尔扎克对转轨时期的社会理解得那么透彻,以至于所有处在转轨阶段的社会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对应自身的影像。巴尔扎克对人类本性挖掘得如此深入,以至于他所写的人间故事经常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不同国籍的人们重新演绎。事实上,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高老头还在溺爱子女,葛朗台还在琢磨钱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拉斯蒂涅、吕西安等还在生存竞争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悲哀,贝姨还在受着嫉妒心和报复心的煎熬,赛查·皮罗托还在破产中挣扎,戈迪萨尔还在口若悬河地推销商品……这正是巴尔扎克毫不过时、至今仍被读者喜爱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