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端木蕻良:“唉,这两个东北男人啊”

萧军与萧红1935年春摄于上海

萧红与端木蕻良1938年3月摄于西安
一
萧军和端木蕻良,前者比后者大五岁,他们都是辽宁人,具体说来,萧军生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锦州市凌海所属大碾乡),端木蕻良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一个属于辽西,一个属于辽北,两地相距不到四百公里。在他们两人中间,还有一位东北女人:萧红。关于他们,不能省略的前情是1938年4月初,萧军、萧红在西安正式分手,5月下旬,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正式结婚;5月底,萧军与王德芬也宣布订婚,随后另组建家庭。1941年1月,萧红在香港病逝;1960年3月,端木蕻良又与钟耀群结婚。

许广平、萧红、萧军(后排左起)和海婴1937年年初摄于鲁迅墓旁
重建家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过去的种种应该翻篇了。或许,萧红是一个太强大的存在吧,她在两个男人心底产生的涟漪久久不能抚平。不仅如此,他们越过萧红,直接怼上了。准确地说,是萧军大刀砍过来,而端木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萧军常常以受害者的姿态,指斥端木蕻良为“卑劣的人”,不仅有“夺妻之恨”,而且还把萧红病逝香港的罪愆也算在端木的头上。一提起这个名字,他便怒火中烧,不能自已。在萧军日记中,他毫不掩饰地把仇恨的火焰迸射出来。1938年6月,他跟王德芬正是新情炽热时,有一天忍不住在日记中写道:“一想到红和那个卑劣的人,就感到一种恶心,也是一种森凉!”(萧军1938年7月4日日记,《萧军日记补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43页,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日期与页码)两年后,愤怒仍然未能平复:
临行前,(舒群)群也谈了一些关于红的事,他们全不满意她跟了那一个卑劣的人。……
……对于芬这样无能的性格我不喜欢。资产阶级的女人全是废物,缺乏革命热情,勇敢的行动,处理事情的能力。(1940年4月8日,359页)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端木仍然“卑劣”着,在他的日记中都不配有名字。耐人寻味的是,萧军对他结婚不过两年的妻子王德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王德芬等同于“资产阶级女人”,接着又等同于“废物”,可是从日记这段话中,确实也能看出他对女性的态度。

萧军与王德芬1938年6月摄于兰州
四十年过去了,萧军余怒未消,看法未变,他分析萧红的性格:
“知善善,而不能从;知恶恶,而不能去!”此萧红性格中意志薄弱一大主观病根也。
她逃婚,原本不愿嫁汪某,后来又和汪某同居,有了孩子,染了恶癖,几被陷于万劫难复之地;知道D.M.的卑贱怯懦,而随他以去……以至死于香港——这就是她性格中的悲剧也。(1978年8月28日,742页)
D.M.就是端木蕻良,在萧军这里,他基本上都是与“卑贱怯懦”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两天后,他又写道:“认为有利可图阿谀死人者是市侩,把一切过错全向死者身上推的是孱头!对于死者无原则,故意表示‘宽大’以显自己仁厚的是伪善者,伪君子……”(1978年8月28、30日,742页)这是表明他不想当“伪君子”,也不想对谁“宽大”?萧军的文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豪气冲天;从另外一面看,他总把自己置于正义的高地,毫不留情地扫射对方,而不知自我反省。这一点他活到老坚持到老,1937年,萧军与萧红吵架后曾这样写道:
和吟又吵架了,这次决心分开了。
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1937年6月30日,21页)
他这是在骂萧红“感情领域是狭小的”,不能容人,可是他自己呢,“爱他的敌人”吗?至少对端木的态度上,就看不出来“男人”的“有时还可以”。不仅如此,听到端木和萧红日子过得“欢快和得意”,他都心怀不满:
到西安,见到了玲,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我走后吟他们欢快和得意的情形,使自己似乎又感到一点烦乱,但这很快就过去了。
武汉不能去,暂时留在这里。我应该加紧工作了,用工作来报复伤害过我的人。(1938年6月13日,41页)
日记中的“玲”指丁玲,“吟”是萧红(悄吟),一句“报复伤害过我的人”,何其杀气腾腾,“报复”,是难以释怀,更严格讲是“恨”,是看端木乃至萧红什么都不顺眼。
“利于己则‘拥护’之,不利于己则‘打倒’之,‘无利无不利’的冷淡之。此为一般人常态,何况聪明的端木之流……”
胡来信说萧红端木等在重庆,办一大刊物,尽拉《七月》撰稿者,而且为他反对者,现亦拉起来了,言下甚愤懑。我写了那样一段话给他。(1938年10月20日,75页)
胡风这也是毫无道理的霸道说法,难道“撰稿者”是某人的私人财产,只能给胡某人写稿就不能给别人写稿?为你“反对者”,就不能另寻出路了吗?这种帮派气十足的作风,大约端木和萧红并未察觉,而萧军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讲什么“利”与“聪明”,说白了,无非是端木有“可恶罪”而已。恨屋及乌,端木的文章自然也在“恶劣”之列:“晚间同沙汀谈天。……也谈到了端木那样恶劣的文章,将来是要施行集体批评的。”(1940年1月4日,291页)我不清楚这个“将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等“将来”,是等腾出手来有空时,还是有朝一日大权在握?如果是那样,幸好,他们都没有掌权。
二
在萧军的眼里,萧红跟端木过到一起,就是明珠暗投,甚至是走向坟墓、下了地狱,他在日记中曾怜悯、哀叹、痛惜,也许是不无讽刺地写道:
阅报知道萧红等去香港,感到一种惋惜,这惋惜是为了那过去费去的劳力。我将来只有一步一步更走向了革命的一方,实际我也应该如此。(1940年2月20日,329页)
下午在刘家遇到杨、端等。从端的口中知道萧红他们去香港和孙寒冰之流去编丛书了,有一种可悲的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一步一步向坟墓的路上走了!(1940年2月24日,330页)
三五年内,没有从那种恶劣心境中走出来可以理解,更何况心高气傲的萧军被萧红“踹”了,难免用这种口气来维护一下自己的“自尊”。可是到1978年,年过古稀的他还是这么认为:“对萧红来说,在我这里她是被保护的天使,到魔鬼那里她就变成一个可怜的奴隶!”(1978年7月22日,741页)萧红离开萧军,不仅早已是成年人,而且有着人生和感情历练,孰好孰坏,她都分不清,非要舍“天使”去当“奴隶”,或者这是一时糊涂?——这些问题,越展开可能越复杂,几年前我写过《被蚊虫咬了个大包》《扯谈》《泼大粪》《温馨更爱女郎花》《端木的另一面》《编故事》等短文,引证过一些细节谈过这些问题,后来收在《躺着读书》(海豚出版社2017年6月版)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看。对有些问题,稍有平常心或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随意放大。比如有人说萧红曾给端木抄写过稿子,就做了“奴隶”如何如何。其实恩爱夫妻,妻子帮丈夫抄个稿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比如针对萧红和端木在一起过得幸不幸福,端木没有直接回答,却是提示大家看一看,他们在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萧红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这也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吧?对萧军这一面,不妨多问一句:如果他待萧红如“天使”,那么,萧红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他呢?
萧军在《侧面》(第一部:我留在临汾,跋涉书店1938年版;第二部:从临汾到延安,海燕书店1941年版)一书中,曾深情款款地谈到萧红以及他对萧红的百般呵护——写这本书时,萧军与王德芬刚结合不久,情深意切地讲前妻萧红,真不知道他内心中怎么安放刚刚与王德芬燃起的恋情。——在与萧红“分手”的经典桥段解说中,萧军再次将棍子打在了端木蕻良的身上,仿佛都是端木之不端才有他们的分手。端木在《侧面》中完全是以小丑形象出现的,萧军虽然没有直书其名,然而不论用什么化名,明眼人还是看得出那就是端木:
凹鼻子杜说完了这俏皮的话,也悄默地退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但他并没有坐下,两只胳膊抱起来了,两条穿着带有拍车的细腰马靴的小腿,又用着大角度的距离在叉开……在站着的时候,他的小肚子总是喜欢挺在外面的。他的脖子并没有毛病,可是平常时候那长形的葫芦头总是更多一点离开中心线侧垂在人的左边,以致那留得过于长的“菲律宾”式的头发常常就要像梳结得不结实的女人们的鬓发垂流下来了。为了这,女人们开玩笑就也叫他作“姑娘”,但他并不为这生气的。
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袋口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萧军:《从临汾到延安》,《萧军全集》,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0卷238页)
凹鼻子,“姑娘”,已经极尽污蔑之能事,到头来端木似乎连人也不配当了,而被称作“可怜的东西们”。萧军还写到萧红的态度:“更是那凹鼻子杜,她比我还要憎恶他……”(萧军:《从临汾到延安》,《萧军全集》第10卷243页)“红在屋子里也焦急地小声骂着这个神经错乱的人……”(萧军:《从临汾到延安》,《萧军全集》第10卷247页)按照萧军这种说法,端木蕻良在萧红的眼里印象实在不佳,最后竟能赢得萧红的芳心,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再进一步推断:这需要多大的助力,才能让萧红毅然决然地投入原本“憎恶”的端木的怀抱呢?《侧面》中,萧军洒着关心萧红的热泪、挥舞着砍伐端木的大刀,乃至1978年在为这段分手的文字做注释,又提起自己作为大英雄解救萧红的往事,却始终回避一个核心问题:萧红何以离他而去?总有原因吧。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萧军也清楚,1978年9月19日他在注释萧红1937年5月4日从北京给他的信时,说了这样两段话:
第二,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第三,引出我和聂绀弩那段谈话,是表明在临汾时我和萧红就决定在基本上各自分开了,当时还尽管未和朋友们公开申明。
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萧军:《第三十九封信注释》,《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金城出版社2011年8月版,191页)
如此看来:无法涂改的是,两个人的分手根本问题在于萧军的“不忠实”以及“无结果的恋爱”。既然这样,把责任推到端木身上,骂了人家几十年“卑劣的人”,好像不公平也不太厚道。再说,你既然与萧红分手,别人就不能与萧红结合,萧红就不能有新的生活?

萧军1977年摄于北京
更令我大为不解的是,就在写下这段承认对萧红不忠的解释文字之后不到十天,在当年9月28日萧军依然在文字中把两个人的分手之责推到端木身上,推到萧红的决定上,同时,也不忘显示一下自己的大度和豁达: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线,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
……
既然有了原先的“约定”,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又是她首先和我提出了“永远诀别”,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不管她此后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天”或“魔鬼”,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对于夫妻、对于朋友……我是谨守着中国这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古老格言的。(萧军:《〈侧面〉注释》,《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259-260页)
在这几段话中,萧军不断地暗示“别人”在其中作梗,当然剑指端木蕻良,他还是耿耿于怀嘛。那么前面对不忠的忏悔,不能说虚情假意,也是浮皮潦草吧?萧军给人的印象向来是侠肝义胆、一身正气的,然而在处理感情等问题上也不能不让人感慨:人是复杂的!萧军的所作所为是他自己说的“谨守着中国这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古老格言的”吗?相信人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端木蕻良呢,背负着几十年的骂名,不仅来自萧军,还有萧军的朋友们。1981年,在胡风的文章里,端木蕻良还是那个被轻蔑的“T”,胡风谈萧红时是这样说到端木蕻良的:“第二年初夏她回武汉了。而伴同她回来的可是和她并不相投、还很看不起的T。”(胡风:《悼萧红》,《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卷132页)1946年,在聂绀弩的文章中,端木蕻良是“D·M·”:“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萧红——引者按)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么?”(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武汉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卷137页)在他的转述中,端木蕻良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三“鬼”,也不配做人。聂绀弩先后曾有数篇诗文谈过萧红,颇有将自己引为萧红知己之感,那么,他能否体察一下老朋友萧红何以要嫁给一个不配称人的人呢?

萧军、胡风、聂绀弩(左起)摄于1984年
三
聂绀弩于《在西安》结尾写过这样一个细节,也算是二萧分手过程中的经典场景,其中的端木蕻良无疑又是作为小丑而存在的:
半月后,我和丁玲从延安转来,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到五台山去的中途折到延安,我们碰着了。一到××女中(我们的住处)的院子里,就有丁玲的团员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D·M·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人都愣住了一下。D·M·就赶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等复杂的意义。我刚走进我的房,D·M·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聂绀弩:《在西安》,《聂绀弩全集》第4卷139页)
他和萧军一样,认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是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萧红后来的确是早亡,然而,这就证明他们说对了吗?对上面的场景,萧军在日记中曾经计划过,看来他是有过多么精心的设计和构思:
《侧面》的结尾预备这样写:
当我满身满脸挂着路上的尘土走进了D服务团所在的一个院子,凹鼻子T先走过来机械地和我拥抱了一下,尴尬地笑着,我也木然地回了他一个拥抱……。红女士远远地表示着身份地站在门口,变得漂亮了,脸有点红的样子笑着……
夜间,她吃着纸烟,不自然地两腿交迭,一位贵夫人似地向我提出了:
“遵照我们在临汾的决定,分开吧,我们的友情还是存在着的……”
“好吧,一切随您的意思……”
我实在倦怠了,眼睛还可以不动地看着天棚板,渐渐地就什么全变成了模糊……。(1938年8月6日,51页)
同样场景,多年后,端木蕻良却另有说法:
端木蕻良在几十年以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他说:那天萧军跟着丁玲从延安回到了西安,然后便在一间大房间里胡乱地按着一架破旧的风琴。当时房间里只有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三个人。萧军一面按琴一面背对着萧红和端木蕻良,气氛有些沉闷。过了一会儿萧军冷不防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和丁玲结婚,你跟端木结婚……”端木蕻良听了顿时感到非常突然。他觉得萧军这种态度,就好像是把萧红当作一件自己不要的东西,顺手摔给他似的,同时他觉得这是萧军对他人格上的侮辱。端木蕻良认为自己一向只是把萧红当作姐姐来看待。萧红比他大,又有过两次同居的经历,身体也很不好,因此端木蕻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和萧红结婚。至于萧军说他要“和丁玲结婚”的话,或许只是想气气萧红。果然,萧红听了勃然大怒。她对着萧军说你和谁结婚我不管,难道我们结还用得着你来主婚吗?晚上,端木良在房间里听到萧红和萧军在壁房间里吵架,只听萧红大声地说,你把我给你的信件退给我,我把你给我的信件退给你……萧军不肯,而萧红则毫无保留地把萧军的信件退了回去。两人彻底闹翻了。端木蕻良眼见着事态如此急剧发展,看到红公开受到萧军的奚落,而自己又一向是对萧红极为尊重的,经过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萧红一边。(端木蕻良1996年6月25日接受孔海立采访录音,转引自孔海立《端木蕻良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81页。这个内容在钟耀群口述、孙一寒整理《钟耀群谈端木蕻良家事》[华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一书第二章中“与萧军的恩恩怨怨”一节中也有叙述,细节略有差别。)

1938年3月21日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1938年3月端木蕻良在西安,手里拿的是萧红赠给他的小木棍。
没过几天,萧军得知萧红有了身孕,看重孩子的他又希望与萧红和好,被萧红拒绝。有一夜他闯进端木的宿舍要与端木决斗,萧红闻知,怒斥他一顿。“虽然萧军的决斗计划没有实行,可是萧军又采取了新的行动,那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走到哪儿,萧军就在一二百步距离的地方跟到哪儿,而且手里还拎了一根粗大的棍子。”(孔海立:《端木蕻良传》81页)这使端木蕻良和萧红不得不远离萧军,回到武汉,不久,他们也就结婚了。端木的叙述是否可信,似乎不能直接判断,而我们能看到的结果则是,随后不久,萧红便与端木结婚了,不是“同居”,是在武汉郑重办的酒席。端木后来也说:“我可以告诉您,萧红是我第一个妻子,在这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我和萧红结婚是在到达武汉,并由池田幸子等人赠送了礼物的。”(端木蕻良1983年3月16日致夏志清信,《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299页)
背负骂名的端木蕻良多年来并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为自己辩解,在私人通信中,他曾表明这样的态度:“我将来有工夫自己写文章,会说清楚的。本来他们的文章自相矛盾处是很多的,实在不值我一驳。但真相毕竟是真相,我是要澄清的。”(端木蕻良1981年11月14日致曹革成信,《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45页)端木蕻良觉得人们的很多误解都来自骆宾基那本《萧红小传》,晚年他曾打算就此写文章,并向友人求证事实:
记得当年我曾接到骆宾基初抵香港时,我与他本不相识。收到他电话时,他说:他本来到港投奔茅盾的,但茅盾并不能援之以手,所以处于困境,打电话给我。我因忙,特请你代我接待他,并安顿他住在时代书店,这一切都由你亲自作的。好像你过去写过一篇文章给我,我不记得发表未,该文因年久,也不知压在何处。吾兄暇日,最好重记此事,寄我,因为我要为萧红和我自己写些“点滴”文字,因为我无暇写长篇大套。(端木蕻良1993年8月14日致张廷珍信,《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518页)
按照端木的说法,骆宾基根本没有机会从萧红口中了解太多的内容,他对萧红的了解也极其有限,那么他的《萧红小传》的素材都来自哪里?是不是看端木不顺眼的那些朋友之口?他总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去想象吧?因为身体原因,端木的文章没有写成,不过,他跟孔海立和葛浩文的谈话中均对当年的事情做了解释,在给刘以鬯的书信中也透露很多细节:
其实有许多事情,很容易清楚的。比如在上海萧军和雨田发生不正常关系。雨田即黄源之妻,当时许多人都知道。黄对此深表愤慨,但不易声张耳。萧红本欲于鲁迅先生前揭穿,但以先生病重,不忍打扰他,仅数次对许先生诉说此事,未向鲁迅先生倾吐实情,遂远去日本。……后来抗战暴发,萧红对萧军忍隐未发,亦冀其在环境改变后,有所好转。谁知在临汾时,与丁玲相遇,又故态复萌。临汾沦陷,萧军从洛川入延安,由延安返西安,他公然宣布要与丁玲结婚,谁知丁玲不予承认。萧红毅然与萧军离婚。丁玲,我与萧红等人为战地服务团写的一剧本正在上演,丁玲在后台又与陈明发生关系,后与陈明结婚,以平息这件公案。吾因不愿涉及个人私事,但不如此,不足说明问题,故连带及之也。
另外,如骆宾基何时来港,当时萧红已在病中,骆打电话找我,住在时代书店。从玛丽医院回家,我带骆到我家中与萧红见过一次面,略谈即去。从此再未来过。萧红既未谈过他的作品,对他也无任何印象。香港战起,十一月七号,骆打电话告我,他欲返上海。我因萧红病,请他留下帮忙,将来一同回国,萧红此时都在卧床。香港战事历时十八天。萧红在养和医院由李树培开刀,不能封口,(喉结核),说话只有气无声,因为要插管子引痰出来。在这期间到处流转,抢救不迭,无时不在危急之中。骆宾基与萧红相识的时间,由十一月七日到一月二十二日不过四十多天。当时萧红谈话都已困难,对萧红有何了解之处。
由于人们所未察,故聊述数语。(端木蕻良1984年4月14日致刘以鬯信,《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381-382页)
信中谈及丁玲与萧军事,后来发表的萧军的延安日记可证这并非捕风捉影,然而,信中言及的很多都事涉隐私,大约也正是端木所顾忌的吧,故而一直沉默不语。他的沉默,似乎坐实了人们对他的指责,“负心人”的帽子要一直戴下去,也越发让人更加义正辞严。
四
像端木蕻良这样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谦谦君子,又有不凡的才华和不小的成就,在朋友圈里怎么就不被待见呢?从与端木有来往的人的回忆文字看,我认为这可能与端木的个性、性格都脱不了干系,以至让人们一眼看上去就有“非我族类”之感。从装扮到行为,他可能都与众不同。1994年3月29日赵淑敏采访端木蕻良时,“端木坦承他年轻时说话常常非常尖刻不留余地,待年事渐长,到了四十岁后才悟出不对,所以慢慢改了。由此可以推断,以往多人不说他好话,可能跟这个原因有关”(赵淑敏:《端木蕻良的感情世界》,原刊《传记文学》第69卷第6期,现收中共昌图县委宣传部等编《端木蕻良纪念集》,内部出版物1998年6月印行,137-138页)。这是到老了他才有的自省,年轻时他更有“个性”:
萧军、端木、萧红都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一分子,萧军、端木却是两位不同型的东北男人。陈纪滢伯伯说陈伯母早年初次会见一批东北作家的时候曾说:你这批朋友,哪像是作家?连乡下扛长活儿的老粗都不如!就指的萧军、舒群、罗烽等人。……至于端木,陈伯伯也说端木与陈伯母所批评的那些东北作家不同型,证之萧军以及多人所形容这观察非常正确。端木到底到老到死,也很文雅而且“很有学问的样子”,他不是装出,乃是实在有他的学养造诣。出身较好的家庭环境;读过南开中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学校;哥哥们都受良好教育,也带领了他;新时代的思潮更熏陶了他,但是他在底子上仍是上一代型的东北男子,潜在的心性,很难不以“我”为主体,对夫妻相处,像他自己形容的“大大咧咧”的。这种性格,纵然无心无意,却会出现像薄情自私的性格。
这段话,既道明端木与萧军等人气质之不同,以至自然而然就被众人排除在外,又指出在“东北男子”的“大大咧咧”这一点上,端木与其他人似乎又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敏感的萧红对端木的“怨”并非全无来处。“大少爷”出身的端木在领会女人心思方面以我为主的迟钝,难免给人造成薄情寡义的印象。赵淑敏也曾分析萧红生命中最后那段时间:“不论骆宾基为萧红写的传中,有多少出自揣摩和猜测,端木则又做了一件不懂女人心理的事应该属实。那时的萧红也许可以找到一百个人帮忙照料,她最希望的还是端木自己的温馨呵护。我曾把这几句话告诉端木,端木久久未语,想来他总算明白外传萧红对他的怨,应当不全是臆测捏造的。”(赵淑敏:《端木蕻良的感情世界》,《端木蕻良纪念集》141-142页)
“久久未语”,这是端木多少年后才被点醒的问题吗?不论怎么样,我认为赵淑敏这个分析是客观的。
汪曾祺谈到端木蕻良在单位里和生活中的“孤傲”,也让人品味出他大半辈子何以落落寡欢:
关于端木的为人,有些议论。不外是两个字,一是冷,二是傲。端木交游不广,没有多少人来探望他,他也很少到显赫的高门大宅人家走动,既不拉帮结伙,也无酒食征逐,随时可以看到他在单身宿舍里伏案临帖,——他写“玉版十三行洛神赋”;看书;哼桂剧。他对同人疾苦,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不善于逢年过节“代表组织”到各家循例作礼节性的关怀。……至于“傲”,那是有的。他曾在武汉呆过一些时。武汉文化人不多,而门户之见颇深,他也不愿自竖大旗希望别人奉为宗师。(汪曾祺:《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原刊《北京文学》1997年第3期,现收《端木蕻良纪念集》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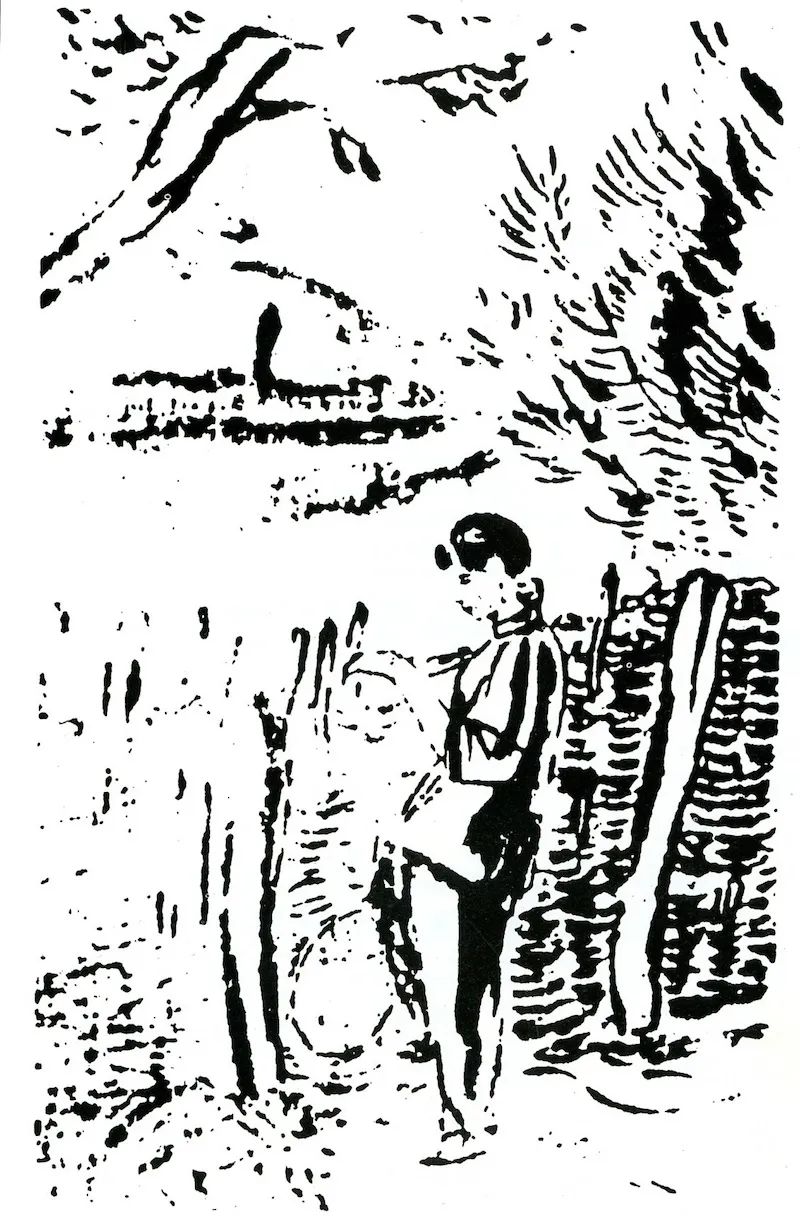
端木蕻良为萧红小说《小城三月》绘制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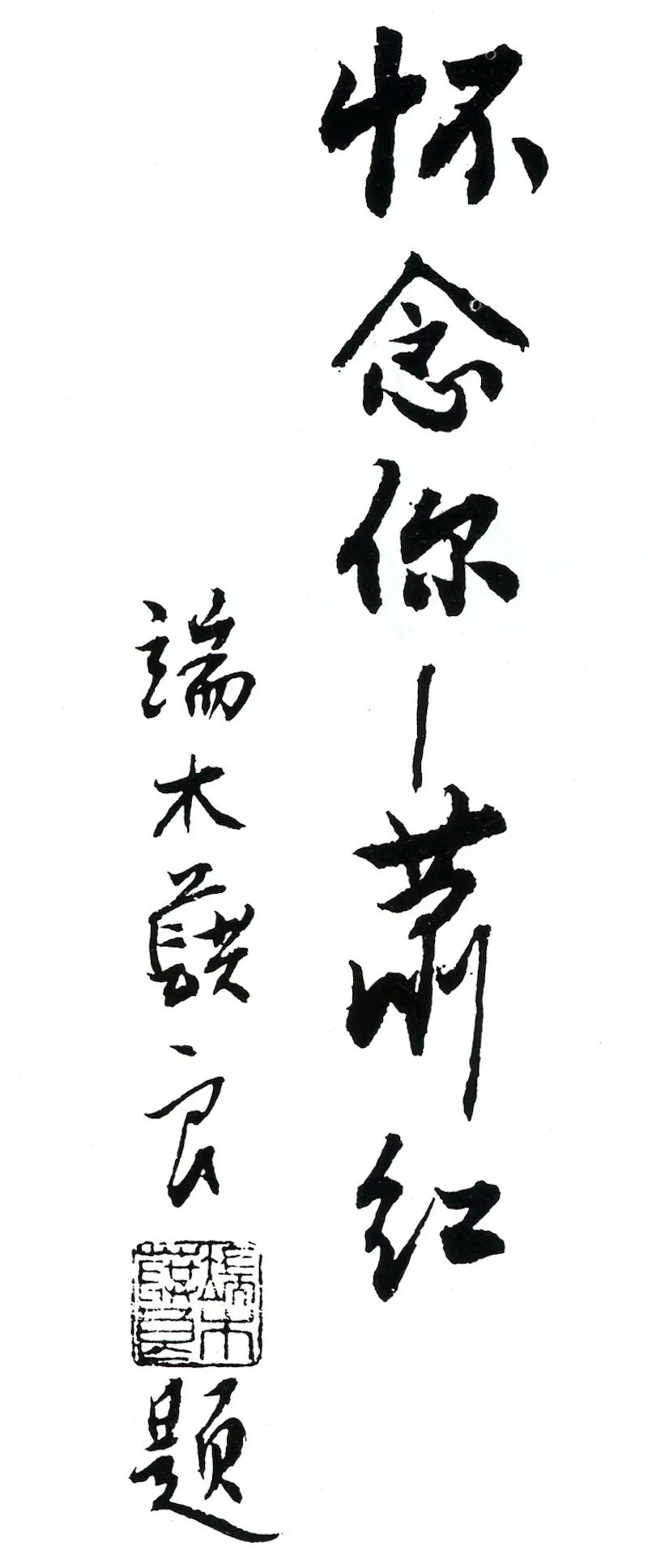
端木蕻良为《怀念你——萧红》一书题写书名
这是深知“江湖险恶”之人的一针见血之论。不走动,不拉帮结伙,不自竖大旗,这也就是自绝于“帮”“伙”之外。文人们,看样子文质彬彬,谦逊客气,谈“宽容”“正气”音量都很大,一旦斤斤计较、勾心斗角和互相打压起来,恐非武人可及。端木蕻良跌打滚爬大半辈子,对这些不会不明白,明白了还趴在单身宿舍里临“玉版十三行洛神赋”,那就不仅是性格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完全是他的个人选择。
五
萧军日记中记过这样一件事情:
下午三时由市文联派车来与滨儿去政协礼堂参加全国文联召开左联五十年大会。……
……
同车竟然遇到了D.M.,竟无意打了招呼,觉得很后悔,但也没什么。(1980年3月28日,769页)
打个招呼如此在意,“很后悔”自己主动了。收到端木寄来的书,萧军的评价是:“端木蕻良把他的《曹雪芹》送给我一本。这人做人很‘厉害’!他是个有才无德的人。”(1980年4月12日,771页)这一回唯一的进步是承认端木“有才”,不过,还跟了个“无德”。然而,送一本书,又理解为“厉害”,仿佛端木能借此又搞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两个人后来的交往,《端木蕻良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一度曾经有好心人想要为端木蕻良和萧军等拉和关系,希望各方心平气和地握手言好。端木蕻良想了想,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过攻击对方的语言和文字,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心平气和的,并不存在什么让他不言好的。他说他在香港办《时代文学》的时候就把萧军、骆宾基等都列入主要组稿对象,到北京以后他又把萧军、骆宾基等都列入他私人的赠书名单里。每次自己有新书出版,也不管他们是否接受都赠上一本。后来,当年曾经扬言要揍端木蕻良的骆宾基也和端木蕻良有一些通信来往。不过萧军却仍旧耿耿于怀地不愿理睬端木蕻良。尴尬的是:有时外出开会,恰逢端木蕻良和萧军要合坐一辆车,萧军就不愿上车了;端木蕻良无言争辩,主动让出车位,骑着自行车上路。(孔海立:《端木蕻良传》174页)
“有时”“要合坐一辆车”,看来不止一次。不过,从前面所引的萧军日记看,至少那一次,并没有萧军不上车的细节,萧军那天还“无意”中打了招呼,也算主动吧。其实,他们也不是没有坐到一起的时候,还有照片留下来呢,钟耀群说:
20世纪80年代,瑞士籍华人作家赵淑侠来采访端木。她觉得端木22岁就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真是了不起,认为端木是一个奇才。北京市文联在文联的俱乐部招待了她,她请市文联邀请萧军、端木、骆宾基同来,她想和这三个人共同照一张相。她当时心里想:这三个人肯定是不会共同来的。接到邀请后,端木问我:“耀群,你看,这个事?”我说:“去!不去干嘛!”结果,三个人都去了。我还给赵淑侠和他们三个人在一张沙发上照了相。(钟耀群口述、孙一寒整理:《钟耀群谈端木蕻良家事》128页)
这张照片后来用在《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上)的卷首,照片上共有六人,他们挤在一个沙发上,可以说是人挨人,近距离,赵淑侠和骆宾基居中,紧挨骆宾基的就是端木蕻良。左面那一侧,紧挨赵淑侠的是萧军,他们的眼神都冲着拍照者的镜头,即前侧方,故彼此的目光并无交集。萧军像是若有所思,骆宾基的表情最为凝重,端木蕻良最为轻松,几乎是张着嘴在微笑。——这是不是无意中透露出,他已经放下了诸多历史的误会和重重心事?赵淑敏曾转述过这张照片的拍摄细节:
因为我听姐姐说过,那年端木、骆宾基、萧军一起参加欢送赵淑侠的聚会,赵淑侠提出要与三位前辈作家共摄一影的时候,主办者似乎碰了难题。不管端木被骂臭了,从不曾在文字上辩驳故交的抨击,却也数十年没有往还;另两位无论在言语与文字中更大力地苛斥过端木,这样大的提议,实在强人所难。眼看那情况就僵住了,还是端木蕻良稍迟疑一下,首先坐了下去,因而另两位才也比肩落座,完成了那历史的一页。(赵淑敏:《端木蕻良的感情世界》,《端木蕻良纪念集》136页)

难得的东北作家聚会,左二起:萧军、赵淑侠、骆宾基、端木蕻良、雷加,摄于1980年代。
端木蕻良放下了,坐下了,然而,别人不一定都放得下。端木蕻良信中谈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和耀群于六日由沪飞京,回来后,耀群清理大批积信,未发现有哈尔滨请柬。我们既不知何人主持,也不知何人出席,但只要有请柬,我虽疲惫不堪,但还决定赴哈参加的。我们又托人去文联作协打听,是否压在那里,也没有。所以只得作罢。收到你的信,才知道萧军和骆宾基从中作梗。”(端木蕻良1981年5月10日致钟汝霖信,《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下317页)这应当是1981年在哈尔滨召开的萧红纪念会,“邀请了中外人士数十人,其中有葛浩文以及许多年轻的国内外学者,应邀的还有萧军、骆宾基、舒群、塞克等和萧红生前有关系(包括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士,就是偏偏把和萧红举行过婚宴并共同生活了长达近四年的端木蕻良排除在外”(孔海立:《端木蕻良传》173页)。多少年了,端木蕻良一如既往遭到“一致”的排除。难道彼此之间真有解不开的疙瘩?细数一下,无非那几件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嘛,每个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不能释怀,还要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这是难得聪明,还是难得糊涂呢?

1985年10月,端木蕻良在汉口找到1938年5月他和萧红结婚的大同酒家,登上二楼,感慨万千。

1987年11月4日端木蕻良夫妇在广州萧红墓前
端木和萧军,两个东北同乡,本来是很好的朋友。1937年春天,端木在给读者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萧军:“新作家萧军极好,气魄很大。”(端木蕻良1937年4月10日致读者信,《端木蕻良文集》,北京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8卷下20页)那一年8月,端木蕻良与二萧相识后,也很谈得来。1937年11月,端木蕻良接到萧军、萧红的信,就是催促他去武汉的,信中还附有萧军的长诗,在文学上可以信任的朋友之间才会这样寄诗文,这也证明萧军对端木很友好。后来,端木不顾腿疾没有完全痊愈,匆忙奔赴武汉,到武汉后,最初,他们几位东北作家曾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很多美好的事情尚未开始,便匆忙结束,想不到在武汉他们已渐渐埋下冲突的伏笔……唉,这两个东北男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