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有灵性的文学翻译翩翩起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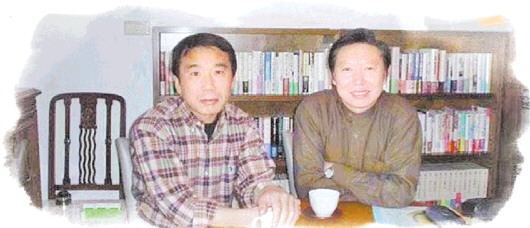
林少华(右)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东京。
从黑土地的吉林大学出发,南下珠江之畔的暨南大学,北上黄海之滨的中国海洋大学,他执教三尺讲坛四十多载;作为拓荒者,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45部,总发行量超过1420万册;他退而不休,辗转全国各地高校,向青年学生讲授审美忠实的翻译观和开卷有益的心得……他就是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
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教授您好,请问您是怎样与村上春树先生结缘的?
林少华(以下简称“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广东暨南大学任教时,机缘巧合,翻译了《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1989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村上春树写这本书时,是三十七岁;书中主人公渡边君,也是三十七岁;我是迟了三年翻译的这本书,也是三十七岁。三个“三十七岁”赶在一起,说奇妙也够奇妙的。
然而,不同的是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的处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
再看我这个译者。你别说,我的处境好像还没那么低档。住的是破格提为副教授后分得的两室一厅,桌子不但有,还是新的,请木匠师傅新打的“两头沉”,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减价转椅,唱机也不是村上那种“随身听”,而是留学回来在友谊商店买的免税组合音响。播放的乐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
星移斗转,月落日出,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翻译之初,“三十七岁的我”身上还多少带有青春余温,大体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满怀豪情,而今,即将年满七十岁的我,残阳古道,瘦马西风,“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不过,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桩,那就是我的翻译业绩,迄今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来,我翻译的书起码有一百本了。翻译过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边淳一等十几位。以作品言之,《我是猫》《罗生门》《金阁寺》《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分外受到认可与好评。
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和《刺杀骑士团长》在内,由我独立翻译的有四十三本,与人合译的有两本。这四十几本沪版村上,截至2021年12月底,总发行量超过1420万册,读者人数则远大于此。这其中,《挪威的森林》总发行量超过600万册。也就是说,我这支自来水笔涂抹出来的译文,已经摇颤过数千万读者的心弦。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如静夜纯美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又像远方炊烟袅袅的小木屋引领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长满三叶草的山坡让自己抱着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纪末的反思》中,将《挪威的森林》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挪威的森林》入选“金南方·新世纪10年阅读最受读者关注十大翻译图书”之列。
记:中国读者为什么这么青睐村上作品?
林:2018年10月,金庸先生去世时,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对于村上春树,不妨说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村上。
村上何以这么火呢?据村上自己总结,一是因为故事有趣,二是因为文体具有“普遍性渗透力”。文体,这里主要指笔调、笔触,即文章总体语言风格;普遍性渗透力,用村上的说法,大约就是语言具有“抵达人的心灵”的力量。从翻译角度来看,故事这东西,谁翻译都差不太多,差得多的是文体,是语言。
两次面见村上
记:您曾经去日本任教,其间,曾拜访过村上先生,请谈谈您和他的见面情景。
林:说起来,我见了村上两次,地点是位于日本东京城中心的村上春树事务所。
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1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翻译了村上先生十七八本书了。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神交”,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所感,甚至能够看到他的表情,感觉到他的呼吸,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村上春树。
用钱锺书老先生的话说,鸡蛋好吃,吃鸡蛋就是了,何必见那只下蛋的鸡?话虽这样说,但如果有机会见面,对翻译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村上一般不轻易和别人交往,尤其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不喜欢上镜,记者很难采访到他。我对和他见面还是有些自信,就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表达了我想见面的意思,村上很痛快,就约定了2003年1月份见面。
记得尽管当时正值一月寒冬季节,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色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想到作家两个字。
我们交谈时,村上不大迎面注视我,眼睛更多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沉稳舒缓,颇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尤其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边君,而且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
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好像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他也是翻译家,翻译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果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后来我又采访了他,内容涉及灵魂的自由、孤独和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见面是2008年10月底,借去日本东京大学开“东亚与村上春树”专题研讨会之机,是和别的学者一起去的,聊的内容比较杂。东京大学有位学者说,村上受到鲁迅的影响,尤其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见到村上,我当面向他求证。
村上说,那是巧合,不过他是看过《阿Q正传》的,对此文评价很高。他说,鲁迅描写了与作者截然不同的阿Q形象,使得鲁迅自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
这两次见面,我感觉我们两人相似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很珍惜时间,不想虚度每一天。
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
记:谈起村上,绕不过去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话题,村上多次提名,却都无果。村上的诺奖缘分,您怎么看?
林:村上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审美标准的“理想主义倾向”。村上表现理想主义,对社会公正、正义方面的诉求,同时对待暴力、集权主义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如他对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的个案进击式的扫描;他追问人类终极价值时体现的超我精神;他审视日本“国家性暴力”时表现出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在拓展现代语境中的人性上面显示的新颖与独到,以及别开生面的文体等。
事实上,村上连续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十几年。同样作为事实,年年入围,年年落得个所谓陪跑下场。个中原因,固然一言难尽。至于究竟为什么没有得到,所有说法都是猜测。
倘若容我大胆假设,村上未获诺奖的原因会不会和翻译有关——英译本会不会未能充分再现村上文体的特色?
我一向认为,一般翻译描摹皮毛转述故事,好的翻译重构原作的文体之美。在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很看重文体或者语言风格的艺术性,尤其艺术创新性。我觉得,在这方面,村上的语言风格自成一体,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总的说来,村上在中国之所以那么流行,较之故事有趣,更在于文体的别致。他文体的独辟蹊径、独具一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学影响,从英语文本,有英语腔,有翻译腔,不纯粹是日本传统文学语言,固然是用日语写的,但不是川端康成、川岛由纪夫,走的不是传统文学路子,向西方文学学的东西多。由此村上作品形成了带有西方英文腔调的语言风格,而这种语言风格再翻译回来,译回英文的时候,这种特色就明显消失了。也就是说,这种语言风格,对中国读者新鲜,对日本读者新鲜,但是对英语读者不新鲜了。村上作品在翻译回英文的时候,语言显得新鲜好玩的东西就消失了。
“翻译是把双刃剑。”我引用翻译过《挪威的森林》和《奇鸟行状录》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杰·鲁宾的说法:村上文体那种来自英文的新鲜感在译回英文的时候就消失了。换成我的说法,英译本未能充分译出村上文体特色或语言的独创性,这很可能是村上连续无缘于诺奖的一个原因。
记:您讲到,村上文学的主题之一,在于表达孤独、孤独感——不断叩问现代都市夜空中游移的孤独的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请您解释一下。
林:村上是纯粹的城市人,诉求最多的是城里人的感觉,表达城里人的孤独感、疏离感,纠结和郁闷。尤其是在网络信息时代,村上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我想,提供的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城市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中、嘈杂声中感受到生活的诗意。如今在网络、智能手机的影响下,人们对花花绿绿的碎片信息的追逐,而忽略了身边的大自然,如一声鸟鸣、一缕夕辉、一朵牵牛花、一朵蒲公英,网络、智能化手机钝化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感受,钝化了生活的诗意。
村上文学,恰恰带来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如此高度城市化,甚至后现代、后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如何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保留一分对于弱小生命、对于细小寻常风景,敏锐审美的感觉,使自己的心灵充满诗意,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我想,村上通过一种文本,通过中译本,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视角。
2017年,我翻译了村上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小说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花了堪称天价的版权费——那可不止“一掷千金”——买来的。如果仅仅买来一个有趣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值得的。中国会讲故事的人多了,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种具有“普遍性渗透力”的文体,那么就会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种异质性审美体验,进而拓展中国文学语言表达的潜能和边界,同时带给中日两国文学和文艺审美交流以新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么版权费无论天价还是地价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翻译:一般翻译转述内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语言美感、文体美感。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旨趣、妙趣和乐趣所在。
记: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翻译的?
林:文学翻译是艺术,是语言艺术,有灵性的文学翻译翩翩起舞。而对于艺术来说,所谓正确、精确并不总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愉悦、重构审美信息。换言之,真正的文学翻译,不是传达杨贵妃的三围数据,而是发掘“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性美感。这也是我的翻译观:“审美忠实”。
翻译和弹钢琴有关。有人说,原文好比乐谱,译者好比钢琴手,乐谱是同一个,但弹起来一人一个样。大家面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曲谱都是一样的,但是十个钢琴家弹奏,就是十个味道。《挪威的森林》,文本是一样的,一百个人翻译,有一百个《挪威的森林》。故事是一样的,主题是一样的,情节人物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语言风格,特别是通过语言给人达成的审美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我爱讲台,舍不得学生的眼神
记:近一二十年,您到全国各地的高校给大学生开讲座,他们提问时比较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林:2018年,中国海洋大学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面向大学生开展“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我受聘任后,本着加强美学教育、提高大学生审美素质目的出发,从修辞之美讲起,以文学为主,其中村上春树文学这一块讲得比较多,侧重于他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特色,和修辞、美育联系在一起。
通识教育,讲的必须是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学生是自愿报名参加。讲村上春树,学生提问时,比较关注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村上文学翻译、村上印象、孤独等内容。
每次讲座,我非常看重讲稿,即使讲的时候不照稿念,手中也一定要有稿,稿件内容是经过推敲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听过别人的演讲,有相当一部分人,山东讲完了关东讲,关东讲完了广东讲,一篇稿不知道讲多少次。有的听众说,“那个老师的讲稿我已经听第五次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作为演讲者,告诉自己可不能那样,多不好意思呀。
即使要用旧稿演讲,也要与时俱进,补充新的内容、新的证据。我讲村上文学,除了接触面广之外,我注意要有一点幽默感,甚至自我调侃也好,演讲面对的毕竟不是学者,不是学术研讨会,而是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时也有社会各界人士,尽可能用共性话题切入,带出一点学术性来,让演讲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我喜欢用书面语言演讲,还颇受听众欢迎。讲座上,口水话的语言、日常性的语言听多了,突然听到文学性书面化语言,哎,就会有一种新奇感,可能我打了这么个擦边球吧。
我演讲时,向青年学生传递美感,注意用有美感的语言,唤醒大学生对美的感觉,尤其对唐诗宋词之美,唤醒潜在因子。古代文学的基因,毕竟还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只需要进行文学的引发和激活。我告诉他们,一日不可虚度。别老看手机,碎片化的阅读,很容易把自己的语感搞坏了。开卷有益,通过文字审美阅读,有一种快乐感、幸福感。如果这种感觉消失了,是多大的损失啊。
记:与年轻人交流,对您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演讲可以获得新的刺激,相当于无偿地占有别人的思想资源、情感资源。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一线,我毕竟还在第一线工作着,经常接触年轻人,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我能够被年轻人所接受,应该是一种幸运。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且做点什么。我没有感到与年轻人之间有代沟,孩子们很可爱。他们认真看书,认真思考社会、人生和未来。
说到底,我爱讲台,舍不得学生的眼神。
关东、广东和山东
记:关东、广东和山东,在您的心目中,有什么不同的生命体验?
林:今年我即将年满七十岁,从生命的长度来说,目前这三地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每个地方大都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如果细说,关东是我的出生地,广东是我的福地,山东则是我的新天地。
我1952年出生在关东,后来跨入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吉林大学。毕业后南下广东,在暨南大学开始了教书生涯,经历了翻译《挪威的森林》的兴奋和喜悦。我翻译村上春树作品40多本,主要作品是在广东翻译完成的,广东让我走上了翻译之路,奠定了翻译事业的根基。
我祖籍山东蓬莱,古称登州府。1999年,我因缘际会来到青岛海洋大学工作,教授日本文学。当时,村上文学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了,因为翻译村上,我也有了知名度。
在中国海洋大学二十多年,我有幸得到了专业内外许许多多学生的喜欢,得到了外国语学院内外许许多多同事的喜欢,同时得到了校长的喜欢。管华诗校长时代,我得以在一无档案二无户口的极端情况下破例调入海大;吴德星校长时代,我在年满六十岁时面临“一刀切”退休的时候破例延聘五年;于志刚校长时期,我接过了学校“名师工程”通识教育讲座教授聘书,也算是破例。校长们的关爱,显示了海洋大学所特有的精神格局、境界和情怀。
好在我是农民出身,关东的黑土地告诉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不得偷懒耍滑投机取巧。目前我翻译了一百本作品,大体二分天下。一半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即沪版村上;另一半在青岛。
看老版连环画重温童年记忆
记:请谈谈您最近的计划,比如翻译、著书、演讲等。
林:常言说,翻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他人做久了,就想自己做上一件。也是客观上有报刊约写专栏文章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逼着自己每周琢磨一篇。10多年来,写了600多篇散文、杂文、小品文,现在是668篇,150多万字,已经结集出了10本书,给自己做了十件“嫁衣裳”。
这次到关东的故乡度假,计划赶一部书稿,翻译一本书,还有就是把《三国演义》连环画重看一遍:在院子葡萄架下,搬一把藤椅,看《三国演义》连环画,老版的,买了好几年了,一直想坐在葡萄架下,把小时候没有看全的补上。一年忙到头,始终找不出时间来,今年我一定要重看一遍,重温童年的记忆。
我这辈子有两大爱好,或者两大幸运,一个是书,一个是树。教书和种树,也就是树人和树木。碰巧,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我的爱好是种树,喜欢大自然,喜欢花草树木。客观上,我在乡下的房前屋后,种植了一二百棵树。篱笆外面种植散树,院墙里面种植果树。我的快乐,来自阅读,来自花草树木。
尽管住在海边,我去海边的时候很少。我是山民出身,在山沟里长大的,对山、对花草树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审美角度看,大海毕竟是宏大叙事,自然有变化,微观上看不清楚,感觉比较单调。山就不同了,一年四季甚至每天都有变化,树叶发芽、长大,一天一个样。颜色上,春天是新绿,夏天是浓绿,秋天是金黄,山的表情要比大海的表情丰富得多。
翻译、著书、讲座……退休了还被认为有“剩余价值”,还被人需要,更是一种幸运。讲座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听者云集,山鸣谷应,掌声笑脸,香茗鲜花,想痴呆都休想,夫复何求!一句话,不是苦了,而是乐了,美了,爽了!
受访者简介:
林少华,1952年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主要著作有《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乡愁与良知》《雨夜灯》等,译著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作品,以及《我是猫》《罗生门》《雪国》等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 许钧谈枕边书[2022-05-17]
- 王家新:它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命名”[2022-04-27]
- 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翻译与传播[2022-04-22]
- 67岁的林少华 为何自认不适合重译《挪威的森林》?[2022-04-01]
- 汉语语境中的西语诗歌翻译实践[2022-03-29]
- 2021年度日本文学综述:现场、沟通与边界的探索[2022-03-18]
- 王家新:诗无论古今,“崇高”依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2022-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