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评价中的圣俗问题 ——以寺庙空间为切口的考察
摘要:在汪曾祺小说评价史上,出现了大量围绕圣俗问题展开的研究,这与作家笔下出现的寺庙和僧尼形象密切相关。汪曾祺家学传承、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表明,佛教文化的确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但作家与宗教思想、义理之间并无密切关联,寺庙空间在其文本中更多承担的是表现世俗化生活的功能,其寺庙题材小说的出现以及和谐、圆融风格的形成也有着比佛学修养、禅宗体验更为复杂的背景。学界常见的那种用佛教观念解读汪曾祺小说的路数存在误读的嫌疑。解读汪曾祺的创作不应一厢情愿地将其带入批评者建构的“传统”,而是要回到作家自身以及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后立刻引起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题材“没有政治,没有革命”[1],却把大小和尚和他们日常的生活空间带回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而以寺庙为空间的叙事,在汪曾祺8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并非孤例:这包括了《受戒》《幽冥钟》《仁慧》等。在50—70年代,寺庙生活几乎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湮没,并不常见。当汪曾祺在80年代初开始描绘寺庙并将它们与宏大叙事剥离时,对读者和评论界构成了挑战,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其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从《受戒》发表开始,以汪曾祺的宗教观念为向度展开的批评就已经出现。从“神的冷酷的戒律清规丧失了一切权威”[2]的反佛教立场,到后来将《受戒》所表现的人之欢愉归入禅宗“不生思虑,直指本心”[3]之法,评论界不断勾连汪曾祺思想及其文学创作与佛教传统之间的关联。而汪曾祺在晚年又为《世界历史名人画传》的“释迦牟尼”卷撰文,似乎更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他与佛教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若对汪曾祺的家学传承、成长历程、教育背景[4]等进行考察,其实很难发现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正像汪曾祺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自报家门》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的,相比中国传统的道家和佛家,他从情感上还是更乐于接受儒家思想。他明确表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5]但是,缘何这样一个接受佛家思想很少的作家创作了很多以寺庙为叙事空间的作品?寺庙空间在汪曾祺笔下到底承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秉持着宗教观念?一直以来评论者在解读汪曾祺以寺庙为背景的小说时是否存在误读?这些都是值得清理的问题。以汪曾祺小说中的寺庙空间形态为切口进行考察与反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其作品审美特质的生成以及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进程。
一、 “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
汪曾祺在《受戒》创作谈中曾说:“我的家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我的家乡没有多少名胜风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6]的确,在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区,佛教从唐代开始就深刻影响那里的社会文化和风土民情,到目前为止,相比当地传播的另外三大宗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仍然是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宗教。有佛教信仰就必然有大大小小的寺庙和僧团,据高邮地方志记载,清乾隆以后,高邮地区较大的佛教建筑有:“寺45个、庙67个,庵261个、塔院7个,殿8个、念佛林2个、念佛堂5个、塔4座,寺庙房屋6000余间。”[7]这些建筑多毁于20世纪40年代的战火,在汪曾祺出生的1920年,它们虽然在用途上有所变更,但大多风貌犹存,历史上著名的高邮八大寺[8]中的绝大部分在那个时期还较好地保存着。随着当地寺庙的发展,僧人数量也逐渐增多。“民国20年(1931年),高邮县成立佛教协会,铁桥[9]任理事长……民国36年,高邮计有僧尼918人”,之后仍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但绝大多数信众对佛教的接受局限于“只知教规而鲜知教理,对宗教的信仰与对鬼神的迷信往往混淆在一起。真正因思索人生,探寻历史,到宗教中寻找真善美,而皈依神灵者极少”[10]。从地方志的记载和统计来看,这些寺庙空间与僧尼形象在高邮地区随处可见。汪曾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寺庙林立的地方,僧尼也自然成为家庭日常交往的对象,这构成了其家乡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
出生在高邮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汪曾祺,与寺庙和僧尼必然会产生一些联系。在他出生时,按照当地风俗,若在寺庙或道观里给孩子记名,便可得到神佛护佑,鬼怪不敢近身,可起到消灾祈福的作用。由于汪曾祺出生时汪家没有后代,且他是三房长子,故格外受到家人宠爱,因此他父亲不仅给他在寺庙里记名,还取了法名“海鳌”。另外,“他的父亲为了慎重,特别在书房中用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梅红纸端端正正写上‘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两边各有一个字,一边是‘皈’,一边是‘依’。‘皈’字比较生僻,一般孩子不认识,但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还没上小学就认识这个‘皈’字了”[11]。这大概是汪曾祺第一次和佛教文化发生关系,但这除了使他获得一个用以庇佑人生的法名和认识了“皈依”这样一个词汇外,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额外的影响。

在汪曾祺的家庭成员中,祖母因为祖父的大病而吃长斋,也会给幼年的他唱“观音老母站桥头”的“偈”,但他不过是把它当作“歌”或“古话”来听而已。汪曾祺早年接触到佛教经文大约是在他继母张氏的诵念中。继母张氏在汪曾祺五岁时来到汪家,她识字,念过《女儿经》,“她有时也念《金刚经》《心经》《高王经》,这都是为她的姑妈念的,她忘不了姑妈对她的领养之恩”[12]。从小伺候汪曾祺的“大莲姐姐”也是信佛的,可能还受过戒。待汪曾祺长大后,她就住在庵里成了一个“道婆子”[13]。由此可见,无论是继母出于情感动因而诵经,还是“大莲姐姐”带有泛神化色彩的认知方式,其实都处于“鲜知教理”的民间信仰层面。汪曾祺也的确从小就接触过一些和尚,因为每逢家里做法事,他就被叫去磕头,之后陪同喝粥、吃挂面。除去这些,汪曾祺早年似乎并没有接受过任何佛教教育,而家学对他的熏陶更多是在其他方面。祖父汪嘉勋和父亲汪菊生都很注重对后代的文化教育,虽然汪曾祺弄不清祖父的“思想”。他曾回忆:“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14]但汪曾祺也承认,作为“杂家”的祖父的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祖父教汪曾祺写字、读书、写文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所读大多是《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并做过若干篇“义”,如《孟子反不伐义》等。而父亲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则是在作画方面。即使汪曾祺童年时期有过对佛教的浅显认知,也远远抵不过之后儒家思想、书画中的审美意识对他的影响。
汪曾祺读小学时开始切身体认故乡的寺庙。“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很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15]或许真是因为除却寺庙,高邮地区没有什么名胜风景,所以寺庙就成了孩子玩耍的地方。“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便是这些庙。我们去看佛像。看释迦牟尼,和他两旁的侍者(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还老那么站着,我常为他不平)。看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眉罗汉。看释迦牟尼的背后塑在墙壁上的‘海水观音’。观音站在一个鳌鱼的头上,四周都是卷着漩涡的海水。我没有见过海,却从这一壁泥塑上听到了大海的声音。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16]到了初中时期,汪曾祺来到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学校附近就是高邮县第一大寺善因寺,他经常到寺里游玩。善因寺后来也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表示:“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我读初中时,天天从寺边经过。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几回。”[17]善因寺方丈铁桥和尚和汪曾祺的父亲是关系密切的画友,父亲第二次结婚时,铁桥和尚曾作画送给父亲做贺礼。有研究者指出,“这件事给汪曾祺印象太深了。他觉得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而铁桥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18]。从这些经历来看,汪曾祺和他的家庭走进寺庙或与僧人交际,与信仰关系不大,除做法事外,甚至连民间祈福的想法也很少,那只是高邮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汪曾祺不断强调那些寺庙之于他是“雕塑艺术馆”“美术馆”“公园”,与其说寺庙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的是一个敬顺仰止之地,倒不如说是获取审美意识和休闲放松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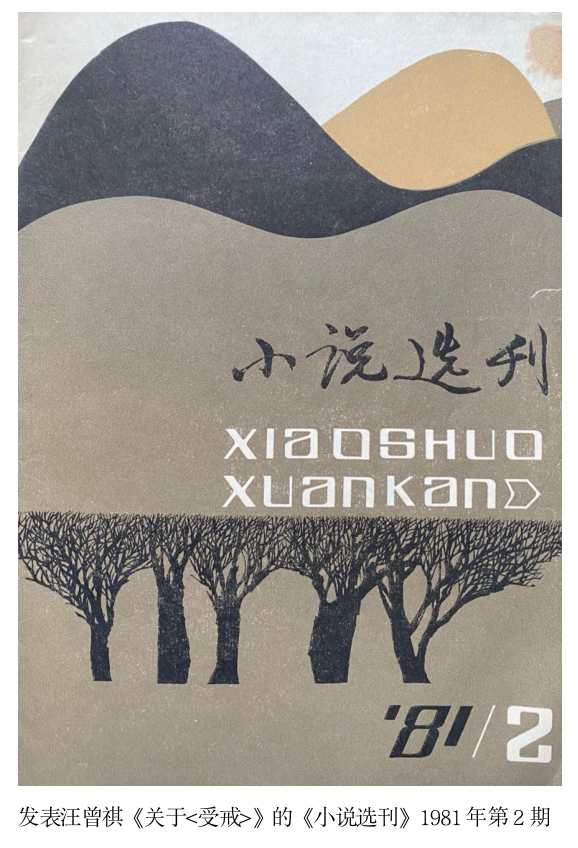

由于抗战的影响,汪曾祺曾随父亲在庵中生活了半年。十七八岁的汪曾祺当时对庵门上“一花一世界”的对联并不理解,而他似乎也没有兴趣弄懂,“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哲学的美。我那时也就是明海那样的年龄,十七八岁,能懂什么呢”[19]。这是汪曾祺一生中有据可考的唯一一次寺庙生活经历。在这段时间,他除了继续观看周遭日常生活的世界,并没有跟随和尚研读经藏,而是一边准备考大学,一边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书对汪曾祺的一生影响深远。1939年,他阔别生活了十九年的故乡高邮,踏上了去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求学之路,同时有幸投身沈从文门下,开启了一生的文学生涯。
离开到处都是大小寺庙的高邮后,汪曾祺几乎再没有近距离体验寺庙生活的契机,纵观他此后的经历,也无文献显示他对佛教思想有深入探究,而他晚年为《世界历史名人画传》中“释迦牟尼”卷撰稿的前因后果,恰恰可以用来说明汪曾祺其实受佛教文化影响不大。汪曾祺在1991年1月28日写给友人黄裳的信中谈及此事:“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20]可见,汪曾祺被要求为《世界历史名人画传》撰稿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曾写过和尚,而正是被迫要写这样一本书,他才开始真正学习佛学知识,而此时汪曾祺的寺庙题材小说皆已完成。由此看来,那些因《受戒》等小说而认为汪曾祺当过和尚或具有深厚佛学造诣的猜想,似乎真的是一个误解。
二、 “日常”书写与情绪的“缓释”
了解了汪曾祺的家学传承、成长经历以及他与高邮众多寺庙之间的关系后,我们的确很难在其思想中梳理出一个所谓的“宗教观”,再结合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一个人如果相信禅宗佛学,那他就出家当和尚去得了,不必当作家”[21]的说法,不难推测,汪曾祺受到的佛教文化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但在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寺庙是当地日常生活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庵中避难的半年,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乡的原初经验通常会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当汪曾祺以文字的方式召唤旧梦时,寺庙成为其小说的叙事空间就不足为奇了。
汪曾祺书写寺庙生活,其实就是在描写高邮人的日常。他曾表示:“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从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22]这几乎可以看作80年代初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缘起。而据此推衍,“四十三年前”刚好是1937年,当时汪曾祺17岁,上半年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他终生难忘的初恋[23]。暑假后,日军占领江阴,他就随祖父、父亲在庵里避难。为此,汪曾祺晚年还追悼、感怀那段时光:“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繖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24]而接下来的避难生活,让他发现在寺庙林立的故乡,“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25]。于是,他用自己初恋时“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26],虚构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纯洁、健康的感情。作家从记忆中选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然后开始描写他所观察到的寺庙生活。因此,汪曾祺笔下的寺庙空间和相关人物几乎都可以找到原型,他曾坦言:“《受戒》所写的荸荠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们的法名是我给他们另起的),他们打牌、杀猪,都是有的。”[27]“庵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明海是没有的。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则是我亲眼得见。”[28]“和尚怎么还可以娶个老婆带到庙里去。小和尚还管她叫十(师)娘,和尚赌钱打牌,过年的时候还在大殿上杀猪,这都是真的,我就在这小庙里住了半年,小英子还当过我弟弟的保姆。”[29]由此可见,汪曾祺几乎是按照当时高邮地区寺庙生活的普遍情况塑造了小说所讲述的空间,与其说他在有意消解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对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30]的如实描写。因此,汪曾祺这样回应批评界在《受戒》发表后提出的意见:“有很多人说我是冲破宗教,我没这意思。和尚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戒律,本来就很解放。很简单,做和尚是寻找一个职业。”[31]
汪曾祺小说中的寺庙空间与和尚形象的确都不存在清规戒律和宗教观念,而出家在作家笔下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庙与僧》《受戒》和《仁慧》是处理寺庙空间最多的三篇小说,若从寺庙场域、人物活动和运作机制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对寺庙形态的塑造,会发现它们的世俗特征极为鲜明。在《庙与僧》中,婚房里常见的雕花木床占据了房间一半的空间,一大块咸肉挂在梁上,很少有人做佛事,通常只有三尊佛像冷清清坐在那里;和尚们不仅吹水烟袋、杀猪、唱百种时调小曲,还可与师母同住。《受戒》中的荸荠庵也不成规模,和尚不做早晚课,经常打牌,有家眷,吃肉,清规戒律无人提起。《仁慧》中的寺庙破败不堪,一副败落景象:尼姑不大守本分,办斋、用酒,也放焰口,办素菜馆。由此不难看出,汪曾祺笔下的寺庙皆不成规模,甚至有些破败,形态上大多僧俗结合。处于其中的僧尼除在一些特殊时间举行佛事活动外,可以杀猪、喝酒、吃肉,实际上与俗家生活别无二致。而在运作机制上或自由散漫、摒弃戒律,或模仿俗家的家庭结构及生存方式。与其说汪曾祺小说中的寺庙空间蕴含着宗教神圣性,不如说它们只是另一个场域下的世俗家庭。而对出家人来说,如同《受戒》中的明海一样,“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因为“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32]。将和尚与劁猪的、织席子的、箍桶的甚至“婊子”并列,意味着出家只是职业选择之一种,与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的职业没有本质区别。明海之所以出家,是因为家里田少不够种,就派最小的儿子去当和尚。他受戒是因为只有受了戒才可以云游挂褡,不是野和尚。明海的出家与受戒似乎都与行为本身的神圣性相去甚远,因此他与小英子之间质朴的爱情也就有了可能,读者显然不能用“破戒”对小和尚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在《仁慧》中,仁慧当家以后,不在意任何人的评论与反对,办素斋,请男客,用酒,放焰口,在一个没有戒律的寺庙里,这些行为都合情合理。仁慧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任何谣言一笑置之,自由自在云游四海,一切显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在这样的寺庙空间中,宗教与任何世俗性的职业、行为并无任何冲突。
无论从汪曾祺的自述看,还是从相关历史文献看,小说所写的的确是那个时期高邮地区的真实状况。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倾向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的寺庙中就已经出现未纳入崇拜体系的民间伎乐表演。在寺庙的造像上,有些寺庙将四大天王比附成“魔家四将”,把金刚力士称为“哼哈二将”,这显然是受到小说《封神演义》的影响。晚清太平天国运动逢寺必毁,这些寺庙后来虽有所修缮,但大多仍处于破败状态。此外,寺庙再造的过程也没有将世俗与神圣严格区别开来,“中国寺庙似乎总在力图缩小与世俗社会的差距,总在尽量地消侵宗教的压力,总在尽量地为其信众营造一个富有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的空间”[33]。在《一九三○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一文中,法舫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作为布教之所的大小寺庙,“如今俱失去了布教性质,变为一种家族式的私人庵堂”[34]。可见,当时的寺庙无论在外观与内设上,还是运行机制与活动范畴上,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都渐渐模糊,但这并不能代表当时寺庙的全部情况。其实汪曾祺本人就曾结识过不同类型的和尚,如他小时候就见过戒行严苦、自号“八指头陀”[35]的老和尚;也认识庙里的方丈——衣履讲究、谈吐不凡的阔和尚(如与汪曾祺父亲交往的铁桥和尚);还在家里做法事的时候认识了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和尚等。但在小说中,汪曾祺选取的并非戒律森严的寺庙空间,而是由阔和尚、职业和尚组成的世俗气息更浓厚的僧团及场域。这表明作家在追忆四十三年前旧梦时,有其在现实基础上的主动选择。
汪曾祺在谈到《受戒》时特别指出:“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36]其实不只是《受戒》,他在80年代创作的那些和几十年前故乡有关的作品,都是中国人情感的总和。寺庙不仅是一种宗教建筑形式,作为重要的敬顺仰止之地,同时也象征着某种神圣话语。统治者往往利用寺庙空间的转喻意义,将权力合法化。传说元末张士诚向承天寺的大梁射了三箭就登基建立了政权,高邮地方志也的确记载张士诚将府邸设置在承天寺[37],其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借助寺庙的神圣空间建构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寺庙空间常常作为败迹淫行的事发地。如《红旗谱》中地主恶霸冯兰池砸掉古钟欺压百姓的恶行就发生在河神庙,《林海雪原》里一撮毛的藏身之地是神河庙,《白毛女》中恶霸地主黄世仁奸污喜儿的地点也是在佛堂。如果说以寺庙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是深入到民间意识形态之中的正义和良善,被安置在寺庙中的罪行就是站在正义和良善对立面的邪恶,这种邪恶需要革命的力量来铲除。在这样的书写中,革命与宗教都处在与邪恶相对的结构位置上,使得前者也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神圣和崇高。可见,寺庙空间的神圣性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存在的,而对寺庙世俗化的书写就隐喻了意识形态的松动。因此,汪曾祺没有选择那些戒行严苦的寺庙作为笔下故事发生的空间,而是注意到世俗化的寺庙形态与人性中被压抑的情感。正如他在与施淑青的对话中所言,“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38]。在《受戒》等一系列以寺庙为叙事空间的作品中,他用人性的宽容观看僧尼的七情六欲和情感表达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上一个历史阶段遗留给读者的紧张情绪,以及个人情感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三、 相关评论的再反思
在汪曾祺以寺庙为场域的小说中,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当戒律根本没有人提起时,不仅所谓“出家”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受戒”也丧失了其应有的神圣含义。这或许正是汪曾祺不断强调《受戒》这篇小说完全没有冲破宗教的原因,他要表达的其实不过是美和健康的人性。
即便没有冲破宗教的意思,寺庙生活的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在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上,有一篇“战战兢兢”的《编余漫话》,编辑不止一次提到“题材”问题,表示“题材在转换,就是在这期小说专号上,也是看得清楚的”,之后又说“本期作品在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上,表现得比较显著”[39]。然而有些评论者还是大发感慨,“《受戒》的题材也真奇特(至少在现时社会是这样)。小说中的人物,一不是什么英雄,二不是工农兵,竟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和尚。没有写这些和尚由唯心有神论者转变为唯物无神论者,由膜拜释迦牟尼转变为信仰马克思,更没有写和尚们搞什么其乐无穷的斗争(总之没有写革命),却偏偏写他们平平常常的生活起居,叙述他们如何烧香念佛,甚至写他们如何不守佛规和女人搞恋爱”[40]。此外,因为这篇小说独特的题材,也促使评论者开始考辨汪曾祺小说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唐挚把这篇小说看作是“宣扬无神论的檄文”[41];可人则认为《受戒》表明迷信宗教和戒法的时代已经走向了末路[42];而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受戒》情节怪诞,有违生活的客观真实,“实际上起着粉饰美化佛门生活的作用”[43]。虽然汪曾祺并没有体系化的宗教观,但《受戒》毕竟涉及宗教题材,在当时的语境中,写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如前文所述,50—70年代的革命叙述一方面借助宗教修辞建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从无神论的角度取消了宗教的神圣性。那些庙宇佛堂,实际上很难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空间,而是混同了民间信仰与伦理,并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所向往的正义与良善。它们散落在文本的边缘处,甚至与寺庙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被革命历史叙述压抑了。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在80年代初期让寺庙以及与之有关的生活再度浮出地表,显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而一旦触及这个命题,政治化的思维很快就让人们嗅到了“旧时代”的味道。于是就有了诸如“大家知道,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为了愚弄和毒化人们,它不但有满篇骗人的教义,而且还有一套束缚其信徒的戒律清规”[44]这样的论调。这些评论者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小说中的健康人性,就先抓住故事发生的空间大做文章:“也很难想象,在神权施威的旧中国,一个佛教徒可以无所顾忌,无所羁绊地和一个农村姑娘自由恋爱……问题的关键是小说根本回避了有戒律存在的客观现实,因为实际上起着粉饰美化佛门生活的作用。”[45]显然,评论者把佛教看作戕害心灵的毒药,而评价小说好坏的标准之一,是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控诉佛教对人性的束缚。这些早期评论虽然没有明确探讨汪曾祺小说创作和佛教之间的关联,但当他们做出如此评价时,一个预设的前提是: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隐含着自己的宗教观。然而,他们忽略了作家本无意颂扬或批判宗教,而是把30年代的日常生活在80年代重新召唤到文学中来。遗憾的是,一些熟悉“十七年”文学创作与批评模式的评论家,是无法辨认和接受这种日常生活的。
或许正是因为汪曾祺在80年代以后不断碰触这一题材,才使人们渐渐形成他与佛教有关的“前见”。作家在美国发表演讲时就曾提到,“在国内有十几个人问过我,当过和尚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受戒》(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读过《受戒》)”[46]。陈平原编的《漫说文化》丛书中的《佛佛道道》(1990),就收入了汪曾祺的小说《幽冥钟》。陈平原还在《导读》中指出,汪曾祺笔下的“钟声似乎沟通了人间与地狱、实在与虚无、安生与超越,比起有字的经书来更有感召力”[47]。这似乎坐实了汪曾祺与佛教义理之间的深刻联结。此外,汪曾祺对台湾有人将他的小说《复仇》当作佛教小说感到非常不解,“台湾佛光出版社把这篇小说选入《佛教小说选》,我起初很纳闷。去年读了一点佛经,发现我写这篇小说是不是很自觉地受了佛教的‘冤亲平等’思想的影响的”[48]。事实是,汪曾祺在写这篇小说时,无意碰触有关佛教的命题,他只是有感于1944年前后的社会现实,以寓言的方式折射出当时的现实生活,并对人类寄托了自己的希望而已。
90年代前后,评论者开始在审美的层面阐释汪曾祺小说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作品一以贯之的和谐状态与禅宗圆融无碍精神的相得益彰。这一评价方向的出现,和80年代中后期汪曾祺的《受戒》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缘起、学界对其中传统哲学意识的挖掘不无关联。1989年,杨剑龙明确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汪曾祺的内心深处积淀着浓郁的庄禅意识[49];1995年,林江、石杰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中论述了儒道佛的共同影响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50];1999年,和汪曾祺有着密切交往的金实秋发表《佛教与汪曾祺作品》一文,认为佛教文化为汪曾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思想,并有意昭示作家人生经历和佛教之间的关系[51]。这些言论开启了汪曾祺小说评价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此后从佛教的角度探索汪曾祺小说的题材、理念、意境的文章层出不穷[52]。不过正如上文分析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其实并不是来自对佛教义理的深谙,它更可能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谈到父亲对他性格的影响时,汪曾祺也说道:“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53]此外,对儒家“爱人”的理解、恩师沈从文的创作也或多或少地对汪曾祺和谐圆融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影响。
汪曾祺寺庙题材小说的圣俗问题,不仅涉及重新确立寺庙空间意义的历史过程,暗示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精神世界流变的脉络,也让我们重新审视80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的评价问题。虽然每部作品都难免有被读者和评论者误读的命运,但重新梳理作家成长的背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作品。对汪曾祺评价中的圣俗之辩做出有效的清理与反思,也可重估其创作的基本价值和审美特质。而时常有“孤独之感,寂寞之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54]的汪曾祺,其实也曾做过文学批评,他对阿城《棋王》的评价似乎可以看作对批评界误读其作品的回应。汪曾祺说:“有人告诉我,阿城把道家思想揉进了小说。《棋王》里的确有一些道家的话。但那是拣烂纸的老头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王一生的思想,不一定就是阿城的思想。阿城大概是看过一些道家的书。他的思想难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纠在一起……我不希望阿城一头扎进道家里出不来。”[55]汪曾祺赞赏阿城,不是因为他对道家哲学的理解抵达了怎样的高度,而是无论是“吃”还是“下棋”,他面对的都是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就像黄子平所言,“在每一个‘价值失落’因而急需‘价值重建’的年代,人们总是先回到最简朴最老实的价值基线上”[56],这其实也是汪曾祺创作的基本价值和前提。
注释:
[1] 梁清濂:《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受戒〉有感》,《北京日报》1980年12月11日。
[2][41] 唐挚:《赞〈受戒〉》,《文艺报》1980年12月12日。
[3][50] 林江、石杰:《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 相关材料,参见拙作《〈受戒〉的周边》(《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5]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6][16][17][19][22][25][28][36] 汪曾祺:《关于〈受戒〉》,《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
[7][10] 王鹤、杨杰总纂:《高邮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8页,第707页。
[8] 明及清初指天王寺、光孝寺、净土寺、九曜寺、悟空寺、光福寺、护国寺、华严寺;清中叶之后指天王寺、承天寺、放生寺、善因寺、乾明寺、永清寺、镇国寺、净土寺。据统计,在汪曾祺出生的年代,除九曜寺在清初被毁外,其他著名寺庙仍然存在。
[9] 铁桥和尚(1874—1946)曾任善因寺方丈,高邮佛教协会主席,他十岁在三圣庵拜指南和尚出家。铁桥和尚是和汪曾祺父亲过从甚密的画友,汪曾祺小说《受戒》中的石桥和尚即以他为原型,《三圣庵》中也出现了铁桥和尚的形象。
[11][12][18]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0页,第33页。
[13] 汪曾祺在《大莲姐姐》(《作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表示,“我们那里有不少这种道婆子。她们每逢那个庙的香期,就去‘坐经’,——席地坐着,一坐一天。不管什么庙,是庙就‘坐’。东岳庙、城隍庙,本来都是道士住持,她们不管,一屁股坐下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14] 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作家》1992年第4期。
[15][30][53] 汪曾祺:《自报家门》,《作家》1988年第7期。
[20] 转引自黄裳:《也说汪曾祺》,《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页。
[21] 汪曾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自述》,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页。
[23] 参见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21—22页。
[24] 汪曾祺:《我的世界》,《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页。
[26][29][31][38] 汪曾祺、施淑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27] 汪曾祺:《〈孤蒲深处〉自序》,《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2—323页。
[32] 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90页。
[33]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34] 法舫:《一九三○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史专集之七(民国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页。
[35] 八指头陀,曾任中华佛教会第一任会长,是清末著名诗僧。
[37] 参见王鹤、杨杰总纂:《高邮县志》。汪曾祺读小学时,就经常去承天寺看钟,也多次听说过张士诚在此登基的故事,后来他将这些内容写入了小说《幽冥钟》。
[39] 《北京文学》编辑部:《编余漫话》,《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
[40][42] 可人:《戒不掉的五欲六情——读小说〈受戒〉后乱发的议论》,《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
[43][44][45] 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有感》,《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7期。
[46] 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5页。此信息载于汪曾祺在1987年10月20日写给妻子施松卿的家书中,内容为汪曾祺于1987年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驻校”时,在“我为何写作”的讨论会上所作的发言。
[47] 陈平原编:《佛佛道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读第4页。
[48] 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晚翠文谈新编》,第284页。
[49] 杨剑龙:《论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51] 参见金实秋:《佛教与汪曾祺作品》,《出版广角》1999年第1期。
[52] 1998年以后,以佛教文化意识、儒道佛思想交融角度探讨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成果层出不穷,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谭桂林《佛教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创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认为汪曾祺的《受戒》通过描写佛教人物生平经历表现人性与佛性的冲突、融合的主题;樊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佛家精神》(《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认为汪曾祺阐释了佛家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世俗化、民间化的佛家精神等。
[54] 金实秋:《禅风禅韵——汪曾祺佛教机缘漫议》,《补说汪曾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0页。
[55]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56]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
- 在汪曾祺看来,太次的茶叶只能煮茶叶蛋[2022-02-10]
- 汪曾祺小说的反讽艺术[2022-02-07]
- 汪曾祺:“人间送小温”[2022-01-27]
- 汪曾祺的懊悔[2022-01-12]
- 汪曾祺:你们都对我好点啊,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2022-01-10]
- 王彬彬: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2022-01-05]
- 汪曾祺笔下的“食相”与“吃相”[2022-01-04]
- 水流云在——汪曾祺的昆明情结[2021-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