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能够在真诚的直言中言说,是我期待的批评愿景

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江苏紫金文艺英才,南京申创世界“文学之都”特聘专家。曾任《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任《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历史是精神的蒙难》等,编辑出版《韩东研究资料》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紫金文艺评论奖等各类文学奖项二十余项。
记者:读你的批评文章,在欣赏你的学识、素养和见解的同时,更加深切感受到的是你批判的激情、真诚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我觉得当下很多做批评文章的人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所以特别想问问你,在你看来,批评何为?你当初是怎样走上批评之路的,这些年回头看,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何同彬:从事文学批评,一方面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南京浓厚的文学氛围有关,尤其是2003年左右,经由朋友的引介接触到很多南京“民间”的诗人、艺术家,真正从学院进入了生动、鲜活、多元、异质的文学现场,唤醒或者说是启发了我内心中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同时,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接触到的鲁迅、尼采、阿伦特、卡夫卡、加缪、佩索阿等一批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作品、学说,又把我对文学的兴趣引导到更加强调自由属性、公共性关怀的“泛政治化”的方向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艺术的私人性先天的那种不足:把主体“抛回到……轻飘飘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当中,再次脱离‘现实世界’”,有一种“悲哀的不透明性”(阿伦特),这种情况下批评何为,或者批评的功能是什么呢?也许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强调的到“私人与公共相遇之处”去建构一个“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治,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以此观念为起点,我写了不少相关的文章(包括相关访谈),如《重建青年性》《批评的敌意》《“公共性”与启蒙文学的困局》《“寻找政治”与永恒的批判》等等。但随着我后来的工作重心越来越接近文学现场,越来越融合进某种文学秩序,这样一种批评愿景就越来越渺茫,一度陷溺于某种批评失语或失范的尴尬处境之中。严格意义上,我现在也还没走出这样的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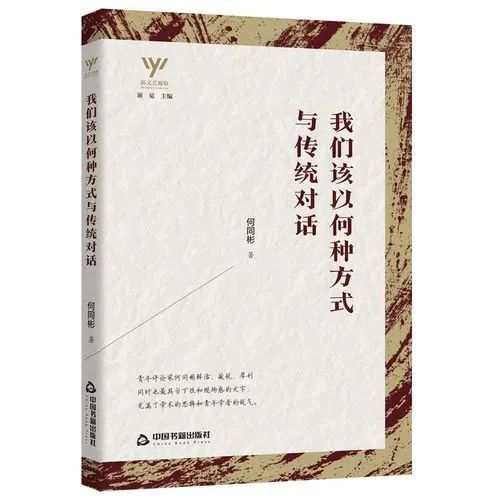
记者:如果批评文章能抵达“私人与公共相遇之处”,可想而知会引发读者更多的共鸣。只是目之所及,很少有批评文章能做到这一点,反倒是更多自说自话,那文章写给谁看,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不时听作家朋友说,他们基本不看批评文章。至于读者么,就我听到的反馈意见,他们似乎也不怎么看。那批评文章难道只是给各种文学奖评奖作参考,或者为各式作品经典化做准备?这个问题还关系到批评的有效性,虽然这所谓有效性,不只是关系到受众多少,但如果一篇批评文章写出来,要是没什么人看,那有效性也自然就大打折扣。你怎么看?如果批评文章也有理想读者,那你觉得怎样的读者才算是理想读者?
何同彬:近些年因为职业原因,中国当代学者、评论家的批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基本是被动阅读,主动阅读也有,相对比较少(国外的批评文章主动阅读的比例反而高一些),往往是因为关注一些话题,需要了解同行们的研究现状,或者是基于对为数不多的比较靠谱的批评家的信任而去专门阅读。我很理解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是作家朋友基本不看批评文章,其实经常看才奇怪。我十来年前曾经反复说过一句颇易得罪人的话:一个人过了四十岁或四十五岁还经常阅读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含文学批评)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不包括那些因职业原因而做出的被动阅读。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几乎没什么价值,年初周明全兄在一个访谈中关于文学批评的现状问过我的看法,我说得很直接,也不无偏激。我们的文学批评的从业门槛太低了,充斥着太多似是而非、颠三倒四、左右逢源的假话、废话、套话,斯坦纳说得一点都没错:“这个世纪从事人文领域研究的人都习惯于夸夸其谈,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在数学或大部分科学领域,吹牛皮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没法蒙混过关。”包括我自己的文章,我也不觉得有多少价值值得读者们认真对待,所以也就不奢望什么“理想读者”,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预想,那我觉得大家能够在真诚、真实的直言中言说、沟通、争论,是一个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批评共同体或者文学共同体的愿景。
记者:倒也是,前提是大家相互之间得有言说、沟通与争论,这在当下似乎有所欠缺,至少我自己做得很不够,要不是这次读你的文章,我其实不怎么了解你写了什么,更不知道你写过不少诗评,早年还写了一些诗歌。不过近些年来,你倒是批评小说多一些。说来诗歌和小说虽然同在文学屋檐下,却也有着不少区别。你该是深有感触的吧,有过做诗歌批评的经验,会否对做小说批评有影响?
何同彬:和诗歌结缘也很偶然,主要是因为在南京最初接触到并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那一批民间的文学朋友,以诗人居多,比如黄梵、育邦、马铃薯兄弟、张羊羊、夏夜清、苏省等,包括后来慢慢熟悉起来的韩东、朱朱、胡弦、刘立杆等。而且我后来也参与了很多民间的诗歌活动,包括责编民刊《南京评论》、参与“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和“柔刚诗歌奖”等活动,就这样慢慢被我的那些朋友、文学兄长们带到了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方向上了。小平兄肯定了解,中国当代民刊绝大多数都是诗歌民刊,所以文学的民间力量也多以诗人为主,这就天然地造就了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文体作家的那种异质性和反叛性,这些品质对那个时期的我非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我的文学观念的生成、塑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对于我的批评语言的影响也毋庸置疑,这一点黄梵兄多次提及,但我自己倒是“不敢承认”,主要是我的诗歌才华极其有限,以至于始终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
记者:谦虚了。你的有些文章,我还真就当专业的诗歌评论读,其中也颇能见出你的诗人气质。要当真说不“合格”,就是觉得你写得少了,如果你发我的“资料”,已经包含了你历年写的大部分批评文章,那数量确实不怎么可观。想来你做批评,一直秉持少而精的态度。这一点,真是难得。如今,批评家们为刷存在感、扩大话语权与提升影响力计,都会多写写,何况应对各种约请,也由不得他们不多写。你反其道而行之,近些年倒是写得少了,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如果有焦虑,会怎么缓解?我大约能想到,你身为《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也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发挥批评的效用。那你怎么平衡编刊物和做批评的关系?
何同彬:“少”是真的少,“精”其实谈不上,我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评论家,主要就是不够勤奋。我的师长和朋友其实也经常提醒我要多写。懒惰的正面价值曾经被罗兰·巴特命名为“被低估的一种能力”,因此他鼓励“敢于懒惰”;我也从布朗肖的话那里为自己的怠惰找到了恰当的借口:“‘乐观主义者书写得很糟糕。’ (瓦莱里)但是悲观主义者不书写。”某一类“勤奋的人”对一个糟糕的世界负有更多的责任,但是,反过来说也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糟糕的世界想要变好,只能依赖另一些勤奋的人,而不是所谓清醒而懒惰的虚无主义者。所以,我也会焦虑,焦虑于没能去写那些应该写的文章,同样,不能免俗的是,也焦虑于不写或少写对于我的批评家身份、职业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至于所有的这些困惑或焦虑,是否跟我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的这份职业有关,我想还是尽量做出必要的区分、区隔是最好的方法,也即各行其是,不要互相干扰。
记者: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一般说来,我们会比较关注同时代人的写作,体现在你身上,亦即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你的批评文章里,着实有《重建青年性》等几篇“青年写作”专论。即使不是专论,你也时不时会涉及这个话题,何况你还策划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活动。我真是觉得你为这个问题“操碎了心”。既如此,与其问你怎么看当下青年写作,不如问问你,在有关“青年写作”的众说纷纭中,你可否注意到什么缺失?你认为其中是否有需要警醒的地方?
何同彬:对于一个过于热闹的文学话题而言,“缺失”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导向很多误区或者悖反,我自己关于青年写作的一些说法,如今再回看也不无武断、轻佻甚至哗众取宠之处。青年群体、青年写作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仅凭我有限的视野、了解和感知,就信誓旦旦地下那么多看起来“掷地有声”的质疑和批判,无论如何都是有些鲁莽和草率的。倒不是说青年作家、青年写作不能被批判、批评(就目前的趋势和状况来说其实是越来越恶化的),而是这种谈论的方式(包括姿态、话语和结论)是不是在回避某些更关键的症结、忽视了很多更重要的问题?今年六月底,我们刊物做了一个“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的工作坊,当时我为工作坊拟定的主题提要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青年热”、过度的“青年关注”、“青年性”的话语区隔以及把青年过分“问题化”本身存在的误区;即文坛、文学场域、文学体制、评论界,若干年来对青年作家、青年写作逐渐形成的一种关注、扶持、赞美/批评的话语机制也亟需认真反思。从明年第一期开始我们专设研究专辑,讨论相关问题,希望能够给文学界、批评界提供一点启发或者你所说的“警醒”。
记者:期待。我想所谓的“青年热”,也包含了你和明全兄在对谈中谈到的“媚少”现象。近些年,文学界不遗余力推介青年作家,这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理当给他们多一些成长空间嘛。但我有时翻到他们的一些作品也疑惑,杂志社或出版社是不是把标准放宽了。读相关评论文章也是,虽然批评家们在谈青年写作群体时会指出一些问题,但具体到某位青年作家,某部作品,也多是夸赞。有时我就感慨,要是能切实结合他们的写作谈谈“问题与方法”,该有多好。
何同彬:在最近与明全的对谈中,我们也再次谈到“媚少”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媚少”的根源是“媚老”,隐含着某种自上而下的引诱和规训,无非是利益、权力的传递,最终达成的是“老少咸宜”、皆大欢喜,或者说“老”即是曾经的“少”,“少”即是未来的“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就不会觉得代际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大、有多么重要了。如果一定要在“老”和“少”之间选择一个“媚”的话,那无疑只能是青年了。我完全认同鲁迅的话,也和他一样相信进化论,“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或者借用钱理群老师的说法,换成一种“无奈”的语气:“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所以,我们可以把“媚少”置换为一种更中性的说法:相信年轻人,相信青年作家。对我而言,这种相信不是强迫的,或者是无奈的、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我在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包括某些青年作家)身上看到了某种与生俱来、难以动摇的“裂隙”,一种无法被整合的、“冷漠”的分离性力量,包括他们愈发开阔的视野和知识背景,这两者的结合会在未来衍变为某种极其正面的能量和价值。
记者:这倒是个值得珍视的现象。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关注到了当下青年写作中的“异时代”性。你在《直言、逃兵与批评的“异时代”性》里,就倡言批评得有“异时代”性。你还说:“恰当地、正确地讨论文学、写作文学,目前已经堕落为一种非常恶俗的能力和习惯。”那不妨说说,在你看来,我们做批评怎样不至于“堕落为”做演员?是否保有“异时代”性,是必要的前提?
何同彬:其实在那篇文章中我已经大体做了一些“回答”。避免做一个文学“演员”、一个“做戏的虚无党”,首要的品质就是坚持“直言”,要逾越狭窄封闭的文学观念的边界,拒绝重复性地遵循“堕落风格的公式”,用“直言”性的批评去直面“毁灭”或向更深的毁灭坠落的文学整体与文学现实。我们(的文学)需要说出一些“秘密”,这些“秘密”能够始终成为“秘密”,本身就是一桩丑闻。直言的目的就是说出这些伪造的“秘密”,而直言性的批评也是要揭穿“演员”们对文学自足、自洽,文学本位或“纯文学”的那种看似正确、实则荒诞的拥护。倘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直言者”,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在我们的批评生活中成为一个“逃兵”:“逃兵是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他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他对事物的视觉经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它使他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使他远离人类。”(米兰·昆德拉)以上的观点我已经表达过多次,多到我自己都开始“生厌”,因为我自己就越来越难践行,反复强调并说出这些话就难免显得是一个虚伪的文学“演员”。
记者:要不怎么说做“直言者”难呢,难就难在与批评对象“同时代”,难以拉开距离。所以说无论写作,还是批评,需要多一点未来的维度,历史的维度。不过你对“历史”性,或者说也是“历史”化是有保留的。譬如,在《“历史是精神的蒙难”——对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思考》里,你就对文学史思维,以及文学史形成的过度历史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可能比较孤陋寡闻,虽然以前也做过重写文学史之类的话题,却是第一次从你这里读到“文学史思维”这个提法。怎么说呢,文学史家们,包括做着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人们,是应该有一点文学史思维的吧,但作家们大概也是有的,甚至更为强烈,虽然他们很少坦承这一点,但有雄心和抱负的作家,往往都有进入文学史的强烈愿望。这种“文学史思维”,对他们的写作,会产生怎样潜在的影响,是值得加以讨论的。
何同彬:历史感、历史思维肯定是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经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历史冗余的堆砌,那种被尼采讥讽、批判的“历史学热病”,这在他的《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已经阐释得很清楚。苏珊•桑塔格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智性、艺术或道德活动都为历史化这一意识掠夺性地占有。……一百多年来,历史化观点一直占据着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许它一度不过是意识的边缘抽搐,现在却变成一种巨大而无从控制的姿态——一种让人类得以不断保护自己的姿态。”这和海登·怀特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认为当代文学的基本信念和现代艺术的独特目的就是“历史意识必须抹去”,甚至宣称要把历史从一级学科中排除。我们的很多作家就是困守在历史中,或者自愿陷溺于某种历史范畴提供的庇护或者安全性中,故步自封又“名利双收”,根本没有任何冒险意识、创新的动力和创造性的可能。很多的评论文章和研究文章也是习惯于“从头谈起”,堆砌大量无用的文学史知识、理论知识,文本臃肿、观念陈腐。所以,我的那些批评是有针对性的,并非一概而论。
记者:看你这般个性鲜明,如果有人写你的印象记,该是相当有料的。果然读到了黄梵早年写你的《批评的杀手》。他说,你身体里除了靡菲斯特,还藏着一个薇依。他还说,你用那惯有的讽刺语调,竭力唤醒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批评正义。以我看,当下批评界,“靡菲斯特”罕见,“薇依”少有,“批评正义”也似乎缺了点儿。这三者有其中一样就不容易,你身上居然都有,至少早年是都有的。甚是钦佩你“当年勇”啊,也好奇你以后还将怎样一如既往地“勇”下去?
何同彬:黄梵兄和你的谬赞真的不敢当,如果说过去年轻气盛、无知者无畏的时候还真有几分“莽撞”的孤勇之气和践行批评正义的热情之心,如今几经磨砺和蜕变,也都转化“变质”了。我的学生几年前专门发微信“告诫”我:何老师,你越来越慈祥了……我的年轻同事也经常用“何老师,你又慈祥了”这样的话“揶揄”我某些时候的妥协、乡愿之举。这就是现状,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没有“靡菲斯特”的魔性,也没有“薇依”的神性的庸众之一。当然,作为一个“慈祥”或“假装慈祥”的批评者,我的内心还残存了一点年轻时候的“愤怒”的本能,但也不过是偶尔“露峥嵘”。
- “南京文学与批评的年轮”论坛举行[2022-11-23]
- 何同彬批评印象:永远的“青年”[2022-11-20]
- 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2022-11-20]
- 杨庆祥:“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在互动中完成一种精神探险”[2022-11-11]
- 今日批评家 | 李音:外套旧了,只有破洞是新的[2022-11-08]
- 今日批评家 | 康凌:不写也可以[2022-11-04]
- 重建批评的尊严[2022-11-03]
- 金春平:意义的延续与经典的准备[2022-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