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桃不必拒旧符 ——在《学衡》创刊一百周年之际访张宝明教授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辗转十年后,终因内外交困而停刊。三十年后,有人请《学衡》杂志主编吴宓撰述创刊始末,得其回复:“《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时值《学衡》创刊百年,张宝明教授以《学衡》典存昭示“斯文在兹”(《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重审学衡派的是非得失、思考学衡派的当代启示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华读书报》就此专访了张宝明教授。
中华读书报:您先后主编《新青年》读本多种与《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呈现近代中国两股截然相对的思潮,有着什么样的考量?
张宝明:有两点考量。第一,《学衡》宛如一艘沉潜多年且渐行渐远的“人文集结号”,百年了,是时候打捞了!而且需要我们耐心地打捞与梳理。作为近代中国“人文方舟”的《学衡》,如何评价,我们需要跳出“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传统窠臼。班固《西都赋》有言曰:“方舟并鹜,俯仰极乐。”
第二,很多同仁看到这个编选本后会想:开始转向了?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将《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而且编选过三种不同形式的《新青年》读本。我研究《新青年》的过程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就是《学衡》,它是《新青年》的伴生物。所以,走进《学衡》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曾为《新青年》编选本拟过一句话的宣传语:“不读《新青年》,就难以读懂近代中国。”如果回到《学衡》,完全可以说:“在这里,读懂中国与世界。”《学衡》有很多牵挂,与《学衡》相遇也就有了一层牵挂的牵挂。
就这套书而言,首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约稿。没有倪先生的执著,就没有今天这个“斯文在兹”之“典存”的面世。而就本人而言,做这套书有三个“心动”的因素。一是《学衡》在当年文言文大势已去的背景下,以“舍我其谁”的气魄主动担当起挽大厦于将倾的文化复兴责任,充分彰显了“文不在兹乎”的悲壮,充盈着满满的人文悲情;二是《学衡》以“明其源流”的方式向“与日月同辉的经典致敬”,贯穿着“理解”“认同”“同情”之人文温情;三是《学衡》在“家事国事”的关怀中,更有“天下”“世界”的视野和胸怀,流布出人文承诺的多情。这“三情”合起来看,不能不说《学衡》的文字是20世纪以来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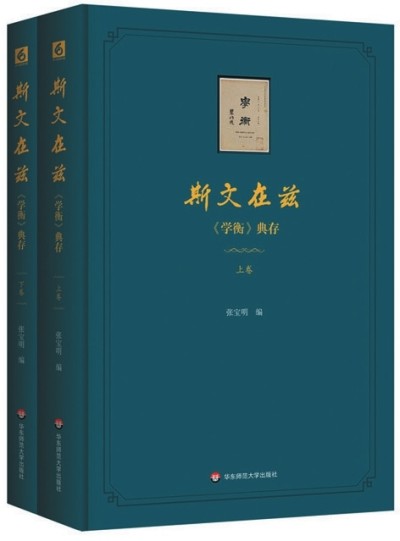
《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张宝明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398.00元
中华读书报:请问您说《学衡》留下的文字可以帮我们“读懂中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什么?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学衡派同样在“睁眼看世界”,却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您觉得该如何理解这一反差?
张宝明: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历史事实,《学衡》的担纲者都是学业有成的海归。他们怀揣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按常理,无论是留学东瀛还是留学欧美,一定是以“他山之石”的心态面对世界,在中西文化的情理中做出伯仲、轩轾的判断。然而,学衡派面对当年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呐喊,始终保持了一份冷静与警惕,不忘守护自家本色。这个本色是不以他者为“喜”,亦不以“己”家为“悲”,而是在喜忧参半、忧乐圆融中建构起中西互鉴、古今汇通的文化通约,他们在保守主义的标签下承载着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开放维新之道。
与新青年派中的“万事不如人”“悔过自新”甚至全盘西化不同,学衡派的内省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呵护文化、维护遗产的自觉特征。固然,新青年派知识同仁也有过“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矫枉必须过正”的自我开脱,但总的文化倾向上却不能不说与《学衡》诸君的文化拣择是格格不入的。就《学衡》的“中正”而言,今天看来,它更为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学衡》所呈现的开放,不是“去中国化”,更不是“全盘西化”。进一步说,即是在不分轩轾、难为伯仲的基础上,打通域界、族界与国界,以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心态渐行渐近。这显然也是一种求真经、悟真道并“止于至善”的文化心态。
顺便说一句,《学衡》与《新青年》在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意识上都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学衡》的自信表现为内敛的、低调的、谦和的自信,具有深沉优容、从容淡定、大气宽容的人文气息。它的自信来源于深层底蕴中的内涵与镶嵌在骨子里的硬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辐射与散发。这里,我们可以称其“有节(制)的自信”。《新青年》的自信则表现为张扬的、高调的、外倾的色彩,时不时流布出激进、超能的积极锐气。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无制(衡)的自信”。归根结底,在学衡派眼中,劝谕人类节制乃是文化的应有之义。
在学衡派看来,从事新文化运动者就是挟西方文化以令国人的典型“自信”者,这一以西方文化为上的新青年派恰恰不是“自信”,而是“他信”。在“信他”还是“信己”这一选项上,学衡派的文化心态呈现的乃是一种厚重、稳健、中正的消极自信。骨子里的自信流布在创刊号的简章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由此而来的文化“怀柔”同样能赢得八方来朝的“远人”格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的就是这一文化景象。
中华读书报:《学衡》以倡导新人文主义为主导,请问新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有什么区别?进而请问,《学衡》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与《新青年》主导的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同?
张宝明:首先,我想纠正一个观点,《学衡》倡导的是人文主义,而非倡导“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名词并没有被学衡派所提及,而是后人在概括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所提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区别。如果硬要作出区别,也可以说是时代价值观念的渗透而已。在本质意义二者还是源流合辙、一脉相承。
事实上,倒是如你所说,值得一提的还是《新青年》与《学衡》因对Humanism的不同理解、译介与倚重而出现的分庭抗礼之思想张力。文言与白话之争其实是这两种思想谱系话语权争夺的外化。新文化运动中,通过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诠释发挥,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成为“Humanism”两大主流译法,而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也依据“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成为“五四”时期并峙的思想双峰。
回到“五四”的历史与文化语境,由于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启蒙意义,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天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拥戴。对人道主义的重点引介,新青年派是从人本身,从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他们对于劳苦大众不幸的同情,重心不是政治与经济,而是源自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的关注。“思想艺文改造”呼唤“人”的到来,与“人的运动”“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等“人”同气相求。一时间,人道主义成为文学革新运动中最为坚挺的主心骨,也是新文学家和思想先驱“言必称”的启蒙工具。
然而,那些为新青年派尊崇的人物在学衡派看来却是一些不安定的灵魂,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分属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实验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人道主义的拼盘。于是,以批判人道主义著称的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在学衡派的推介下登场。白璧德坚守的是一种调和、克制、收敛的规训,反对偏激、过度或极端的做派。学衡派中的吴宓、梅光迪以及后来的新月派作家梁实秋等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其影响, 最终成为其忠实信徒和传播者。吴宓曾对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比较,“人道主义主张兼爱,与人文主义 Humanism 之主张别择而注重修身克己者截然不同”。沿着白璧德的路线,学衡派认可的艺术立身之“古典”“中庸”“自制”,带有一定的“发乎情止乎礼”意味。
中华读书报:记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两个重要学派的差异:“学衡派,为灵魂寻找故乡的仁人;新青年派,为故乡寻找灵魂的志士。”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解读?
张宝明:这个问题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路径依赖与选择问题。新青年派与学衡派都怀有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寻找出路的同气相求之抱负,只是在那个时代救世济民、救亡图存之路应该怎么走,何谓正道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方高歌的是“归家”,一边引吭的是“远方”。换句话说,新青年派是要在打破传统以后的重组,旧派是要在传统基础上的意义寻绎。无论是文化观念的对峙还是文学理论的交锋,都是围绕文化的整合方式进行的。
“打倒”或说“推倒”之后“建设”,这是新青年派惯用的话语,也是他们内在的逻辑。他们认为固有的文化中的大部已经失去保护“吾人”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来一个彻底的觉悟,在换血式的“革命”中寻绎到让我们仰仗的新文化。这个觉悟是“彻底”的,并从中悟出对旧文学、旧文化、旧伦理、旧政治等等一切之“旧”的家当破坏、颠覆的必要性。“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从今以后的“新”方案,乃是科学的、民主的“政治”,科学的、民主的“艺术”,科学的、民主的“文化”,科学的、民主的“文学”。冠以“科学的”“民主的”头衔就可以畅通无阻。“科学的”“民主的”修饰词就让他们要立意的内容焕然一新。而凡是“新”则必然优于“旧”、胜于“旧”。
与新青年派不同,学衡派诸公更乐意从原典上寻绎精神世界的皈依。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份文化的“背景”才厚重,只有这份文化的“定力”才可靠。在“可爱”与“可信”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后者。他们认为四书五经已经成为经得起检验的元典,《诗经》《离骚》等千古流传的文学作品已经深入人心。这些经典乃是文化积淀、深层结构,不是那些随风飘荡的时髦、可爱之流可以比拟。而这一切,又都归结为对文化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信奉,对文学教化育人功能的领悟。
在学衡派,有规训才能对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这里就形成了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差异,也产生了强调责任还是权利的分歧。归根结底,双方在思维方式上,一个是发散、外倾的、“积极的”、高调的;一个是收敛、内倾的、“消极的”、低调的。在前者,个性的张扬、话语的扩张是其根本特征;在后者,自我的规训和内心的自律构成了主体。“学衡派”的收敛、内倾、“消极”不是不要进化,不是反对创造。他们主张创造是在传统意义资源基础上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在“因袭”的平台上发挥,在“摹仿”的前提下创造。当然“因袭”不是“抄袭”,“摹仿”的目的也不是停滞于临摹和仿真,目标还是要推陈出新。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守成战略。
新青年派不能容忍这样的一种不死不活的惰性,他们主张个性的张扬和发散,积极、激进地超越,是要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空前绝后的逻辑上抽刀断水。于是,推翻、推倒、打倒、革命之类的词汇不绝于耳。以西学取代中学,以白话取代文言,以自由体取代格律体,以“她”替代“伊”,“此国人所以混淆迷乱而不能自已者也”。然而,“吾华为数千年礼仪之邦,其间因风俗礼制人伦维系之久长,故节制的、个人的、消极的伦理道德,莫不完备”。这里所谓的“节制的”即是说规训和收敛;所谓“个人的”即是内倾和内化;所谓“消极的”即是谦逊的、低调的,为规避骄嚣、鲁莽而设。在这样一个“莫不完备”的文化面前,我们若不家珍自数,反“舍近求远”岂不是“弃家鸡而爱野鹜者也”。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下,我们看到:当新青年派在白话文凯旋之高歌萦绕于耳之际,也正是低调之学衡派自命清高、“舍身成仁”的悲壮之时。
中华读书报:我们还注意到,您在《斯文在兹》序言中将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纠葛喻为“绅士”对抗“猛士”。历史上,“猛士”们引导了中国的启蒙与革命,“绅士”们的作用又该如何评价?
张宝明:我们知道,《学衡》创刊的1922年已经是白话文大获全胜、《新青年》凯歌劲吹的时代。1921年,经过《新青年》的鼓与呼,民间与官方多年的互济,北洋政府一纸公文将居于“厢房”的白话文移至华夏“堂屋”,史称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借用鲁迅先生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句话来概括新青年派的精神气质。
相对于“猛士”,以守成为基调的学衡派同仁则有一种“明知山有虎”之责任担当。他们冒着“不识时务”之嫌,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笑柄,甚至被看成不自量力、螳臂当车,但在他们温文尔雅的“斯文”背后透露了对华夏文明的坚守。
针对《新青年》诸君看似策略的“矫枉必须过正”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心理,《学衡》同仁有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懑。对文白之争中“不容讨论”的做法、新旧之辩中的“绝无调和之余地”的做派,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他们口诛笔伐。
在《学衡》那里,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调和、折中,倡导“过正”的偏执言行,完全违背了人类文明进程中规约、拣择、中和、谦卑的人文向度。不容讨论、不容调和的下一步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破旧立新思维。立新不必破旧,新的只有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才能推出。因此,当新文化同仁以西方文化作为压倒式价值观来取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时,学衡派同仁告诫他们,正道的人文发展观应该是互助、互鉴、互济,在并行不悖中协力前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多元与多彩的文明不应是谁打倒谁、谁压倒谁、谁消泯谁,“我者”与“他者”、“新”与“旧”共存更为符合并立竞进的文化格局。
中华读书报:《学衡》核心人物吴宓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断言:“《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您认为这在今天得到印证了吗?
张宝明:吴宓先生的断言,隐含着一个问题:只有当历史认知到《新青年》派的不足,重新检讨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学衡》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带给近代史一种张力,其意义在于:要建构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伦理共同体都非一日之功。这种历史张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和《学衡》在很多方面是相互发明、互为补充的。
百年后的今天,重读《学衡》,我想说的是,《学衡》不但不是民主、科学的阻碍者、反对者,相反倒是民主、科学的积极拥趸。在他们保守的名声下,其显示出的开放视野丝毫不亚于《新青年》。就家国情怀和世界胸怀来看,也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们以中国传统的“过犹不及”的维度来丈量着自己前进的脚步而已。
中华读书报: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吴宓先生曾言:“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新旧问题应该说是《新青年》与《学衡》争执最大的焦点所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这一说法的意义?
张宝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在当下。何者为新?何者为旧?这不是一个楚河汉界的问题。新旧可以对峙,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替代。从《诗经》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诗句、孔老先生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联想到从古希腊就开始的箴言“弓”与“箭”的关系,再到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关于“对立造成和谐”的“六弦琴”关系解读,都能佐证这一点:新,不意味进步;旧,不意味落伍。梁实秋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对此,吴芳吉、曹慕管、吴宓都专门撰文予以辨析。他们认为,严格意义上“新文学一词,根本不能成立”。周作人有一个“新旧”说:“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本来就并不需要打上“新”的标签来增值,更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失色,反之亦然。
在学衡派诸君看来,对“吾国文化”中“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的经典视而不见,这无异是文化上的“自残”。舍近求远不如近水楼台,真正的人文之道在中国本土悠长、光辉。在喜新厌旧、厚今薄古成为常态之日,吴宓“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的判断,不能不说是学衡派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
- 汪荣祖:另一种新文化运动[2022-02-14]
- 国史大义、宗纲所在:学衡祭酒柳诒徵的史学精神[2022-02-11]
- 黄克武:严复、林纾与学衡派[2022-02-07]
- 柳门高足景昌极[2022-01-29]
- 刘伯明:理解学衡派的另一线索[2022-01-26]
- 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2022-01-25]
- 《新青年》与“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2022-01-17]
- 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202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