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作家南翔访谈录
本期文艺家:南翔,本名相南翔,1978年就读于江西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8年调入深圳大学,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深圳市作家协会顾问。著有《南方的爱》《当代文学创作新论》《大学轶事》《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叛逆与飞翔》《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绿皮车》《抄家》《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等十余种;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各类作品百余篇;作品在江西、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艺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2018年度优秀作品奖以及第六、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提名等20多个荣誉。作品收入多种文学年度选本,多次为《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短篇小说《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特工》《檀香插》分别登上2012、2013、2015和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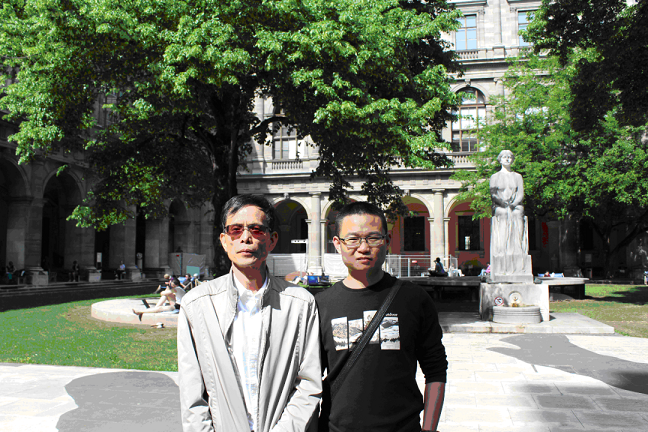
南翔(左一)和欧阳德彬在维也纳大学
欧阳德彬(以下简称欧阳):据我所知,很多作家都是跨界写作,同时涉猎多种文体。您怎么看?您主要写作哪些文体?
南翔(以下简称南):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据我观察,很少有虚构作家不写非虚构的。小说家不写散文、随笔和纪实的很少;反过来的例子倒不太多,纯粹写非虚构、不写小说的情况较多。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一个作家写非虚构写到一定年龄,想转虚构便比较困难。比如说三毛一直写散文,后来想写虚构,可作品中张三、李四怎么想的她自己也不得而知。尽管有人说三毛的散文也有虚构,但是跟小说意义上的虚构并非一回事。后来,三毛又写回了散文。又如北岛、舒婷这些著名的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不大写诗,起码不以写诗为主。他们转型写非虚构,写回忆,国外游历之类,总之是写散文、随笔。当然反例也有,譬如以前写非虚构的作家梁鸿,近几年主要写长篇小说了。小说家大都兼有散文,如王安忆虽然是一位小说家,但也有蛮多散文,内容包括德国故事、美国旅行、驻海外聂华苓写作中心的经历等。
就本人而言,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发表小说,也发表过大量的散文、随笔,后来结了一本集子,叫《叛逆与飞翔》,分了七八个部类,包括阐发篇、缅怀篇、叙事篇、观察篇等。
欧阳:对。我读到的您的第一本书,就是《叛逆与飞翔》。记得当时课堂上,您讲课就多以此书篇章为例文。
南:对,大学课堂有其特点,绝大多数讲非虚构,讲虚构的课堂很少,主要因为大学的写作课时间很短,很多还是作为中学写作的承接。最近有些大学开了创意写作课,甚至将创意写作者作为硕士、博士来培养,聘请有创作成果的作家任教,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创意写作源自欧美,我们国家的大学在“文革”前17年基本不教创作,而且到现在为止,教授写作的大学也寥寥无几。很多人声称,写作是不能教的。前不久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坛,会议结束之后,我与王安忆有一个对话,她也认为大学不培养作家。但我不这么看,大学固然可以不培养作家,但还是要让学生进行虚构写作练习,这一点特别重要。一个学生如果没有虚构写作练习,他可能连欣赏虚构作品都很困难。即使是评论家,我觉得如能做一些虚构写作训练也好,有利于深化自己的评论和理论。
欧阳:我记得您经常将“三个打通”理论挂在嘴边,其中有一条便是“创作与理论的打通”。其他好像是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世界文学打通,课堂与社会打通。
南:是的,必须两条腿走路。纯粹搞创作的作家,也要接触一些理论,创作实践与理论修养相辅相成,才能做出较大成就。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理论思考,譬如有位作家很早就著有《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类的理论著作,他当然引入了一些观点,但也不无自己的吸收与考量。有人认为一个作家最好是创作、理论三七分,最好兼通一点翻译,像鲁迅这样的大家,创作、评论、翻译皆有涉猎。当然反例也有,比如沈从文、汪曾祺,外语都不大好。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全凭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创作,但他和鲁迅同样都是中国文学的高峰。
这里插入讲一下文体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强调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单独有一个奖——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只奖励长篇,不奖励中短篇。一味地求长,我觉得这是俄苏文学的传统。我们在“文革”前17年及“文革”结束之后,虚构作品主要表现为两种文体,一个是短篇小说,一个是中篇小说。各省的作协一直都有文学刊物,“文革”前除《收获》外,还没有什么大型文学刊物,“文革”之后出现《清明》《芙蓉》《花城》《长城》《时代文学》《大家》等大型刊物。早先的省刊都比较薄,可能跟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匹配,所以没有中篇类型。“文革”后各个省突然冒出很多大型文学刊物,中篇小说便兴盛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很多中篇在写法上更像长篇的路数。短篇是单独的门类,不少作家比如一位军旅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在1990年后就不写短篇了。他认为写短篇小说更需要才华,并自认为只是一个资质中偏上的人,觉得写长篇可能更合适。俗一点说,长篇小说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获得“茅奖”,每年都可以重印1万本甚至更多,便可以一直拿版税。加上各地多主导长篇,因此很多作家会去写长篇。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我虽然也写了《没有终点的轨迹》《无处归心》《南方的爱》等几个正儿八经的长篇,还有一些组合式的长篇,像《大学轶事》和《海南的大陆女人》,但大多数是中短篇。其实你看鲁迅和沈从文,被认为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是以短篇写作为主,中篇都很少。沈从文唯一一个长篇还没写完,但他的中短篇小说《边城》等非常棒,包括他的非虚构作品。1989年在《清明》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我向汪曾祺先生请教,问他用写短篇的手法写长篇是否可行。他回答他没写过长篇。当时《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也在旁边,汪老说林斤澜还写过中篇,他连中篇都没有写过。林斤澜小说以怪、险取胜。学者黄子平写过一篇名为《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的论文,专门研究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不太容易看得懂,语言及结构非常奇绝,但是有特点。林老跟汪老是一对哥们、好朋友。一个作家的文体意识还是很重要的,汪曾祺先生就说过他写不了泰山,因为泰山太雄伟了,他的个性难以进入;如果一定要他写,那是小鸡吃绿豆——强努。他在一篇散文《泰山很大》中这样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
《芙蓉》马上刊出的短篇《曹铁匠的小尖刀》,也是生活现实和历史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的例子。一个作家朋友读后,认为小尖刀是一个象征。小尖刀是一把隐形的刀,在里面是显形的,实际上也是把隐形的刀,割痛了你和我,反映走出或坚守农村是对还是错,它是很多矛盾的组合体。
欧阳:相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虚构写作是否需要更多的精力?
南:到了晚年,比如巴金到了晚年主要写《随想录》之类的,写作虚构会比较吃力。当然也有例外,像杨绛百龄之后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洗澡之后》。一直写虚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她的生命力比较旺盛。其实也不能忽略非虚构的重要性,一方面它需要你始终对社会保持一种关切,对时代、对人性有一种了解。现在资讯很发达,电脑、自媒体、手机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传播很快。另一方面有很多隐藏在社会和城市,乃至广大乡村皱褶里的、深含其中的、需要去发掘的东西。只有被发掘出来的东西,你才能有一种亲切感、成就感,有一种发现与发泄的快乐,补充你虚构的不足,同时也体现你对现实的关怀。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它既可以成为非虚构作品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可以补充虚构作品的不足,比如素材知识的不足。
虚构作品最适合表现生活的悖论。虚构和非虚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虚构文学适合展现巨大的空白和张力,非虚构文学把什么都谈透了。小说有很大的留白,但留多少有技巧上的考虑,所以更值得阐发。但非虚构也有它不可抹杀的功能,因为它真实,阅读者多。我的老同学郭春生说,在国外非虚构作品好卖,比如机场书店,非虚构作品卖得很贵,虚构作品反而便宜,这当然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了。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主要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就因它有巨大的想象力充盈其中,人们的理想标高在其中;非虚构类的获奖作家,近年除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还真不多。
欧阳: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处女作发表时有着怎样的心情?经历了怎样的创作过程?
南:实际上从“文革”那会儿就开始创作。1971年底我被招工,1972年初当了铁路工人,还不到17岁。那时候我开始写诗歌,主要发表在铁路局的机关报纸《前线铁道报》副刊上,后来也在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发过一篇短作。《前线铁道报》只是企业内刊,《人民铁道报》才有公开刊号。那些诗歌的名字完全不记得了。那时候普遍看不起短作,就像现在很多人一开始就写中长篇一样,看不起短篇小说,所以当时诗歌写得很长。但当拿到《前线铁道报》时,我发现自己的诗歌被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没几句原话,事先那种期盼、那种自豪、那种喜悦转瞬间化为乌有。因此,我后来编辑文章,要么发回让作者自己改,要么就原样退回。我认为把作品改动太大,不像是人家的原创,作者也没有成就感。为什么说这个经历?因为那时当工人,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上也很苦闷。
1978年,我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工作满五年可以带薪,月薪41元,由原单位宜春火车站支付。这是另一种生活场景了。尽管所有教材还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还有不少油印本。大学二年级我开始写小说,教我们写小说的是卢启元老师,广西人,前几年去世了。他研究冰心,研究四川老作家沙汀。老师课讲得非常好,瘦瘦小小的,从来不发脾气,很温和的一名学者。他布置写作作业时,我交了一篇小说。当时班上100多人,我大概得了85分,全班也就两三个这么高分。受他鼓励,我立即决定去写小说,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短篇小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影响还很大,只要有时间我就跑到图书馆二楼阅览室去借杂志。图书馆什么杂志都订,包括《人民文学》《收获》,也包括省一级的刊物,如安徽的《清明》、江西的《星火》、湖南的《芙蓉》。那时候搞不清杂志是文联办的,还是出版社办的。不了解这些,也没人引导你。教师大都是“文革”劫后余生回来的,几乎没有搞创作的。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会走很多弯路,无人引领就不知道怎么投稿。
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大三时发在《福建文学》的《在一个小站》。责编黄文山后来当到了主编,很多年后开会见到过他,对我来说这种正向刺激是很重要的。大四快毕业时在《清明》发了《第八个副局长》,写的铁路局的事。我住铁路家属宿舍,对铁路生活一直很了解。那时候文学热到什么程度?《第八个副局长》发表后,铁路局的正、副局长都找去看,对号看看是不是有他的影子。其实我写了一个正面的副局长,当时也没有对文学作品无限上纲或者对号入座,更别说文字狱了。
毕业已经是1982年了,写了很多,可以说正式步入文学创作的殿堂,在《清明》《芙蓉》《青春》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家》、公安部的《啄木鸟》都发表过作品。在南昌还当过一段时间《百花洲》杂志的社外编辑。现在一些有一定知名度作家的第一篇稿子就是从我那发出来的,并与作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比如河北保定的专业作家阿宁。我在《百花洲》发过长篇小说《没有终点的轨迹》;后来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为了好卖,责编将标题改成了《相思如梦》,说好卖其实也就万把册。还有《无处归心》,应该都是那个年代出来。较早的一本集子是部分中篇的合集——“海南的大陆人”系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南建省前后,我在海南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生活。结集时因为是自费的书号,为了好卖改成《海南的大陆女人》,其实里面男人女人都有,但女性多。比如《米兰在海南》是位女性,还有其他六七个中篇。有些刊物后来没有了,比如《淘洗》等几篇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型刊物《小说》,《小说月报》头条转载了这个中篇。《米兰在海南》发在哪里我都不大记得了,当年被《中篇小说选刊》头条转载。、
欧阳:后来您离开南昌来了深圳,是怎样的原因和契机让您做出南下的决定呢?
南:大概到了1996年,我就琢磨着要转移地方,觉得再不挪就挪不动了。当时看到韩少功的一些话,一个湖南作家,在人生还能挪动时去了海南。也因为教授职称拿得比较早,三十六七岁就是正高了,省里算是破格的了。在大学毕业后九年之内我把职称全部拿完了,动的心思就更强了。还有一点,1993年我在《深圳法制报》待过一段时间,体验生活。
欧阳:您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又是怎样机缘进了深圳大学?
南:半年左右,800块钱一个月,跟新来的大学生午睡在一起,条件还是很艰苦。我来深圳时,并不想待在法制报,只想进两个单位,一个是深圳大学,第二个就是《深圳特区报》。那时候还没有报业集团这个说法,但是去这两个地方都受阻。当时深圳大学还没有文学院,叫中文系。我去深大求职,有一位叫陈喜书的,后来成了一名后勤干部。他当时只是办事接待,给我打了一个盒饭。我后来说,你对我有一饭之恩。他当时说如果你调入,你就是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了。那时候很少有30多岁的教授。
进深大时面临着档案转移的问题。1996年,我担任江西建省40年以来最大的典型人物——邱娥国事迹的总撰稿及报告文学的主笔。此事缘起于当年我跟西湖区公安分局的一位领导比较熟。他们给我讲起这个人,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给他写了一篇人物通讯发在《江西日报》的周末版上。当时标题取得很大,叫《陋巷丰碑》,后来报纸刊出来压小了一点。他的事迹不断扩展,最后进了人民大会堂讲演,成了一个大典型,被公安部评为一级英模。我在1996年拿到深圳大学的商调函,但是南昌大学(原江西大学)因我担任了邱娥国事迹的撰写工作,不好放行,要我找省领导签字。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最后拖到1998年底才走成。
我很感激章必功校长,1996年他给我发出商调函时,任深大副校长兼深大师范学院院长。人生旅途的关键一步有时候很重要,我在章校长的调动下,来到深圳大学。他是一个很有才也很有人文情怀的校长,广为学生爱戴。到深圳大学后,教学之余,我依旧坚持写作,包括2000年前后出版长篇《南方的爱》,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探索者丛书”系列。每个系列出三本,现在停了。第一个系列我忘了有哪些作家;第二个系列有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长篇;第三个系列一共三个长篇,打头的就是《南方的爱》。
2000年前后,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品《博士点》,发在《中国作家》头条,为《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和刘元举很熟,他当时在《鸭绿江》担任编辑,说我的《博士点》影响很大,连《辽沈晚报》都在连载。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后来写了封信给报社,说连载不但不通知,稿费不给,连样报也不给?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才陆续收到样报与稿费。我倒不是要问责责编,而是要提一下版权的问题,虽然那时候版权意识没这么强。《博士点》获《中国作家》年度奖——大红鹰文学奖,当时获奖的还有毕飞宇的《玉米》、金敬迈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奖金在当时不算低,还得到赞助商提供的一套西装。之后我写了几篇大学系列中篇小说,《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生》《专科生》《成人班》等,六个中篇发在不同的刊物上,最后结集成《大学轶事》。之后还写了一个中篇《博士后》,也发在《中国作家》。
回过去说,其实在南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就是民国题材。90年代,还没有民国热,我写了一系列民国题材中短篇小说,两篇发在《上海文学》,《失落的蟠龙重宝》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发在同一期,还有一个短篇收在《前尘:民国遗事》里。这本集子特别为一些老朋友,尤其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喜欢。他们喜欢那种语言、那种情调、那种遥远的历史回声里的人与事。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个年代时间太短,塑形为一种回望的姿态。那本小说集里的人物与故事,现在还有人在问起,特别是《前尘》的结尾为什么是帮佣的儿子跑到浙江大学来找当年西迁的老师。实际上就是饥荒年代,他在贵州老家饿得没地方吃饭,他爸妈叫他来找当年的雇主。这篇小说留了很大的空白,但也有很大的历史张力在里面,通过人物来写历史。
201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人的葵花》,是《北京文学》发的《女人的葵花》等好些个中篇的结集。《女人的葵花》被北京一个演员买了版权,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拍出来。那个演员把所有转载《女人的葵花》的杂志都找齐了,我告诉他说其实都是一个版本。后来他特意到深圳来见我,寻找该小说的原型发生地龙岗的一个水库。他乘公交一站一站过去看那个水库,真是一个有心人。
这些年我写了更多的短篇,包括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的《老桂家的鱼》、第七届“鲁奖”提名的《回乡》,反响都很大。此时,我的创作大概已经有了三个维度:一个是底层或情感的维度,像《老桂家的鱼》《绿皮车》属于这一类;第二个就是历史或“文革”的维度,大都收在集子《抄家》里;还有一个是生态的维度,比如《哭泣的白鹳》,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珊瑚裸尾鼠》。
近年的写作中,有四篇上了中国小说排行榜:2012的《绿皮车》,2013的《老桂家的鱼》,2015的《特工》,2017的《檀香插》。然后是集子,包括陆续出版的《绿皮车》《抄家》《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面有些内容交叉,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后来我还是把“文革”题材的小说单独放一起出版了,名之《抄家》。中短篇小说集一般不好卖,出版社不大愿意出版,但我这几本小说集都还卖得不错,至少都印了两次。
越到后来写得越少,一年两三个中短篇,不过每次发表转载率都还比较高。2018年《江南》第3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洛杉矶的蓝花楹》,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获2018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2018年第9期刊发短篇小说《疑心》,也包含了对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追问,被《小说选刊》第9期、《小说月报》第10期、《新华文摘》第23期转载。
欧阳:您的好几个小说都获了奖,文学杂志社主办和机关主办的文学奖项,各有侧重,您怎么看?另外,您这几年的中短篇创作很受关注,有哪些新的构想呢?
南:这其实很难区分,因为评委都是交叉的。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奖项由刊物负责,更多从文学性去考量;国家级的奖项权衡各种得失,其中也必然包含政治导向。
就这些年我的写作来看,有三个“打通”:自己的经历跟父兄辈经历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现实和历史打通。比如《回乡》,就是现实和历史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没有那种生活经历很难写出来。我真实的大舅是1940年代末去台湾的,十来岁就走了,到了1980年代末回来省亲。在这篇小说中,各个人物既是虚构,又有生活的影子。还有一篇原发《作家》的中篇《远去的寄生》,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是将自己经历与父兄辈经历打通的题材。我的一个哥哥读初中时遭遇“文革”,下放农村结婚生子,在矿山和工厂都工作过。他们那一代不少人是有思考的。任何时代,不跟风、不从众、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是我最看重的一种品格,何况作家乎!我哥哥属于老三届,他很聪明,但因为家里人多,生活比较困难,父母要他初中毕业以后考中专。初中毕业时要填满八个学校,结果他填了七个中专技校,最后一个填高中,因为成绩太好去了高中。“文革”后,下放农村劳动,30多岁染病去世了,跟积劳太甚有关。我常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活到当下,不知能出多少成果!我们活着的人要珍惜机会,包括延续和光大前人的思考与智慧。
欧阳:您最近写的很多小说,都是不同时代及场景中的小人物,有奋斗也有挣扎。记得《回乡》写到农村一个落魄青年,后来生父返乡给盖了个房子,把自己的所有价值都融在里面,包括自信与自尊,最后又死在房子里。
南:对,最后又终结在其中。还有一些跟生活紧密相关,像《老桂家的鱼》也很值得说,你也去过现场,当时根本没想到写小说。
欧阳:刚去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了解陌生生活的渴望、好奇。
南:上次也说到好奇心!不管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作家,总是要好奇、敏感,对吧?
欧阳:嗯,想了解这些人到底怎么生活。
南:这个过程其实很长。最早赖欢海在那教数学,后来考了我的研究生。他说深圳的疍民没有了,惠州的疍民还在。2003年,我带了几个学生,开着一辆捷达车跟他去。当时疍民的船上鸡鸣狗吠,我们都不敢贸然上去,只有这家向我们招手。他们很热情。有两个细节令我很吃惊:一是没有电,用的是液化气灯,盖着一个罩子,有点像我当年在铁路上的汽灯。二是卧室厨房、船舱客厅连在一起,三代人住在里面。粪便直接排到水里,水很脏不能喝,他们要到岸上去买水,五毛钱一担。我带了一点茶叶给他。之后每年都去,便成了好朋友。有时给他们一些钱,学生给他一些八成新的衣物。这篇小说后来收入《绿皮车》。在北京开《绿皮车》研讨会时,很多专家认为那条鱼是神来之笔—为何会跳到上面?那是一条翘嘴巴鱼,有着鲜红的玛丽莲·梦露般的嘴唇,而背脊则像山一样。我一直想让女船主带她老公去看病住院,但女船主好像不太舍得。她不舍得有她难言之隐,两个媳妇、孙子都没有固定收入。虽然遗憾,却也是人之常情,我还开车带他去看过病。
欧阳:他两个儿子结婚后也生活在船上?
南:一直在船上,靠打短工维系生活,给别人开船挖树蔸等等,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想让学生多点观察。这条鱼就是我想用来代替的一种人世间最好的情感,类似于雌雄同体的男女之间的情感。但专家认为,这条鱼象征了老疍民不屈不挠的命运,眼睛半睁半开,带着一层荫翳,藏着很深的感情容量。小说里写到,老疍民死后,周边高档住宅区居民反映这个地方脏乱差,市政府便要清除。现实生活中当然没有完全清除,却不停地受到一种挤压。老疍民的妻子在船顶的枕头席子上发现一条风干了的鱼,往深里想,是能找到内在逻辑链的。老疍民得到种菜女人的关心和帮助,帮种菜女人挖沟、建浇菜蓄水池。种菜女人后来得了乳腺癌,因女儿在国外,一个人生活其实很孤单。但两人完全没有男女的那种苟且,纯粹是底层中年男女之间的互相同情。老疍民全身浮肿,爬上大船都费劲,更不可能在舱顶放一条鱼,其实这显示出他的一种心境。然而老疍民跟老婆撒谎说鱼挣脱尼龙网跳到了水里。他老婆自然很生气,好不容易打上一条鱼,卖给酒店是很值钱的。此时此刻,她看到这条鱼时迎风号啕大哭,其中有很大的感情容量,是后悔?惋惜?还是痛恨?很复杂。《老桂家的鱼》影响很大,在《上海文学》刊发后,《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名作欣赏》等杂志皆转载,并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宗璞的小说、余光中的诗、张承志的散文。
欧阳:您的小说往往有多个题材来源,您曾跟学生们讲过,要从自己和亲属的经历,从新闻、历史中积累和开掘素材。
南:是的,即使一个小说,它的题材来源也是广阔的、杂取的、丰富的。譬如《远去的寄生》这篇小说,最初是为《南方周末》一则真实的消息所触动。讲一个老者临死前很痛苦,他当年让儿子去当兵,儿子不慎打坏了一个领袖石膏像,被退伍回来后精神失常死了。这触发了我对父兄辈以及一代人,甚至不止一代人的青春生命的思考。这些就是我说的三个打通。
另外对于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和写作还强调三个信息量: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一个作品如果像大家都看的肥皂剧,都是酒吧街头这些时尚元素,没有更多的知识信息,就没有多大价值。我为什么会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信息量很大。对我们这种有一些经历的人,如果不能够通过自己的笔把那个时代那种社会那些人生的感受写出来,那后人怎么了解?所以我比较喜欢看年长人的传记或者他们写的东西,汲取里面信息,譬如王鼎钧、许倬云等人的回忆录。审美信息量能够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特点,比如《绿皮车》的这种整体象征,《老桂家的鱼》这种个体象征和语言追求。深圳一个青年作家说,南翔的小说很有辨识度,那辨识度通过哪里体现?从你的故事、你的角度、你的思想表达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语言特点。像王安忆的小说,跟韩少功肯定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跟其他武侠作家写的也不太一样,就因辨识度存在。信息量是我非常追求的一个词,虽然它看上去很中性,却是好作品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点。现在我越来越对生态问题有强烈的关注,因为全球变暖。《人民文学》首发的《珊瑚裸尾鼠》,缘起于澳大利亚政府2019年宣布的第一例因为人类活动导致气温上升而灭绝的哺乳动物。物伤其类,人类也是哺乳动物。
欧阳:您以前也写过不少非虚构,零零散散见诸报刊。最近的这本《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应该是您非虚构写作的一次集中呈现吧?
南:《手上春秋》之前也曾经写过散文、随笔、专访,几十年里,采访过不少人,到目前为止采访过两三百人,上到国务院离任的副总理,下到煤矿800米深处的矿工。
我从小就佩服动手能力强的人,包括各种匠人。20多年前,读到日本作家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里面写到铁匠、木匠、船匠、刮漆匠、手编工艺师、纺织工艺师……总之那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手艺人的一鳞一爪,它们的传习过程,令我流连与沉迷。盐野米松对日本尚存的传统手工的记录及其对手艺人的采集,其意识及动手都很早,这应该得益于他的敏觉、怜惜而生出的抢救心态。他跟踪采写的不少手艺门类以及手艺人,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锵然步履,渐趋式微。
这种令人疼怜的传统手艺及手艺人现状,在我们身边、在其他国家,料想情况大致相若。这似乎是无可奈何之事。实际上,一苇可航的日本,其民间技艺有不少发端于中国。1999年中文版《留住手艺》出版,盐野米松在导语里说:其实日本的手艺很多来自我们的邻国中国,中国是我们的土壤,我们的文化从那里发芽、成长和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盐野米松每年都会来中国,不仅行走,考察与采写各类手艺,并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了相关书籍。这位颇为恋旧的作家曾表示,日本在经济、历史和民艺保护上走过不少弯路,希望中国不要重复这些错误。
2019年5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手上春秋》研讨会,有评论家说能不能写一些像日本工匠那样几代的传承,其实盐野米松写几代传承的例子也不多。中国跟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二战前后,老百姓生活比较平和。中国1949年之前多战乱,之后多运动,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还经历下岗转型,很难有代代承传。书里写到的蜀绣、夏布绣等,主人公都是当时下岗的女工,或者经历转型的人。有些属于老三届,有些甚至没有学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很想做一点事情,有耐心,有毅力,便最终选择了手艺,在兴趣与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加之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能够应对家庭生活。小人物的沧桑经历,一条条线经纬交织成全面的共和国历史。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领袖的历史、大人物的历史,它更是小人物的历史、小人物的辛劳、小人物的困顿、小人物的跌宕、小人物的挣扎、小人物的悲伤、小人物的欣慰,只有如此才是一部完整且真实的历史。
欧阳:您第一次采访手艺人是什么契机?
南:两年前在深圳松岗讲座,偶然间得到采写手艺人的机会。松岗街道的干部代为约访了一位区级“非遗”——木器农具的传人文业成。这位七旬老人带我看了他所制的农业时代的犁耙(木器部分)、粪桶、谷磨、秧盆、水车、风车、鸡公车(独轮车)……还有一些他陆续收来的岭南木器农具与家具。文业成告诉我,省市搞农业器具展览,常常问他借这借那,他们的展品远没有一个老木匠收藏的多!南方湫隘潮湿,且多白蚁,无论是寄藏在朋友工厂地下室的农具,还是堆放在屋后只有一个避雨篷置顶的木器,大都岌岌可危。文业成很希望在屋后的那块宅基地上盖一座房子,建一个活的博物馆——可以在里面修复、制作教学与观摩用的木器农具。但由于各种原因,批不下来。我在采访之后写了一篇《木匠文叔》为之吁请。文章在《随笔》与《城市文艺》(香港)刊发之后,有市内记者及人大代表过去看望文叔。可是牵涉一个个人农具博物馆的落地,路尚迢遥。我写这篇自序之时给他去电话,他依然叹息,收藏的四五百件农具及家具,因年久失修、白蚁蛀蚀,已经毁损了三百多件,连一个妥帖的存放之地都成问题,更不用讲日常展示或者修复之所了。木匠文叔的例子尽管是个案,却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某些“非遗”的现实处境。
欧阳:《手上春秋》是您看重非虚构写作的体现,采访与写作过程中有哪些实际困难?
南:我注重非虚构写作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上大学之前,我当过7年铁路工人,接触的人比较驳杂,尤其是接触底层人物较多,对苦难、沧桑、辛劳体会较丰富。这些人你要关切他们,仅仅通过小说是不够的,想着在散文、随笔之外,写这么一本《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最初没有别的想法,没想马上结集,也没想要写多少人,发现一个写一个,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甚至不管它是不是“非遗”或者是什么级别的“非遗”。我只关心两点:一是人物本身有没有沧桑感;二是人物年龄是不是够大,年龄够大才可能有沧桑感,所以写的人物都是50岁以上。其中最年轻的捞纸工周东红也已50多岁了,上了央视《大国工匠》栏目第一集。全书包括制茶、制药、刺绣、蜀锦、正骨、成都漆器、铁板浮雕、锡伯族角弓等14个传统手工艺。
接触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不够熟悉,很难马上推心置腹,也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比如广西壮族做女红的黄美松不懂汉语,没有多少文化。有些靠朋友帮忙,有些靠当地主管部门打电话沟通。历时两三年,做了这么多采访,写了一本十七八万字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不好界定是散文还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显得太硬,散文好像又太软,最后还是归类到非虚构,因为非虚构的范围很广,散文、纪实、传记等,甚至一些博物、科普都可以归入非虚构。
欧阳:北京的评论家、文学博士付如初写您的一篇评论,形象地把您的采集比作是“把书桌搬到田野上”,这反映出您怎样的创作观?
南: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强调田野调查。可能我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那天跟王安忆对话,她说她比较害怕跟人打交道。她属于书斋型,我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田野型。她希望我回归一点,多在书斋里待一待。但我因受制于眼病、颈椎,有时候不能伏案太久。
田野调查不一定是到田里去、到河里去,而是要求笔者深入民间、深入基层、深入到人物中,用心感受并发掘出很多东西,不论是老人的经历、年轻人的经历,或者是不曾接触过的陌生行当。就像我俩上次一起去四川渠县采访竹编手艺人刘嘉峰。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凭借着自己的手艺,解决了养家糊口问题。他出身不好,却能在“上山下乡”高潮时期逆向进城,落户到县城,还娶了一个好媳妇。女方看重的便是他的心灵手巧。这些全是技艺给他带来的好处。这些人物的历史,不是金戈铁马,不是晨钟暮鼓,却很有意思,可以折射出一个大时代的波澜。
手艺人的人生可以给现在很多年轻人一些启发。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一种比较富足的体面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靠父母的荫蔽,或者贵人相助,或者时来运转,等待命运的安排,当然也有,但肯定不是一种常态。
任何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采集与嫁接更多的人尤其年长者的经历,才能视野开阔,这一点对当下的大学生、研究生尤其重要。现在很多学生不会采访,也不愿意采访,满足于在互联网上找例子、做论证、写文章,我对这种情形,很是忧心。
欧阳:在处理现实题材上,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和记者式的人物访谈有何区别?
南:北京研讨会上,很多评论家、作家对《手上春秋》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此书当然不同于记者式写作。我在文章里主动灌注一种审美意识,由于技艺本身是美的,再用富有文采的笔调把人物形象勾勒出来,因此每一篇写完之后,都深受手艺人喜欢。有很多人被各大媒体访谈过,其中有一位在交谈时说,中央台几个频道全采访过他,但看完我写的文章后,认为是最好最全面的。
此书在14个传统工匠之后,也写了一个当代工匠,就是压轴之作《钢构建造师陆建新》。中国一线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与陆建新有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北京中国尊、深圳平安金融大厦、广州西塔……他也是广东省唯一的“央企楷模”,接受的采访资料打印出来就有一尺多厚,内容大同小异。此文发表在2018年第12期《中国作家》杂志一个专栏头条,后来被国务院国资委收在《大国顶梁柱》一书里。当时我也在犹豫,他好像较难算入中国手艺人。汉语词典中“工匠”的解释只有四个字:手艺工人。现在我们给工匠赋予了精益求精和当代意识,古代工匠其实也追求精益求精。陆建新把一沓图纸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在施工现场他要解决很多问题,要有很多发明创造。其实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现在既非创造大国,亦非制造大国,缺少的就是这种专注、纯粹的工匠精神。
我也没有停止探索,包括题材及形式的探索。每行一步,都希望有赓续者,包括现在写的生态小说。生态被破坏的程度大大超过所有人的预期,但很多人是麻木的,洪水不淹到脚脖子底下就觉得跟自己没关。作家应该要有一种敏锐、一种预见、一种情怀,如果一位作家没有这种素养,那一定是跛足的,很难写出更好的作品。我想,接下来一个时期的写作可能会跟生态有关,遇到了可写的素材,非虚构也会继续写下去。
欧阳:在手艺人系列非虚构的采写中,您更偏爱哪一类手艺?结集成书时,是否就保留了这个顺序?
南:在采集手艺人的过程中,我倾向于与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相关的工艺,正是这些门类及技艺几千年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日常成为现在的模样。换言之,虽然有些技艺逐渐退出了当下生活,可却如盐入水,融入了我们的历史与思想,成为我们血肉的一部分。如文叔,尽管他是第一个被列入“非遗”项目之后的传人,却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深圳已无农田,即使之外还有广袤的田野,却也不再使用秧盆、禾锄、水车之类的原始农具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哺育过多少代人的农耕过程、景观及器物。
同时我也热衷于寻找年长一些的手艺人。这里面采集的15人,都是半百之龄以上,从50多岁到80多岁不等。一般来说,年长者的人生经历要丰富一些,对技艺的感受要深入一些,对传承转合的痛感也会更强烈一些。质实而言,我想以鲜活的个体沧桑,刻画出一个行当与时代的线条。这本书里依次写的是木匠、药师、制茶师、壮族女红、捞纸工、铁板浮雕师、夏布绣传人、棉花画传人、八宝印泥传人、成都漆艺传人、蜀绣传人、蜀锦传人、锡伯族角弓传人、平乐郭氏正骨传人……取自东西南北中,汉族之外,还有壮族、锡伯族,基本都是“非遗”传承项目或项目传承人,从市区一级到世界级(人类“非遗”)都有。却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书里排在最后的《钢构建造师陆建新》。采写陆工,旨在传统手艺人与当代工匠之间,标一道津渡,有一个承接,现一条源流。
欧阳:一些评论家把《手上春秋》归于非虚构之列,我宁愿将它看作一种糅合小说与散文技法的跨文体写作。
南:《手上春秋》一写个人经历,二写行当技艺,三写传承难点。期望做到历史与当下、思想与审美、思辨与情感的熔铸。各路传人的艰辛与企盼、灼痛与欣慰、彷徨与坚定……都应该留下不朽的辙痕,不因其微小而湮灭。这部书写竣之际,一个朋友说,你写了一本什么年龄都可以看的书。想来确实如此,个中的人物、技艺、故事、情节、细节以及一帧帧精美的插图——各位工艺匠人的杰作,连小孩也可以从图例中感受到传统技艺之美。所谓传统文化,不应局限于读书诵文的感受,更应在日常生活中习得。
手艺与器物无言,却承载了几千年的文明,汩汩如流,理当珍惜、珍爱、珍重。“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间应未有。”(王安石)用文字与影像打造一个个手艺人的博物馆,此其时也。愿与更多的作者与影像工作者一起,深入乡野与民间去采撷,拾得斑斓,留住芬芳。
(作者单位:南翔,深圳大学文学院;欧阳德彬,职业读书人)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