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题”之“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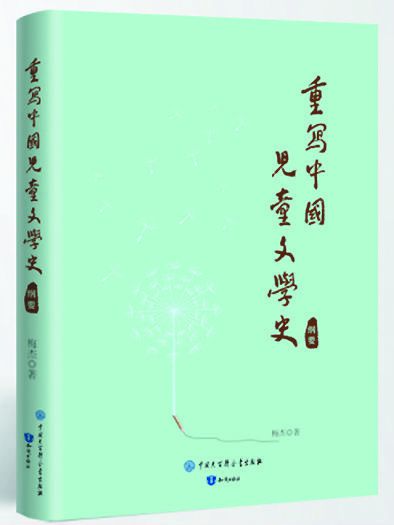
梅杰兄来信,嘱我为他即将完成的新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作序。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历来欠缺,现有的几种或著或编之书,虽也来之不易,但又有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词不达意之嫌。所以,对梅杰兄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努力姿态,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忙乱,若是对梅杰兄的大作,无暇慢慢阅读,不能细细评说,岂不愧对,岂不怠慢,乃婉言辞谢。不想梅杰兄知我苦处,提起了周作人“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一类话,允我写一篇“以不序为序”的文章,终于进退无路,只好应承下来。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叙述,历来有两种截然反对的观点:一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一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我本人持论,不仅属于后者,而且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一观点的发明者。
我要说的“书外边”的“意思”,就是一些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古已有之”论者的研究方法,若是作不完全的归纳,则有其四。
其一,不管古人怎么看、怎么说,就只管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意见为儿童文学史的事实。主张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人往往都这样做。他们分不清文学史的写作里,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当下的研究者的“言说”。
举个例子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的《叶限》,古人是将其称作“志怪”的,可是今天的“古已有之”论者却一定要将其称为“童话”。其实在古代,《叶限》并没有作为“儿童文学”而被对待过。今人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效法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将 古 代 的《叶 限》进 行“现代转化”——变为白话文,讲给“现代”的儿童们听。那么,你说讲给“现代”的儿童听的《叶限》,是古代的儿童文学,还是现代的儿童文学?我说,任何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根据之一就在这里。如果这时,“古已有之”论者搬来克罗齐,说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用的,因为克罗齐说的意思,不是你想说的意思。甚至毋宁说,克罗齐恰恰在反对你们让历史研究失去活生生的生命这种做法。
其二,“古已有之”论者只将“儿童文学”看成一个个“实体”(作品),而不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观念”。我说儿童文学研究缺乏“理论”,这是原因之一。儿童文学史研究要拥有理论的那种“谛视”目光。“谛视”的“谛”是真谛的“谛”。“谛视”式研究为的是透过现象和经验,看穿研究对象的精义和本质。
在方法论上,儿童文学史研究有必要明确这样的认识:所谓“文学”,它并不是一个“实体”,即不是一系列具体的作品,而是人头脑中的一种观念。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而存在,“文学”只能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他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是一种意识。”
还是举前面的《叶限》那个例子,“古已有之”论者信誓旦旦地将其说成“儿童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叶限》是“儿童文学”,这属性是作品本身所天生固有的,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知道,《叶限》自身并不能规定自己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古人将《叶限》定性为“志怪”,今人将《叶限》定性为“童话”(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正因为古人与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因为古人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才没有把《叶限》定性为“儿童文学”。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能够把安徒生的童话拿到原始部落去讲,就会出现那里的成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恩物这种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
其三,“古已有之”论者将儿童文学看作可以“自在”的文学。这个问题与“其二”讨论的问题有联系。
我感到,当今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儿童文学”是可以“自在”的文学。但是,文学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一经阅读,文学就不是“自在”的,而是交由“自为”的、“自觉”的读者了。
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自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的,而是在人类的心智进化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才被自觉地创构出来的。我们举两个发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先声,但不是“自在”的行为之事例为证。在西方,很多学者都有共识,把英国的纽伯瑞出版《美丽小书》的1744年看作儿童文学的开端。纽伯瑞自觉地以“教育和娱乐”(写在书的扉页上)为《美丽小书》的创作和出版理念。在中国,“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语)。叶绍钧在拿起儿童文学创作之笔以前,就有了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叶绍钧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是受了西方儿童文学的直接影响。
其四,“古已有之”论者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时,采取“孤证”的态度。
如果儿童文学治史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的话,就应该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知识”话语,必有它产生的历史。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能与成人文学“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的发生及其确立,还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发生,是来自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地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奇迹。
但是,“古已有之”论者在论证中国古代所谓“儿童文学”的存在时,却用“孤证”的方式敷衍了事。也许他们也不想敷衍了事,可是巧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仅仅靠“孤证”,是无法建构出文学史的。“笔下无史”,这就是我读目前的古代儿童文学史叙述的鲜明感觉。
已经说了不少“书外边”的“意思”。其实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意思”多多少少还是与梅杰的这本《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藕断丝连。从这一点来说,这篇“不切题”的序文,竟又是有些“切题”了。看来,周作人的文思还不是吾辈所能师法者也。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梅杰/著,知识出版社)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