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2年第3期|张远伦:日常的神性
他是为神灵黥面的人
那个错手把墓碑上的神像划出了痕迹的雕师
是我的外公,他叫李国文
他是为神灵黥面的人
——《古镇匠人》
外公一生与石头为伍,石头是他的衣食父母,是他的儿女,还是他的知己。当然,石头也是他的敌人。
童稚时代起,我就经常在黄泥坡上,看到他藏身于石头之中,满脸黏着一层灰尘,蹲伏着,缓慢地雕刻石头上的每一个图案和汉字。他心无旁骛,在晨曦中隐身,直到暮晚,沉浸在石头的世界里,仿佛雕刻的是时光,是生命,是自己的心灵。
他首先要选取村子里上好的页岩,页岩薄薄的,一层一层的,便于切割打磨,还不易折损。它们有倾斜的取势,不是45度朝地,就是45度朝天,最顶上一层,往往孤悬,显出危殆,却轻震不落。5.12汶川地震那次,村子里掉下的,也仅仅是一块垂石,像是下巴上终于除去一个小小的石瘤。石头与村庄成天然锐角,滑落下来轻而易举。
他一生都在违天道,违自然之道,把这些石头从本来的位置上取出来,耗费大量时间,为每一块石头“封神”。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似乎又以一己之力,把对自然的索取变成了对自然的馈赠,他内心有满盈亏欠,手下有残缺完美。他用精细的技艺实现了这片山坡的奇妙平衡。
如今,取石头的顶盖,揭石成碑,仅需要电锯,那把我推为金属之首的老錾子,外公的家当,像一截被磨损过的时间简史,躺在他的工具箱里,已经很久了。
把石头分层,我不知是不是海洋干的。一层石头睡在另一层石头上,又一层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沉重。外公是知道这种沉重的,他尊重这种力量的压迫感,用钢铁的利刃把它们慢慢地撬开。我在村里住了十多年,从未想过自己也睡上去,由于太过卑微,我害怕去离天更近的地方。有一天我看见麻雀睡上去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作轻盈,或许麻雀在顶石上的出神,真是高贵的,也或许,她仅仅是因为饥饿,才去了高处。有一天,我看见外公也睡上去了,像麻雀那样,也很轻盈。他在顶层上休憩,入睡,鼾声传来像是在传递蓝天的信息。他睡了一会儿,忽而又翻身下来,像一块石头轻轻落在大地上,而后又开始凿石头。
外公不是需要石头,他只需要石头的一个截面,它满是凹痕和凸起,像是层石之间的咬合,或者叫吻合。木头这样的行为,叫作榫卯之交,石头这样的行为,叫作唇齿之交。我们要把这样的层面变成截面,无非就是去掉它们的咬合,或者吻合,我们要一个平面。外公是一个高超的整容师,他懂得石头的经脉和内心,因此他小心翼翼,像一个对村庄犯错的肇事者,动手前,反复抚摸这一块石头,像爱,也像祷告。
每一块石头的层面、截面、平面,在外公的手掌抚摸之下,都是柔软的。
像是他自己的面子。
他要精心地打磨它们,让这些石头,渐渐成为某一位神灵的表情,呈现伟大的人力所不能抵达的美和善。我知道石头的老幼,亦或是尊卑。在一名老石匠那里,是伦常,还是“道”。他似乎洞悉了另一种时间,用远古都不足以描述。可他的手指,无数次去过那里。
他的石头面子,有的粗点,粗到我能看见它的母体,里面尚有另一种石头做的纤维在游弋;有的细点,细到我误以为是石碑的裂隙,可它们有韵律,有动弹的迹象。这些石头截面上的痕迹,被学者称为古生物化石,被外公称为“石疤”。他说:石疤好,是块老石头。那些年,我会趴在外公磨平的石面上,好奇地欣赏天然的石头艺术品—那些有着美妙身段的古代小昆虫化石。
它的体型折磨过我的诸多词语,玲珑、修长、匀称、圆润。我会从它圆弧形的腰腹,看到它逐渐消失的触须,然后停留在巨大的想象里:它是一只在石头里睡着的虫子,石头让它变成了石头。一块小小的母性的石头。袖珍版的骸骨之美,源于低调的白色。这是真正的白骨。石质的白骨,与石头的青色,形成了绝配,那意味着两种时间,一种包裹另一种,也意味着两种骨头,一种包裹着另一种。老石匠要做的,就是从中吸出髓来,我要做的,就是停止对骨头的想象。
它从海洋里来,到石头里去,再到墓碑上,被看见,被磨砺,被当作修饰。它是最后被风化的石头,当名字变浅、消失,它们,作为有体温的石头,坚持到了最后。有时候,一个它,恰好出现在墓碑的一个字上,躲避不及,便碎屑纷飞,被老石匠用一把平錾削掉,代替它出现的那个字,成为了石头的另一个意义,一个不完整的意义,有时候是姓氏,有时候是名字,有时候是虚词,但从来不是一个标点。它运动到墓碑的显要位置的时候,多么希望自己无意义,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空白。
然而,有的石头是有欺骗性的。石头往往会成为外公的敌人,数次考验和折磨他的敬畏神灵之心。原本看上去上好的石材,常常会有难以觉察的杂质和缝隙。它们会造成外公心中神灵的破损,让数天的工夫前功尽弃。因此,仔细辨析一块石头显得尤为重要。裂隙往往看不见,抑或是看得见的纤毫,吹灰尘的时候,裂隙仿佛在动。这时候,老石匠需要一点水滴上去,有点像是滴血认亲。裂隙,渐渐露出深黑的底色来,蒙尘的时候,会形成一线水渍蜿蜒而下。裂隙会说破就破,一块石头就废了,一个优雅的平面就废了。
只不过,对于外公这样技艺精湛的老石匠来说,神灵的破损往往会带来另一种命运的转机。裂隙的形成,不是运程有了线条,不是石头老旧,而是石头有了新面孔。边角料,有时会做成一座墓碑的向山石,用来指向,成为石头中意义的代表。外公会变废为宝,变旧的残缺为新的完美。
打磨好石头的平面之后,外公要给石头上漆了。给光滑的一面上黑漆,一把刷子就够了。不需要多么精致,不需要多么虔诚,有时候他需要先给石头上一把火,烤干它;有时候他只需要阳光,和一场小梦,醒来就可以刷了。他满头灰尘,满身污垢,黑漆沾身,状如旷野之中的孤绝灵兽,在刷完碑面后,他站直身子,一声长嚎中,把体内无法言喻的气息释放出来。
然后他要给碑面打上格子。用朱砂窝取来的丹砂,放在墨斗里混合水,调至黏稠,又能被墨线弹开。他在手指轻轻拨弄之间,便把格子一个一个地弹出来。此时,老石匠从山间牵引出的线条,叫横;彼时,老石匠从山间牵引出的线条,叫纵。此时和彼时,交叉一下,就是方格。再交叉一下,就是网格。老石匠的每一个格子里,都会住进去一个字。老石匠弹出的网格里,住进的是一个人的命运简历,被称为墓志铭,抑或控告书。
我有时候会要求做一名小石匠。我内心那点动静,被冷峻的石头发现了。学徒最难学会的,是定出碑面上的中轴,尺子不能解决年龄和孤独的问题,我的颤抖,往往与自己的偏向有关,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一个没有来得及恋爱的少年,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黄昏,我学会了在墓碑上打格子,标记、删除、清理,像虚妄那样。
这些格子里,会刻上我反复摩挲、反复欣赏的书法字体。有时候是外公自己写,有时候是请先生来写。无论谁写,都是对幼年的我的美的启蒙。
碑面只容得下方和圆,完成的方格子,往往只能完成一场叙述,比如碑序。而祝词进入石头,便会借用圆靠近永恒。比如:“松柏长青”这四个字,在碑面顶部,只能取圆形,呈顶弧状,字体放大,显赫,关于活着的幻想,比关于死亡的现实面积更大。这不需要圆规,只需要一个土碗,覆盖上去,绕着画线条,就可以装下那四个字了,就可以在石头上,让一个比喻,成为祈祷了。
碑面是亡灵的自证,所以需要最先备好,雕刻时也须极其小心,不能错漏,不能破损。而辅助碑面,让整座墓碑得以成型的构架,往往更粗犷。
外公要雕刻一枚大小轻重恰到好处的向山石。它由于高居头顶,而会为飞鸟驻足。这唯一可以独立卸下来的石头,就连不断生长的千年矮树,也动摇它不得,根,从来不到高处去,特别是坟墓的高处。我,从来不到高处去,我怕看见跪拜的人间。而一名老石匠,必须到高处去,他要将另一世界的中轴线校准,要把人间的祭奠,调整到最为符合山脉走向的角度。
他还要雕刻“爪”。其实它更像是翅膀,老石匠叫它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身具飞行的波浪,延展开去的波浪。翅膀里面装着鱼,简单的图案,有了天上,还有了水里,而这个奇怪的爪,可能关乎大地。我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却不及外公更能异想天开。特别是当他具备了艺术化的手艺,就会为死难者献上富于想象力的祝福。这个爪,堪称“封神”的结果,从未见过的物象,水火风雷,以及稼穑鱼获,都像它。
他还要雕刻“向山石”。远处的山峰虽小,却可以搁笔,据说叫作笔架山。实际上可能叫作猴子山。这块石头的存在,指向就有了吉祥的意思,它不仅包含远方,还包含未来。有可能是三个字,比如:申山寅。有可能是四个字,比如:申山寅向。我小小的村子,既是四面,也是八方,我的亲人们,可以把这些方向用完,还可以把别人的山峰花光,把脚步去不了的地方,放在朝向石的前面,用几个字,奔跑而去。
他还要雕刻“盖瓦”。把石头做成瓦片,为神灵和亡灵遮阴,或者挡雨。我的亲人们都在死后上有片瓦,如果数得过来,可能有千片瓦。老石匠雕琢的寒石成为瓦状,其瓦连绵不绝。老石匠做的墓碑不能没有盖瓦,逝者的每一个雨天不能没有破帽。他雕琢得很细心,每一片都要露出光滑的背脊,所有背脊共用一个腹心,看不到的腹心。只有老石匠的錾子看到过,炫技,有时就是点到为止。
他还要雕刻“拜台”。新泥松软,有一个深深的凹痕,有人长跪不起。换成石头,变成拜台,石头,也需要一个凹痕,一个人的膝盖,无法完成,许多人的膝盖,也未必能完成。一个村庄所有悲伤的力量,都在那个凹痕里。这个痕迹,一旦出现,就是神迹。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主碑”。主流,不过一条;主碑,不过一行。石头越宽越是寂寥,写什么都是对的。在村里,人的一生,谋求一块主碑;在村里,一个村庄,只有一条主流;把墓碑立在江边,一块主碑,就有了一条主流。该动的不息于流淌,该静的不舍于昼夜,我在这里,不语。于身旁一条小河,于笔下一百主碑。一个老石匠,伫立在主碑旁,也无语。他的内心活动,略等于神灵的内心活动。我只能猜测,他想到了什么。也许是在用两千多个汉字,默默地念诵一篇祭文。
有时候,神,就是一种想不到,或者意外。
外公的技艺就是将这种“意外”进行到底。他会赋予墓碑上臆想出来的神的表情以各种丰富性。就连他们的体态、眼眸、衣袖等都有数十种变化。
而最让外公懊恼不已的,是偶尔会错手把神灵的面容刻出不必要的痕迹来,像是作为一个凡胎,对神灵施以黥面之刑,这绝对是僭越和不敬的。
然而这一部分里也有最细腻的雕工,在石头上,用叙述性的线条,对一个故事进行呈现。比如“二十四孝”,是外公雕刻得最多的。
孝感动天、百里负米、卖身葬父、卧冰求鲤、弃官寻母……我想每一个孝道故事都被他雕刻过,每一个故事都被他用石头演绎过。我不确定的是,他是否能在“石头语言”里讲清每一个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故事一定是用细节讲出来的。石头造型中的细部镂刻,看似静止而又笨拙,但是用形象也能叙述出整体的情节。这依赖的就是细节的张力。外公显然洞悉了一切语言符号艺术的本质:用形象说话。
外公最喜欢雕刻的是“百里负米”。他会一边雕刻,一边微笑着向我讲述《孝经》:周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现在想起来,他竟然能背诵,实在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当然,这种能背诵也有偶然性,我想原因无外乎:米,是他们经过饥荒之年的人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背米养家,是最为朴素,当地亲人们最容易接受、最浅显易懂、最具有教育意义的碑刻故事。
“伦儿,我给你讲个故事,背米的故事。”
外公停下手中的錾子,坐在石头上,点燃一支叶子烟,吐了几个圈,然后慢悠悠地给我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经历:
“灾荒年,我到湖北大路坝去借米。”
“米还可以去外省借?”
“是啊,我开了集体的介绍信。湖北收成好,我们去借米,承诺来年加倍还。在去的路上,天黑了,我在途中的一个石洞里过夜,因为太困,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身旁有一具死尸。我竟然挨着一个死人睡了一夜,把我吓惨了,但是我还是故作镇定地去了湖北,背回了几十斤米。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想起那个死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雕刻很多背米的孝道故事吧?”
“嗯嗯。”我似懂非懂。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为村民写墓志铭的人
我成为诗人实在是偶然。
我的“必然”应该是成为一名石匠。
在石匠的主业之外,我应该成为一名业余的“写碑者”。
于是,偶然与必然之间,似有某种血缘传袭,命定我必须以“写碑之心”去写诗。而我的诗做到了这一点吗?显然,没有。
1996年,我从酉阳民族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一个叫作“诸佛村”的完小教书。因为写字略微有点规矩,我这个“土秀才”常常被周围几个乡镇的人们请去为他们“写碑”。在他们亲人的墓碑上书写生平序言,也就是“墓志铭”。
不像司汤达的墓志铭——“米兰人亨利·贝尔,活过、写过、爱过”这么简练而深刻,也不像辛波斯卡的墓志铭——“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旧派的人。她写过几首诗”这么诗意。村子里的农人们往往更在乎被记录和流传不朽,平静的一生也要用很多汉字来表达,来展现他们的不平凡。我也常常绞尽脑汁,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然而,他们的命运大多类似,一篇墓志铭的模板就可以代替很多人。然而我不能,我要让他们以不一样的面孔,活在石碑上。所以我调动了很多诗人才有的语言,用诗歌般的句子,来录下他们幸福抑或苦难的一生。
诸佛村的边缘,坡度渐大
在这里写碑,有时候,需要跪着
除了沐手,焚香,对一块石头足够的尊重
就在这个姿势上
由于跪书,我绝不可能用章草、狂草
也绝不可能把对生者的轻佻,用在死者处
请我写碑的人,有时候
会取下他身上的棉衣,垫在我的膝盖下
我挪一下,他们就去挪一下
而这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只对父母做过
在我的诸佛村,如有一个花甲老者为你垫膝盖
说明你写墓志铭上百块了
说明你已经向陌生人下跪上百次了
向冰凉的石头下跪,上百次了
——《跪书》
每次写碑,都要沐浴、净手、焚香,要先将对亡灵的尊重,调至最高频道。即使他不过是一位毕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文盲农人,即使她连一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而被记录为“某氏”,即使他坐过牢或是当过叫花子,即使鳏寡孤独或是非正常死亡,死后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一块石头是对他们的尊重,石头上我写出来的文章是对他们的尊重。所以,我在书写的时候,必须要有仪式感,不得随便,更不能随意。
黑石头潜伏在村庄里,等着一块白布,舒展地,轻灵地,蒙上来。满身污垢的诸佛村人,希望一块石头是干净的。我在写碑的时候,借此防黑漆沾身,并把内心的圣洁,再温习一遍。在我的诸佛村,要是你是一个写碑人,千万别拒绝一块白布。在我的诸佛村,要是你是一个丧母者,千万要准备好一块白布。
入冬,诸佛村有更深的冷寂,一盆杠炭火出现在野地上,寒彻心骨的石碑,渐渐温暖。我僵硬的手指,逐渐灵活,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写了:
“恭序……”
似乎,那盆火的出现,就是“恭”字的一部分,也是苦难序言的引子。那时候的我,很容易忧伤,并未勘破穷困的命运,因此我感激,那些死者为我准备的那一盆火,似在照亮,也似在打开。我看见,鹑衣百结者,和一瘸一拐者,都朝我走来。确切地说,是朝这一盆火,走来。中轴线上那一列字,要写稳当。不能用行书,滑了;更不能用隶书,偏了;正楷,是唯一的体式。写一个不庄严的字,就是一次亏欠,我对村庄的亏欠,不止一次了。为此我深怀愧疚,像一个逃逸者。我的天赋,就像我的罪过,集满一身。
写碑十年,我记得最清晰的五个字,就是:生老病苦死。我在写中轴线上那一列字的时候,要反复默念这五个字。最后一个“墓”字,必须落在这样的顺位上:生、老,必须避开病、苦、死。生前遭罪,死后远离诸般苦楚。这五个字概括了诸佛村的人间,也超越了诸佛村的人间。
不写碑十年,我还在那五个字上念叨。生老病苦死,像佛语,也像巫咒。
天下大寒,适宜写碑。大寒节,立碑日。1999年诸佛村极寒,我的毛笔尖,从未结过冰。一夜大雪,我的木房子周围净是大雪压断竹子的声音,仿佛是我诗歌中的一些句子有承载不了的重量,在纷纷折断。大半夜未眠,凌晨竟然沉沉睡去。然而睡意正浓的时候,门外有人踏雪而来,重重地敲击我的木门。
“张老师,请你给我写碑。”
我穿衣起床,透过窗花格子,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瘦削的中年人站在阶檐之下。
然而让我意外的是,他要给自己写碑。
“你是要为自己修建活人墓吗?”我问。
“是的,就是生茔。我要趁没有死,扭得动,先把自己的碑修好。我只有一个女儿,但是很小就走丢了。我现在是一个孤老头。我死后,拜托邻居把我拖进生茔。要是我的女儿还活在这个世上,她就能找到我。如果我还不赶紧修好生茔,那么我死后,女儿就可能找不到我了。”我突然觉得这个人的墓志铭不好写,而且很沉重。我该怎么给他写呢?便让他先回去,我枯坐在木房里想了大半天。
第二天,我去了他的生茔所在地,一个陡峭的山坡上。依旧是沐浴、净手、焚香,尊重这个活着的人,应该也和尊重亡灵一样;依旧是跪书,山势不平,不跪不行;依旧是他为我找来垫子—一件棉衣,并随时为我挪移;依旧是白布蒙碑,不能玷污他的脸面。
我写道:杨公胜成,生于乙亥,卒于未尽之时,少年擅射,为寨中猎户。及至弱冠,从军报国,退役后牧羊为生。妻早亡,膝下一女,于丁卯秋走失。后杨公南下深圳、广州,西行新疆,数次寻女未果。如蒙天怜,女当回归,见字如见父……
我写一遍他的碑序,仿佛在替他重新活一次。
接连不断的墓志铭,在凛冽中完成,其中一块,写好后即覆盖大雪。写完一个苦难的人生,就天下大雪。
他是为菩萨换骨的人
那个有意把墓碑上的火石,换成了石灰石的石匠
是我的外公
他是为菩萨换骨的人
——《古镇匠人》
外公十六岁时,患了疟疾,昏迷不醒,亲人们以为他不行了,就把他装在木匣子里,抬到山上准备草草掩埋,就在向坑里铲土的时候,匣子里有了动静,继而传出呻吟—他又活了过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虽然一生贫困艰苦,但是高寿,算是奇迹了。
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便召集亲人们全部回去为他送终。然而,大家一直没有送到终,他好好地活着,又活了二十多年。
去年腊月,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哥哥打电话来跟我说:伦,快回来,外公这次肯定是熬不过去了,赶紧来送终。我赶回郁山镇上,一个表弟也到了。他要从镇上开始,走路回村。而我觉得可能还是坐车快一些,却不想被堵在半路。走路的表弟刚刚到外公家里不久,外公就走了,他送到终了,而我反而没有送到,这似乎就是天意。
我成年以后,写字有那么一点功底,其实就是外公启蒙的。
他成为“刻碑人”,我成为“写碑人”。
我们都是在石头上寻觅“神性”的人。他才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是“神性”本身,我是着迷地用汉语言文字符号再现这种“神性”的诗人。
那天,我蹲在他身旁,听着叮叮当当的雕刻碑上文字的声音,突然对他说:我想写字。
他转过头,笑咪咪地说:写字啊,别找我学,找先生学。
先生指的是那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也姓李,就住在村里。他曾经是一位私塾先生,教过书,娶过童养媳,当过教师,成为过“右派”,落实政策后依旧在村里为大家写写字,教教写字。我找他学书法的时候,才进入小学二年级。学习写字的那段时间,生活其实比较平淡,没有多少惊奇和兴奋。倒是有一次,外公告诉我:先生家有两本《易经》,你去借来读,然后你就可以算出自己的未来了。
这让我很感兴趣。但是,没有借到。直到我进入师范学校,先生觉得可以放心借给我了,才让我如愿。当我摩挲着手里两本光绪年间的泛黄的《易经》线装本,觉得那种神秘终于被我体验到了。然而我并未弄明白里面的文字,迄今为止也只记得简单的诸如“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或者“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样的句子。至于它们的含义,我实在没有兴趣去研究。我觉得,只有写诗才足够吸引我。这两本书后来辗转之间不慎遗失,不知去向,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和遗憾。
然而外公是喜欢周易之道的。他常常会借此来阐释一些风水之道。刻碑人与“风水学”,本身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行道。我对此毫无兴趣,觉得被夸大了,成为了“伪科学”,对一个具有现代价值观的“诗人”来说,这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他老人家常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却是对我很有影响的。
在写诗的过程中,我常觉得,诗歌的修行,很大一部分是“善”的修行,天下诗歌,唯善不破。“善”的部分,就是“神性”的部分,就是信仰的部分,是灵魂干净的部分。
外公对石头的认识,就像认识自己的身骨一样。
哪些石头适合雕刻,哪些不适合,他一目了然。他告诉我:页岩中夹有火石的,绝对不能用作墓碑。因为火石易碎。
哪些是火石呢?他说:来,我教你燧石取火。只见他从一堆石头里随便翻了两枚出来,不断地摩擦,发出“啪啪”的声响,火星四溅,一会儿就把一堆白茅草引燃了。
然而当我拿出两块石头,将双手都擦出水泡了,也没能溅起一点火星。
“伦,来,看看什么是火石。”他把口中说的“火石”拿来给我看,上面质地粗糙,有颗粒感,不像可以雕刻的石头那样细腻均匀。“火石”拍断后,容易散,很像是玻璃破了碎片化的感觉。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一种氧化的石英石。
“当你在雕菩萨的时候,遇到火石,必须果断换掉,就像为菩萨换骨,不然你的菩萨永远不能成型。”这句话,我永生都记得。菩萨的骨头不能是易碎的,而应是坚实的。一个人的一生,像外公那样,活到成为全家的“活菩萨”,他也是有坚韧的骨头的。他的骨头是“善”。他活了接近一个世纪,从未害过一个人,从未与人为敌,他的境界已经是通透的了,澄澈的了。他的生命履历,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带有“神性”的奇迹。
他为自己换骨。
默默地换骨。而我们浑然不觉。一个凡人的骨头,因为自我完善而悄然石化。当他躺在冰棺里,我去瞻仰的时候,看见他骨骼突出,像是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墓碑,206块墓碑,沉实地坐落在一个叫“黄泥坡”的地方。
我转进他生前的卧室,在床底下,看到他赖以为生的錾子闪着锋利的光芒。多年没有使用了,应该是锈迹斑斑了。不,是光洁而白净的。显然,他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前一段时间,磨砺过自己的錾子,就像磨砺过自己的傲骨。大的平錾是用来铲平大面积石面的,小的平錾是用来雕刻字迹的,中等的平錾是用来打制神灵和菩萨的粗胚的。大小平錾一起使用,便是为人间的菩萨造像。那么多的“封神”的工具,平静地躺在一起,一点不争功,谦逊地互相成就,并居住在黑暗之中。
然而,它们为外公换骨,为我的诗歌换骨。
当然也为我的生命换骨。
在石头上模仿救世主的人
在村里,每一块凸石都是有善意的。
它努力向悬崖的外沿用力,向扑来的云海,争取更宽的平面。这凌空腾出的虚位,带着悬崖最大的意义,让我错车时停得下摩托,安稳地看着身旁的大卡车驶过。要是没有这块凸石,我不知道自己会多胆战心惊。也不知道,那位卡车司机会怎样向宽阔处倒车,然而在这样的深山险绝处,能找到宽处多么不易。
这块凸石,能让拍云海的老人,放得下三脚架。这高山峡谷,最接近仙境的美,就是那蒸腾起来,弥漫开去,将整个低谷覆盖的白雾。这里,就是最佳拍摄地点。所以它最先沐浴到清晨的阳光,云朵也最先抚摸了它的嶙峋瘦骨,如是此刻云海溢出到路面上,我就是那个一念白头的人,我就是那个尚未来得及悲伤,一瞬间又佩戴金冠的人。
当我进入小镇,看到每一块石头,我都会心有所动,而后满怀敬意。它们都是菩萨,经过无数脚的踩踏,时间让它们变得光滑。一场雨水过后,石头上尘埃尽去,异常洁净。我看到它们的镜面上有打磨的天空,幸运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点微弱的蓝,更多时候,我会窥见石头里的乌云。
蹲在那里良久,换着角度把玩异化的我,有时候狰狞,有时候温润,我沉浸于这存在和消失的谜面。人们都在内心,依照自己的样子雕刻新的菩萨,每一块石头都是半成品。你看,秋日暖阳中,那个微微闭上眼睛的人,一定是在最适合自己的石头上,模仿救世主。
那不就是外公吗?
所有我经历过的石头,最终都成为有灵性的动物。
所有我抚摸过的石头,最终都成为我的某一枚脏腑。
我感觉到它们的搏动。血液和大河穿过我的每一块石头。
依次地,我从村庄走出,经过小镇,抵达了我的都市。
没想到,像自身携带的骨头,它们也跟着我抵达。女儿的命是水做的,那男儿的命就是石头做的。石头笨拙无言,我们可以互相借喻,互相指出对方的硬和软,爱与恨,生存和毁灭。外公,他把弄的那些石头,如今在山间充当着精神的领袖,而他放过的那些石头,如今如影随形,来到长江之滨,成为我精神的导师。
毛重半斤,净重八两。这些石头行遍整个流域,千里河床,打磨和推敲,完成了一块石头的小叙事,很短:“磕碰。终。”它说。这般圆熟和光滑,只不过是石头学会了赶路。而它身上,冰川的体温犹在,我站在这块石头上,保持着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在草地上旋转起来,像石头的种子落在大陆上,它也跟着旋转,陷落,渐渐隐没了身骨。
我一直试图从一堆小圆石中,找出方形的那一枚。我一直试图从一堆五彩卵石中,从红、褐、黄、白、黑中,找出淡绿色的那一枚。大水自由奔袭,却是天下的规则和模具。极其狰狞的石头,在我手里,已经极致温柔。整个下午,我都匍匐在滩涂上,寻找那枚不存在的石头,也像一枚顽石,被幻想漫长地折磨。成片成片的荻花向谦卑的我扬着飞絮。
而有的石头落入小潭,洗自己的碎骨,我的影子落入小潭,洗自己的虚像。更多的石头相互洗涤石头。有一部分石头,划着水去了。更多的我洗涤着我。有一部分我,化成水去了。没有一条河承认我从它的源头而来。我拾起潭中一枚鹅卵石,老树上的喜鹊嚷着说,我拾起了她的小肾脏。好小的一枚石头啊。我交给女儿,她握了一下,旋即敏感地丢掉。水有凉意,石头让她吃惊。
这几天长江水更枯了,似是有意送我去江心滩,信步至江水边沿,小风暗生,点水雀的身影若有若无,有块干净的长江石可坐,却不敢久坐。我不能确定,河床为人类让出半边卧榻,会带来什么。人声喧嚣,巨大的沉默是谁的?
把自己静置在这些长江石上,薄薄的淤泥,经春阳一晒就成灰,抺一抹,露出这枚长江石的暗绿来,坐在上面,看江生縠纹,把自己,静置成一个迢遥的谜。我和石头浑然一体了,圆滑上附着孤绝,隐喻里藏着旁白。这时别猜我,余晖改变了人世的答案。
这些石头,没有一枚是普通的。无论成分如何、来自何地,都值得我歌颂。就像歌颂我的外公,就像歌颂我。
头顶一堆石头,头顶大量的斑纹
和色彩,腰悬玉玦,心口
还贴着白璧
它是一块顽石,经过语言符号学的洗礼
成为拙石—意义逐渐丧失
声带逐渐钝化,近于无语
掀开周遭的众美,取出独美
荣耀如此黯淡
用长江水,洗干净,贴在我的面颊上
为孤独者钤印
我相信它曾为万世开先河,并习惯忍受奚落
——《拙石颂》
有一段时间,我执迷于在九龙滩上寻找我的石头的独美,然而,我找到的是众美。
后来我一直往江心逼近,似乎近在咫尺的石头会成为某种内心的答案。
两弯白石嵌进青石里,我要把石头洗出月光来,然后扔在浅水中,我可以把整片江滩辜负个遍。漫润在水中的石头有万种面影,波纹浮动时,影影绰绰,随手抓一块都是陛下,冠冕上晃动着骨节般的珠子。向大河称臣的,还有更圆润的那轮天上月,它早熟,直逼落日。
然而在暮光下,我终于看到石头的幻之灵了,似乎“神性”的石头化成了鲸鱼。
水位逐渐下降,春天逐渐逝去,大水到来之前,会把自己的枯竭最大化,让我以为河流已然在谦虚地向天空致歉。仿佛水不是水,大石头一波一波的,才是水,它们延伸至江心,有了水的形态和优雅。领头的那块,最先隐入暗浪里。
这些石头,带着大陆最后的劝慰,沉溺至此,只对大河的心脏保持臣服,它们推动着脉象,像一个鲸头领着一串椎形的骨头。我知道,这些石头,和武陵深山里的那些,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扮演诗歌的灵魂而存在。所以它们遇见我,牵引我,开示我。
它们与外公的石头,领略过同一片暮光。
这些石头入水的鱼跃动态,也是静止的,看上去在动,实际上岿然不动。每块石脊上可乘坐两人,小女孩带着我,仿佛要去渡江。
我们缄口,无声,水面起伏。
分明是石之鳍,在身侧不停拍打河流。
尾声
当我和女儿在长江石头鲸鱼上静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鲸鱼的石眼睛。这些石头活着的原因,我们找到了。当石头们行走数万年,行走三千里,来到九龙滩的时候,我知道,它们来看我们了。一大一小,两块弯曲的鱼形石头,各天生一只凹陷的眼晴,小女孩的半瓶江水倒进去,它们就眼波荡漾了,瞳孔一般,与天空对视,与我们对视,像无声的对话:
你是张远伦吗?
是啊。
你是谁?
我是李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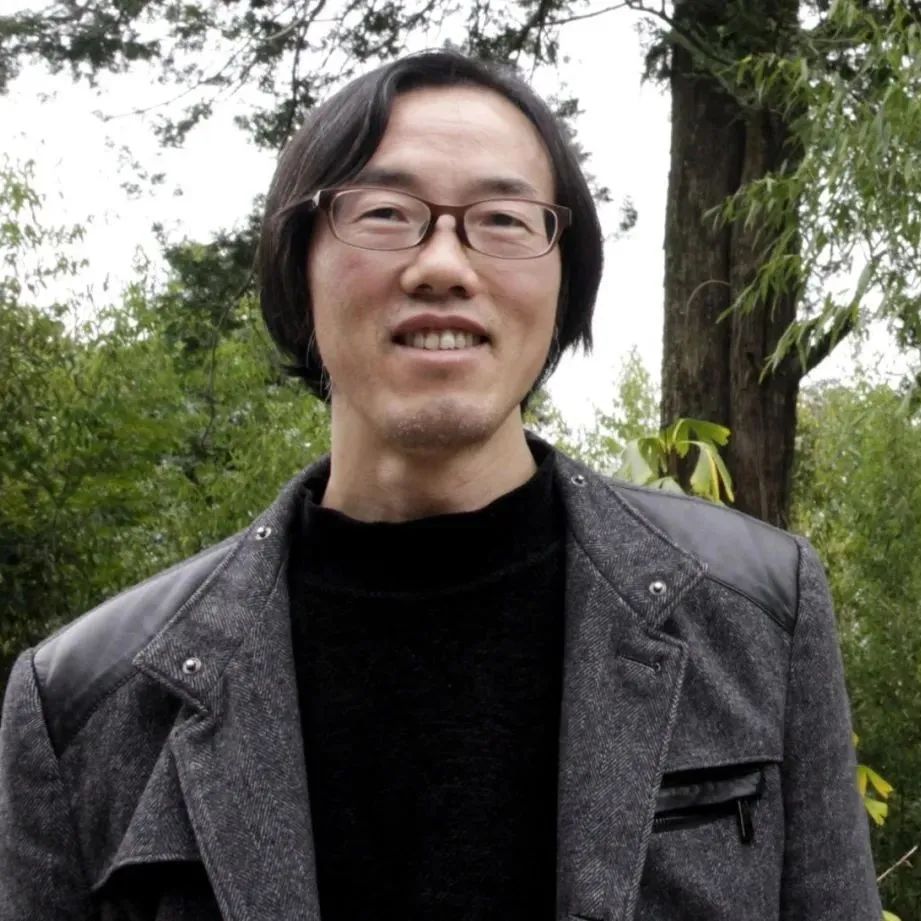
张远伦,苗族,1976年生于重庆彭水。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那卡》《两个字》《逆风歌》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奖、《诗刊》陈子昂青年诗歌奖、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银河之星诗歌奖。入选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