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孟祥:《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动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觉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动仍历历在目。
《讲话》发表以后,伴随着新秧歌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专业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个波澜壮阔的新说书运动,便很快在延安开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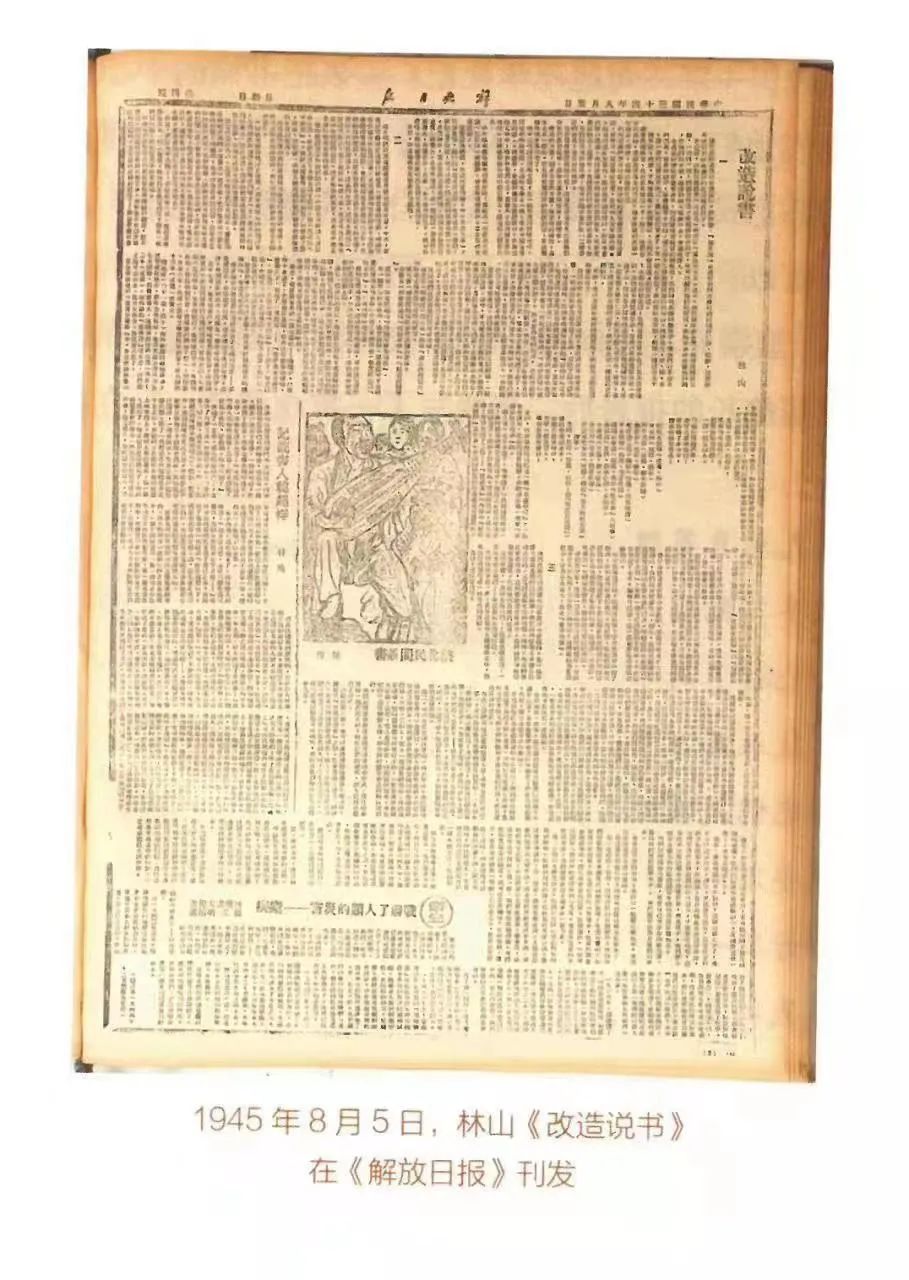
陕北的新说书运动,是在边区文协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首先得到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的支持。1945年4月,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由诗人林山领导。安波、陈明、柯蓝、高敏夫、王宗元等同志,都先后参加了说书组。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实践,逐渐探索出一条路,这就是: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艺人,启发、引导、帮助他们编新书,学习说新书和修改旧书。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是个别访问,选择对象,培养典型,然后通过他们来联络、推动其他说书人,并且采用个别传帮带和办训练班等方式,扩大说新书的影响。
文协说书组首先发现并培养了韩起祥。他们对韩起祥的思想、生活、创作才能、演唱艺术以及在群众中和说书人中的影响等等,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采取多种方式,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方法。
韩起祥在文协说书组的耐心帮助下,在短短的4个月内,思想上和艺术上有了飞跃提高。他在自编的《说书宣传歌》中唱道:“文协、鲁艺、县政府,奖励我来说新书,新书说的是什么?一段一段教育人。自编新书编不好,希望大家要批评!要知编了多少本,请看后面有书名:《红鞋女妖精》《反巫神》《四岔捎书》《掏谷搓》《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王五抽烟》《阎锡山要款》《血泪仇》《中国魂》《合家乐》《王志成吃元宝》《张家庄祈雨》。编的新书还不多,常编常说常增加,希望一般说书人:学习新书要实行!”不久,韩起祥又创作了颇有影响的《刘巧团圆》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曲目。于是说书组不失时机地带领韩起祥在延安办起了第一个说书训练班。随后,又在米脂、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等地举办说新书训练班。当时,全陕北有失明艺人483人,经过训练改说新书的就有273人。像绥德的石维俊、三边的冯明山、延安的刘之有、常栓等,先后创作、改编了《乌鸦告状》《地板》《平鹰坟)《抗日英雄洋铁桶》等新书。此外,陈明的陕北说书《平妖记》,李季的说书《卜掌村演义》,孔厥的唱本《人民英雄刘志丹》《一家人弹词》,戈西的说书《老麦菁偷麦》,拓开科的练子嘴《闹官》等,也都受到群众的好评。
韩起祥的演唱轰动一时,仅1946年9月,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连续8次发表了他的新作品并报道了他的艺术活动。特别是毛泽东、朱德请他去说书,更使韩起祥的名声远扬。

由于韩起祥带头编演新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再加上党报和林山等同志的大力倡导,陕北的新说书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全边区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运动。不久,这一运动又在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山东、苏皖等全国各个解放区开花结果。尤其是冀鲁豫解放区成绩更为显著,在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王亚平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毛主席对旧艺术“既不卑弃,亦不投降”的态度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对旧艺术进行了改革,总计受训的老艺人达千人以上,除对旧剧、旧说唱进行审查和整理改编外,还创作了新说唱词上百篇。像王亚平的《张锁买牛》、李刚的《二元成亲》、沈冠英的《未婚妻劝夫参军》、孟汉英的《济南第一团)等,都是当时脍灸人口的曲艺佳作。边区文联还编印出版了大众读物《新地》半月刊,在边区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区的新说书运动,从1945年春到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在历时4年多的时间里,据初步统计,仅广大民间艺人的曲艺新作,就有上千篇。他们无论是吹拉弹唱,还是说新编新,都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农村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讲话》指导下的新说书运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是思想改造和艺术改造相结合。从具体的艺术改造做起,结合思想改造,互相作用,互相提高,进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改造过程中,还注意及时给予鼓励和表彰。譬如:对艺人编演的新曲目进行评奖;优秀的作品给予发表的园地;对典型人物及时进行宣传报道等等。这样既能提高民间艺人对思想改造和艺术改造的积极性,又能进一步巩固所取得的成果,还能扩大新说书运动的政治影响。
其次,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相结合。新说书运动的兴起,打破了千百年来文人与艺人的长期隔阂,第一次使二者完全结合起来。解放区革命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结合,是以共同的革命目的为基础,所以他们的结合是自觉的、同志式的。只有这种“同志式”的结合,才凝聚着革命的战斗情谊。像林山与韩起祥的结合、王亚平与沈冠英的结合、何迟与王尊三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
二者的结合,使现代曲坛焕然一新,它大大推动了新说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间艺人与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不仅接受了进步思想,在艺术创作上也接受了新文艺的表现方法和写作技巧。而知识分子通过与民间艺人结合,一方面指导着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地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诗人艾青在《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一文中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学艺术的成绩,主要是学习民间得来的。例如秧歌、腰鼓、年画、新的歌曲、大量的快板、说书、大鼓词.....”。
再其次,新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讲话》发表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思想感情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文艺创作也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说唱艺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赵树理的小说。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最早是以“现代故事”来发表的。稍后的《李有才板话》,更是以他杰出的“板话"艺术,赢得中外读者的赞赏。他把说唱艺术与小说艺术融为一体,成为解放区民族化、大众化的一面旗帜。应该说,在解放区的作家群中,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像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王希坚的《地复天翻》,邵子南的《地雷阵》,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等等。这些作家或作品,或向曲艺学习结构形式,或向曲艺学习评书笔法,或向曲艺学习接近群众的口语化语言,或向曲艺学习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这些学习和运用,对于促使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是至关重要的。
新说书运动对诗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采用了陕北“信天游”的格式,阮章竞的长诗《圈套》,则自称是“俚歌故事”。至于张志民的叙事诗《王九诉苦》和《死不者》,那简直就与快板无甚区别了。与此同时,诗人王亚平则把鼓词视为“唱诗",而“孩子诗人”苗得雨,干脆就把大鼓词收进了自己的诗歌集。还有陶钝的长篇说唱《杨桂香鼓词》,马少波的快板《嵩潜庄》等。这种“曲词合一”的艺术实践,正是新文艺与民间说唱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1950年,韩起祥(左)与陕北说书《刘巧团圆》记录整理者高敏夫(延安鲁艺人)合影
此外,现代说唱艺术还对戏曲乃至绘画都产生了影响。众所周知,最早的歌剧《白毛女》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和民歌小调改编而成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曾影响了评剧《刘巧儿》的移植改编。新秧歌传到东北以后,又与二人转合二为一,从而产生了二人转秧歌剧。在晋察冀,相声与戏剧相结合,出现了一种“相声喜剧”。在冀鲁豫,坠子与戏曲相结合,于是出现了一种“坠子戏”。在山东,快板与小调相结合,又涌现出“快板小调剧”。在陕甘宁,说唱与绘画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支“艺术轻骑兵”新洋片。
说唱艺术一方面促进了新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另一方面新文艺又给说唱艺术以影响。像小说《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乌鸦告状》《平原烈火》《晴天》,戏曲《白毛女》《血泪仇》,诗歌《赶车传》等,先后被说唱艺术所改编。文学艺术的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正是《讲话》发表以后,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说书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曲艺队伍,并为社会主义新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说书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正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像林山、安波、陈明、柯蓝、高敏夫、赵树理、陶钝、王宗元、马烽、西戎、何迟、王亚平,以及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毕革飞、杨星华、曹永山等,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作家和民间艺术演唱家,有的还长期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工作。这批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先进分子,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说书运动的行列中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改变了曲艺队伍长期以来涣散无力的局面,代之以共产党员为先锋的无产阶级曲艺队伍的形成。这支曲艺新军,既是新说书运动的开拓者,又是社会主义新曲艺的建设者。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不忘初心,满怀希望,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行。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