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读些“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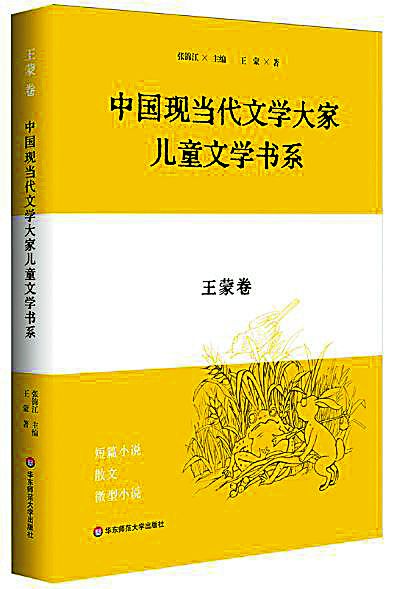
去年,为策划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儿童文学书系·王蒙卷》,我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王焰社长一同拜访王蒙先生,将已经选好的书目征求他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中国作协在烟台举办的笔会时,就与王蒙相识、相遇。2013年8月,我和他在北戴河做过一次关于文学的深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面缘王蒙》,应该说,这次见面是十年之后的重逢。
旧友相见,分外亲切。他说,他的耳朵听不太真切,让我们坐得近些。这是一个并不大的客厅。我们围着长方的茶几落座,我与王蒙贴邻,只隔着放台灯的圆台。茶几上摆有插着放大镜的笔筒、《新京报》等。王焰社长说明了来意,我拿出一张纸,上面是《王蒙卷》所选的书目。我研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的37卷本《王蒙文集》其中的《短篇小说》上下卷、《散文随笔》上中下卷,依据自己从事文学教学、创作、理论研究的经验,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短篇小说17篇、散文31篇,并向王蒙阐述了所选作品的评判和感受。
其中一篇是《无言的树》。作品写一株连名字都没有的平常的树的命运。这树从来不说话,但它是一个永远的沉思者,不想参与世间任何纠葛,却又被动地卷进了世俗的旋涡。一场灾难才使它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归于平常。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却写出了平常中的惊奇、深思、感叹。我认为,这是一篇貌似童话,又非童话的魔幻小说。一株树能有如人一般的思索情愫,是不可思议的魔幻,而其之所以有此魔幻功能,是在“当它长在一人高,并且被一只山羊啃了一口以后,它产生过这样一朦胧而温暖的思绪”,所有的情节随之沉浸在这株无言的树的魔幻思绪之中:它能听懂五米之外响杨的炫耀的“话痨”,它有对水的愿望,它能感悟到月亮、太阳、云、雨、雷、雪、虫、鸟、长出新的芽和蕾、叶和枝以及相恋男女的美好,它能体味到与风做朋友的喜怒哀乐,它听懂了人对它的审视、抨击、研究、指责,它能明白火红狐狸对它的挑衅……在这若干魔幻细节枝蔓的拥簇中,却跳不出一个现实“它从来不讲话”。因为“它从没感到过讲话的必要,从没产生过讲话的欲望,它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它自己的讲话能力。讲话能力的问题对于它根本不存在。”这根不可斩断的现实绳索,牵一发动全身,在魔幻的花团锦簇之中,使这个“它从来不讲话”的现实熠熠生辉了。
其中,还有一篇作品《坚硬的稀粥》,一看题目便是魔幻,世上哪有坚硬的稀粥呀?稀粥又是坚硬的,这是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王蒙用独创的语言、结构与情节,风趣、幽默地用第一人称(孙辈)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拥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高挑的儿子,以及那个“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徐姐”的大家庭主持家政、议决膳食维新,一本正经而又滑稽可笑、虚妄无边的荒诞故事。我脑海里立即跳出安徒生的《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王蒙的荒诞与这些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孩子们读来估计会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
在读《致爱丽丝》时,我的脑子如万花筒一般闪烁不定,闪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福克纳的《达洛威夫人》等。故事中,一个求教的文学青年愤怒于他的作品不能发表,临走留下一篇习作叫《绿色的太阳》,通篇一派胡言,东拉西扯,牛头不对马嘴,组成怪异的句式,像一个癔症患者思维混乱的疯语。作者借此巧妙地把世间不同的物质、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遭遇扭揉成一个魔幻的面团,可以让孩子们去思索、去破解,而“解谜”恰恰是孩子们最想做、最感兴趣的事情。
我们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认同和共识也越来越多。王蒙更加激动了,他变得年轻而有活力。我望着他泛红的脸,由衷地敬佩他在谈论文学时的精神气。在豪放高语的对话中,王蒙应允为这套丛书题写下这样一句话:“童年的阅读是最宝贵的”,并颇有兴味地问道:“你们在我的文集微型小说卷中选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再选选,有七八篇可选,特别是成语新编。”他兴致勃勃地讲了新编成语故事《刻舟求剑》《鱼目混珠》,在场人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也会喜欢这些可爱的小故事,乐意读,并乐在其中。王蒙表示,对于先选的一批篇目没有意见,并建议我们还可编一套世界名著作家的儿童文学丛书。回沪后,我重读了《微型小说卷》,果然遗珠不少,又选了十篇,编在其中。
王蒙的魔幻小说打开了儿童文学的另一扇窗户,我认定它是“别一样”适合孩子看的文学,也可说是“别一样”的儿童文学。魔幻艺术特征正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任何一种魔幻对于儿童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或有神秘的色彩,给儿童带来丰富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感受,这是童年美学的重要基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