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沐:从一粒种子照见人生
“可能是看中我吃苦耐劳的性格。”杨沐猜测。2019年9月,海南出版社策划了地方特色重大选题“南繁”。“这是一个涉农的冷门题材,在浮躁的当下,去哪儿找一位愿意下沉田间地头体验生活,踏踏实实下‘笨’功夫的作者?”总编辑谭丽琳找到海南省作协,希望推荐一位海南作家来书写。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考虑再三,找到了杨沐,对她说:“有一个写作项目可以采访袁隆平,你想不想接?”
杨沐如愿采访了袁隆平。2021年2月,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袁隆平,地点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育种基地。媒体报道中提及,袁隆平每天下午都会下楼,到稻田边走走。冲着报道里的话,杨沐“闯进”湖南育种基地。
这天,袁隆平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他居住小楼的二层走廊式阳台。小院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的杨沐,向楼上的袁隆平招手,“袁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海南的作家,写南繁采访过您。”
一、序章
在“南繁”的故事开始之前,是一段有关饥饿的往事。
1960年,北方大旱,土地裂开了口子,地里没收成。河南农学院农场试验田的玉米尚存,这片地不大,有机井灌溉,长势良好。这一季杂交玉米即将出成果,良种有望提升产量。玉米灌浆后,玉米棒时常丢失——附近的灾民饿得面黄肌瘦,有一回几个灾民偷玉米,和看守实验田的学生打了起来,打破了学生的头。
院长吴绍骙骑着自行车,赶到试验田。他不忍心处理灾民,对保卫科长说:“给他们掰10斤小穗、瘪穗,让他们走吧,打人的事就算了。”几个月后,吴绍骙才知道,自己家里也缺粮,一年多来,妻子喝粥,把饭留给了他和小外孙。吴绍骙感到心酸,自己育了一辈子种,结果家人吃不上饱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方大旱,南方水灾,我国经历三年困难期,出现饥荒。“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是饿死了人的。”袁隆平至少亲眼见过5个人饿死,尸体倒在路边、田埂边、桥下,他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说道:“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
那时,各地食堂时兴“双蒸饭”,指米饭蒸熟后,中途加水、盖紧盖子、上猛火,这样蒸出的米饭能多一倍。“双蒸饭”很松软,看着好像很大一碗,一吃就饱,不顶事,吃完以后,很快又饿了。“双蒸饭”水分多,吃多了会浮肿,有人往饭里加小苏打,米饭像面团一样发起来,不顶饿。
袁隆平在农村蹲点,因为吃不饱,站不住,双脚无力,出现水肿。生产队有一口大锅,用少得可怜的一点油抹一下锅底,再煮上一锅红薯藤,供七八十口人吃。年轻人饿得慌,跑上山挖带淀粉的植物根茎,用火烤着吃。睡前,他们都烤烤脚,把全身烤热了,再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袁隆平还是浑身冰冷,吃得少,身上没多少热量。
袁隆平喜欢游泳,高中时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大学时赴成都参赛,得了第四名,前三名进了国家队。这段时期,袁隆平不再游泳,哪怕住在沅江边,饿着肚子,游不动。他喜欢拉小提琴,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把小提琴。而此时,学生和老师饿得垂头耷脑,只顾着到处找吃的,渐渐地,袁隆平对拉小提琴也提不起劲儿。没有粮食,兴趣、尊严、道德,一切无从谈起。
作家阿乙写过一篇寓言故事《想学魔法的孩子》,浩宇出门冒险,被孕妇推到大锅里炖了,她用筷子捅一捅,确定肉煮至脱骨,才往锅里丢一颗不大的盐巴。这样的情节并非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阿乙解释:“在那个年代,外甥把舅舅吃了,舅舅把外甥女吃了,爷爷把孙女煮了,朋友走在路上没有回家,一定是被人敲死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吃树皮。”
二、采风
“事实是,人必须得吃东西,是吧?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人类没法存续下去。粮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杨沐在写“南繁”之前,没有如此深切的体会。她出生于1964年,自小在城里长大,她记忆中,虽然伙食算不上好,但也没饿过肚子。有天去超市,杨沐特地拐到粮油区,看到最便宜的散装大米一斤2块多,大米白花花的,颗粒饱满。她买回家蒸了一锅,很香,嚼着弹牙,有黏度,和网购的袋装大米没什么区别。
签出版合同前,海南出版社协调三亚市农业局等单位,希望他们为杨沐的采访大开绿灯,并开出介绍信,安排她去三亚南繁基地实地看看,确定有写的想法,再签合同。拿着介绍信,杨沐敲开了三亚南繁科学院的大门,住进了职工宿舍,由此开始了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采访。到了三亚,杨沐和当地人聊天,老百姓都知道育种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外省人来租地,种了几个月后,带种子离开。大家都说,“育种队来了”,但也仅限于此。这让杨沐震惊,老百姓都知道育种这回事,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在这里,杨沐见到了72岁的李登海。他一手拎着一袋沙袋,拿起来就走。常年暴晒下,李登海的头发呈现出玉米须状的焦黄色,他声音洪亮,操着一口夹杂着山东方言的普通话,能成段成段地背出《实践论》及马克思、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科学种田怎么搞?就按《实践论》上说的,先感觉,再总结。再感觉,再总结。”李登海能唱一整首《三百六十五里路》,他信奉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好日子不会找上门。
二十出头时,李登海是村里的民兵队队长、农科队队长。他向生产队要了一亩多试验田,按照《实践论》和专区农科所下发的栽培实用手册,带领20多个青年做试验。他们像妇女拿篦子篦头发那样伺候地,控制种植密度、浇水量、施肥量。整个夏天,买不起圆珠笔的李登海,用着路上捡的铅笔头,在小学生作业本上记录数据。玉米收获了,亩产400斤,平均增收100斤,公社书记带着李登海一行人敲锣打鼓向县里报喜。
1978年,李登海在海南扩繁“掖单1号”,培育出的“掖单2号”“掖单3号”亩产均超1500斤。1988年,李登海科研小组培育出“掖单13号”创造了我国夏季玉米最高单产1008.88公斤/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粮食供应出现缺口,粮价猛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业部提出用6年增产1000亿粮食,这一目标仅用2年超额完成。除了提升粮价,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之外,李登海及其全国科研团队培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粮食增产。
12月的三亚,玉米仍在生长。84岁的堵纯信和妻子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房屋被农田淹没。杨沐眼前的这片试验田有40亩,是堵纯信用奖金和积蓄自费租的。退休以后,他申报不了科研项目,但地还是要租的——做科研要有块地,没有地,一切想法都白搭。这位曾在1997年培育出玉米杂交种“郑单958”的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仍跋涉在育种路上。20多年来,“郑单958”长盛不衰,累计推广8.68亿亩。他还想更进一步。
长期以来,这对农科老人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在张掖种上一季,回郑州休整2个月,年底再来三亚种地。妻子劝说丈夫,年纪大了,别再种了,太操心。堵纯信笑着说:“那不中,地还是要种的。”堵纯信身量清瘦、手脚麻利、说话利落。在他身上,杨沐看到某种和植物相近的气质,“就像树一样。”农田里,有风过境,玉米叶沙沙作响。
三、挖掘
收集素材时,杨沐和100多位育种家聊过。他们来海南的经历,大多类似——坐一二十天车船到海南,用扁担挑着种子、日用品。当时,蚊虫蛇蚁在岛上横行,庄稼一不小心就被牛羊啃了,南繁人还遇上过地震、台风。这种景象让杨沐时常有一种垦荒的错觉——往日的南繁像一块被踩实的土地,她必须铲除杂草,刨出土块,挖出潮湿的故事。
杨沐完整地淘洗出程相文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程相文的经历的确具有代表性。1963年,大学毕业的程相文分配到河南省安阳专区浚县原种场。当地玉米穗巴掌大小,1/5不结籽,亩产不到200斤。这是种子退化所致。程相文选择北上,途经河北、山东、辽宁,至吉林,到各省农科院求良种。他没出过远门,蒸了75个馍晾干带上,穿着两件单布衫到了公主岭,又冷又饿昏倒在冬天的街头。路过的卡车司机把他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
1964年,浚县原种场计划扩繁“新双1号”,从无到有地在浚县推广杂交玉米种植。接到任务后,程相文打了报告,提出去海南扩繁。因为是双交种,他计划,夏天在浚县种一季,冬天在海南种一季,次年开春,新种子就能种在实验田里。领导问:“海南岛,冬天还能种庄稼?”程相文的大学老师师从南繁创始人吴绍骙教授,在课堂上讲过海南育种。县里同意了程相文的方案。1964年冬天,他只身挑着50多斤种子和50多斤行李,经过14天跋涉,登上了海南岛。
程相文租了8亩地,借了村民老夏家一把砍柴刀,上山连砍了七天柴,第八天扎好了茅屋。住了两晚,第三晚下大雨,狂风把小屋掀翻。程相文抱着种子跑到村里,老夏给他煮了一碗草药汤。程相文重新搭棚子,烧地、熏树枝,用木棍打了一张床。种子种下,出苗、长穗、授粉,到了次年春天,长出的玉米棒子出奇大。程相文更加谨慎,晚上住地里,防老鼠、防野猪。这一季种子运回浚县,亩产实现500~600斤。
1974年,浚县农科所成立,所里只有一名职工——程相文。除了扩繁,他开始培育新品种,1977年培育出“浚单5号”,1981年成立浚县种子公司。1990年,县农科所计划扩繁35万斤种子,70%是新品种“新黄单851”。1000亩“新黄单851”吸引来了年轻人强子,他想收购种子。程相文没答应,这批种子已预售给经销商。随后,种子装上火车车皮,运到浚县,被扣在火车站——强子举报这是一批假种子,工商部按程序查封。
预购种子的经销商扎堆儿闹上门来,要求退款、赔偿。程相文忧虑的是,35万斤种子长期闷在罐子车里有发霉的可能。县里紧急请来10名育种家,经鉴定,种子是真的。程相文没追究强子,他解释:“我们育种的都知道,对那些不好的苗子,只要把它淘汰掉,不选它就是了,没必要半途把它砍了。浇地施肥,也会有它一份。对农作物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强子由他去吧,我不会去打他这一棒子。”程相文像土地一样包容,这是他从土地里学来的。
四、如愿
杨沐第一次见袁隆平在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会场。会后,杨沐拿着一本《袁隆平自传口述史》,向袁隆平走去。她看完了自传,书上是勾画的痕迹。袁隆平问:“你是哪儿的?要写什么?”他有一个习惯,遇见生人,先问对方从哪儿来的,然后再聊别的。如果对方是育种专家,袁隆平会接着说当地适合种植的水稻品种,以及注意事项。如果是记者,他会提供报道思路。
第二次,杨沐去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集中采访了早期研究杂交水稻的几代育种家。她住在距离研究中心一公里远的宾馆,每天骑共享单车来回。小路蜿蜒,道边有古树,空气里弥漫着成熟的水稻香气。研究中心领导安排好采访对象,杨沐上午采一位,下午采一位,有时晚上也可以采一位。如果下午采访时间稍晚,她回宾馆睡个午觉再来。
研究中心门口有一片试验田,科研人员带杨沐下地转转。他们边走边介绍,地里没插牌子,但能一眼看出这一小块田种的什么品种,以及培育人。杨沐感到神奇。对从业超过10年的育种家来说,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水稻身上会带有育种人的气质。
杨沐在长沙待了12天,接近采访尾声,她争取到了见袁隆平的机会。这个消息让她振奋。见袁隆平的前一晚,她网购了一大束鲜花,怕鲜花第二天蔫了,半夜起来喷了两回水。次日一早,杨沐把鲜花放在单车前筐里,从大路驶进小道,轻快地驶向前方。
两三个月前,袁隆平在北京做了一个手术,见杨沐时,他处在休养后期。袁隆平的状态很好,看上去很健康,思路敏捷。在他面前,杨沐像被X射线扫过,她归结为老者的智慧,“目光很犀利,看了你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总体情况。”
袁隆平幽默,他的眼睛亮亮的,用带着湖南方言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对助理说:“你同意我接受采访了?看来我是解放了。”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袁隆平温和、亲切、健谈,交谈中,他很少提到种子问题。当时,袁隆平创新团队的科研目标是双季稻亩产超过3000斤。在杨沐看来,袁隆平考虑的事情都很长远,具有总体性,比如研发推广耐盐碱水稻。一旦出现洪涝灾害导致减产,马上在滩涂种一季水稻,粮食就能补上来。他思考的命题始终围绕,如何用水稻造福人类这一宗旨。

杨沐与袁隆平合影
2021年2月,杨沐在海南。听说袁隆平每天下午会下楼走走,到水稻田边看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育种基地。院子里,几排水稻育种盆放在水泥地上,椰子树特别高。杨沐徘徊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看出了她的意图,过一会,袁隆平从二楼的房间里出来,向下望着杨沐,清晰有力地说:“写南繁好哇。把南繁好好写写。”他又补了一句:“你是海南的,海南的,要把南繁好好写写。”杨沐目送袁隆平回房间。
当时,杨沐心里想的是,等书出版以后,把书寄过来。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袁隆平。3个月后,袁隆平逝世。
五、尾声
基于对杨沐的充分信任,海南出版社以极大的耐心坚持不催稿,但袁隆平的离世,让杨沐感受到时间的催逼。在新疆,杨沐见到了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吴明珠和袁隆平是大学同学,吴明珠的爱人杨其祐和袁隆平是室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吴明珠的世界正在坍缩,她能认出的人越来越少。说着话,她会忽然提到另一件事。但有的记忆,无法被时间带走。比如,助理说:“走,去瓜地。”吴明珠条件反射似的,拿起床边的一只小包,准备下地。杨沐感到时间紧迫,她要更抓紧。
推进选题的过程中,杨沐逐渐找到自己与“南繁”的联系。看着一场报告会的现场照片,杨沐发现投影上的一位老人有点眼熟,他是南繁奠基人、玉米育种家吴绍骙。1971年,6岁的杨沐扎着羊角辫,独自在红砖甬道上玩“跳房子”。这位路过的老人,停下来看了一会,教她“跳房子”的新玩法。末了,还跟她说:“回去跟你爸说,他俄语口语很标准。”
杨沐和吴绍骙住在同一栋楼里,当了几年邻居。她还小,没什么印象。杨沐的父亲杨再上大学时,被学校安排去讲习班当翻译。会上,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支持米丘林遗传学说,认为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产物。而吴绍骙的试验数据证明,自交系间杂交组合增产效果明显,该试验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基础。讨论不欢而散。
米丘林遗传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缠斗还在继续,育种家的命运也随之沉浮。几年后,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占据上风,吴绍骙在河南农学院实验农场种了20个品种,进行玉米杂交种的培育。当年11月,他把208个玉米自交果穗,寄到广西育种。育种家陈伟程曾是吴绍骙的科研助手,经他核实,异地培育应当从1956年春季算起。后来,“异地培育”被称为“南繁”。
杨再是养马学专家,在高校教书。得知女儿接到“南繁”的选题后,他格外关注,把报纸上相关的文章剪下来,整理好给女儿看。杨沐一回家,杨再就问:“写了多少了,还要写多少?”一年后,阿尔兹海默症找上了他,杨再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问:“杨沐在哪?她的书写完没有。”医院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书已下到印厂,她脱不开身。
杨沐预感,父亲正吊着一口气,等她回来。床前,杨沐汇报了喜讯,书出了,反响不错,《人民日报》发了书评,《求是》也计划摘一部分刊发。父亲的眼睛一亮,想了想,狡黠地说:“这么说,我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你喽。”家人笑了起来。那个晚上,杨再很有精气神儿,父女俩人说了不少话。接下来的几天,杨再清醒的时候很少,不再说话。
全家人商议,把杨再送到医院。几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提前为父母庆祝结婚纪念日。杨再很高兴,虽然说不了话,但能听懂,会看着人笑一笑,他感到幸福,眼泪慢慢流下来。子女做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几天后,杨再去世。他很平静,面庞舒展,皱纹、老年斑似乎一齐消失,脸是光洁的,像一个少年。
对话
杨沐& 江玉婷

Q:您如何构想《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一书?
杨沐:大家知道杂交水稻,但不知道南繁,“南繁”是业内人的叫法。南繁不只有水稻,还有玉米、高粱、棉花,包括鱼类。我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对南繁知之甚少。我国审定的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与南繁有关,南繁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底座。当我认识到南繁的重要性后,非常吃惊——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周围,我们居然不知道,海南省外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我想把南繁的简史写出来。就像一块版图,我想知道边界在哪里。从最初几个人来南繁,到一个大规模的育种活动,现在已经建成了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进入遗传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的阶段,这是一段延续60多年的历史。我还想通过几位科学家的南繁故事,展现整个南繁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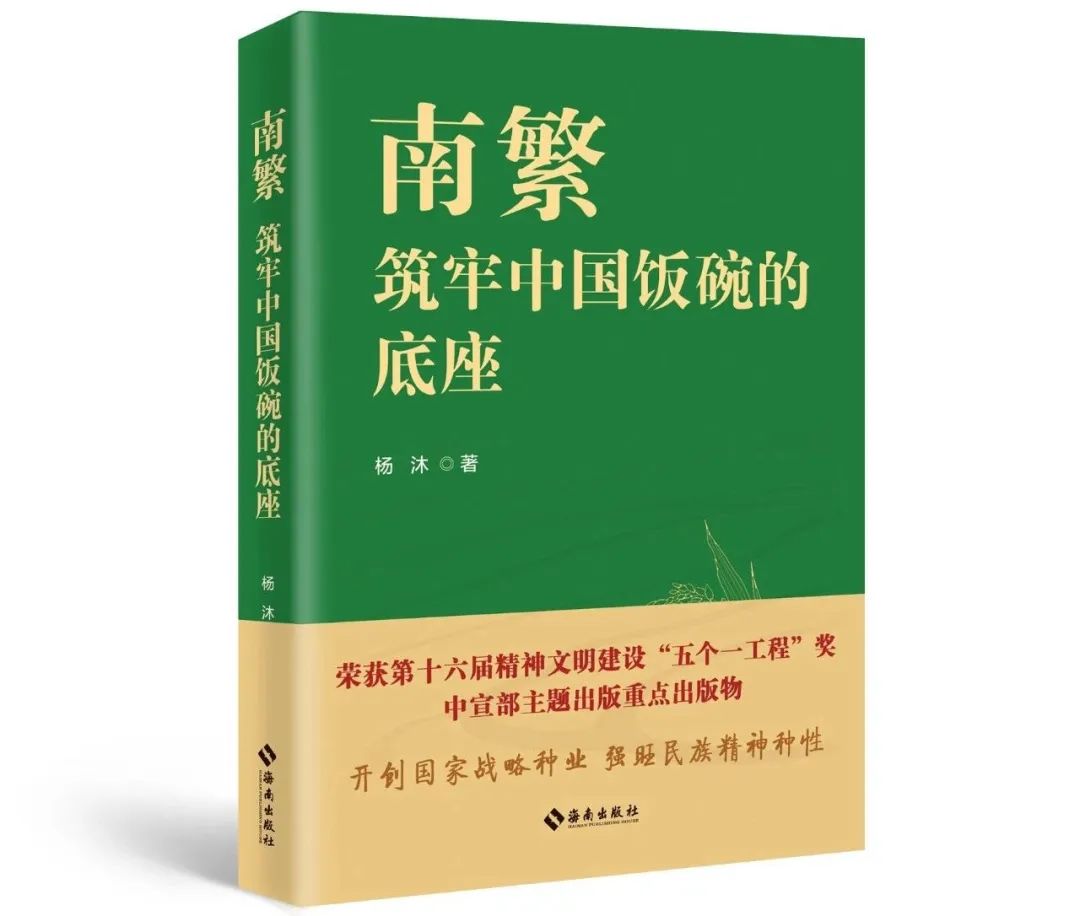
《 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杨沐著
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
Q:书中的体例不太一样。
杨沐:袁隆平、吴明珠、程相文等老一批科学家的经历,能够比较完整地挖掘出来,所以按照故事来写。写抗虫棉发明人郭三堆时,我们探讨了很多次,他不想写个人,把他工作上的事儿写上就可以了,所以按照对话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吴绍骙先生去世。我只能采访他的学生,通过他们的讲述,来写吴绍骙的人生。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吴绍骙是第一位利用南方冬季气温光照到南方做育种科研的人。我也这么认为。我看了吴绍骙科研小组当时的科研笔记,资料很扎实,还看了一些数据。写的过程当中,我反复核对事实。叙述笔调会根据育种家的情况以及我对他们的认识调整。
Q:您写了很多吴明珠在新疆的经历。
杨沐:如果只写南繁这一段,等于是从中间开始说,那样写不出一位育种家的成长。所以,我从头开始讲。她的初心就是育瓜,不要名,不计利。1983年,吴明珠辞去了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市长。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当副专员要在行政管理上花时间,瓜就育不好。后来,她把自己培育的西瓜品种“84-24”无偿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育种家,使这一品种在全国遍地开花且经久不衰。种子在市场上是明码标价的,现在一粒“84-24”种子2块钱。她将种子无偿地提供给其他育种家,让这些育种家进行本地化培育和推广。这种无私来自于她的初心,就是育好瓜,让更多人吃上她培育的好瓜。
吴明珠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说:“一年四季,我天天摆弄瓜,瓜棚就是我的家。如今,我丈夫病逝了,儿女远离了,我一个人还留在新疆摆弄瓜。人们说,我心里只有瓜,瓜是我的儿子,我会和瓜说话……是啊,瓜是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的确是这样。
Q:她培育的甜瓜,让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
杨沐:原来新疆的瓜都是原种。老百姓种了瓜,有一个瓜格外好吃,就把这个瓜的瓜籽留下来,第二年再种。原种会退化,过了几年,个头会缩小,或是长得不好看。原种量也少,在各家都是宝贝。现在新疆的西甜瓜又大又漂亮,都是杂交后的产物。
早期,新疆主要是种粮食,瓜不是主要作物。有一点瓜地,自家吃一吃,老百姓没把瓜当成商品来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了招待外宾,外交部礼宾司到新疆找瓜。这时,“红心脆”已经研发出来了,吴明珠找了20个让礼宾司的人带回北京。这次外交场合上,“红心脆”大受好评,名气打出去了。后来,有香港商人来订瓜,新疆才开始大规模种瓜,逐渐有了商品瓜的概念。
我快60了,我小时候吃不到哈密瓜。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去新疆出差,带回来2个哈密瓜,我们稀罕得不得了。当时,哈密瓜没法运输,用火车运出来得五六天,甚至更久,运的过程中,瓜可能就坏了。经过育种家改良,瓜更易储存,所以哈密瓜才能走出新疆。原来,新疆的瓜只能在新疆种,种子拿到别的地方种,种不了。育种家把种子拿到海南改良,现在瓜种之所以在海南、南宁、江苏等地都能种,正是因为经过了本地化改良。南繁影响了中国人的餐桌,粮食、蔬菜瓜果,包括肉蛋奶。
Q:怎么影响肉蛋奶?
杨沐:猪、鸡、牛、羊等家畜饲料的主要成分是玉米和大豆。单纯吃草长大的牛羊占比非常少。只有粮食足够了,家禽、家畜才能达到一定数量。如果粮食不够,饲料价格也会跟着涨,成本涨了,存栏量降低,肉蛋奶的价格就会涨。
我小时候,周围的人家不少有粮食不够吃的情况,特别是男孩多的人家。后来,粮票取消了,没有粮食不够吃这一说了。写这本书我才弄明白,正是杂交水稻的登场,杂交玉米持续地增加单产,加上小麦的增产,全国年人均口粮在350公斤以上,才取消了粮票。现在,人口在增长,肉蛋奶消耗得越多,背后需要的粮食就越多。粮食从哪儿来?种子在增产中的贡献率在45%以上,这是农业专家评估的数据。耕地就那么多,剩下的潜力就是水利、种子、农业机械化。灌溉、防病虫害、高标准农田,这些是粮食生产的温床,种子就是孩子。配套设施要跟上,孩子也要好。
Q:种子为什么要迭代?
杨沐:打个比方。一开始,粮食不够吃,育种家追求的是高产。产量上来了,需要苗子抗倒伏、抗旱,于是花几年时间,把相应的基因加进去,就出现一个抗旱、抗倒伏又高产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个高产的玉米品种,只适合在河南一带种,拿到四川种显不出高产性,所以,四川的育种家就要培育适合四川的品种。各省在海南基本都有育种基地,培养适合当地生长的品种。如今的南繁基地,占地26.8万亩,有800多家农业科研所、大专院校、种业机构登记注册,每年有超过8000名科研人员在这工作。
Q:看到杂交水稻那章,我觉得育种好难。
杨沐:采访袁隆平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如果他不求真,迷信权威,杂交水稻肯定要晚几年才能研发出来。一开始,袁隆平的研究很艰难,差不多是一个自发的行为。没多少人相信他会做成。1968年夏天,袁隆平种了700株秧苗,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赶到试验田,秧苗被人拔了,一株不剩。找了几天,学生说一口废井里漂着几株秧苗。袁隆平仗着水性好,跳下去救苗,捞出来一篮子,最后活了五株。
五株苗种下去,秋天收获了几百粒种子。他们带着种子到海南,秧苗插到地里没几天,就遇上台风,风大得把牛刮倒在水塘里打转,袁隆平还在地里。助手跑回去,把门板卸下来,用门板把秧苗运回去。1969年深秋,他们又去云南育种,浸种时发生7.8级大地震,房子震歪了。两名助手很年轻,袁隆平说自己好歹有两个孩子,于是争着进平房救种。他在这一批种子上花了好多年,他觉得种子比什么都重要。
袁隆平身上那股排除万难,一定要达到目的的劲头,令人敬佩。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打道回府了。当时还有余震,元江县原种站的老书记劝他们离开。袁隆平笑着说:“我们的种子已经催芽了,走不了呦。”师徒三人就地育苗,在操场上用油毛毡、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大冬天住了3个月。通过这几件事,我觉得袁隆平这个人物在书中立起来了。他就是这样做的。
Q:育瓜也很神奇。授粉后,瓜妞妞要保胎,人在棚里大声说话,坐不好果。
杨沐:在吴明珠眼里,瓜也有生命,和人一样。我向她的助手求证过,说话会导致空气震动,大声喧哗会影响授粉。授粉是育种非常关键的一步。到了授粉期,育种家喜欢自己授粉。如果外包出去,最后出来的成果和预期不一样,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早期的育种家都是亲力亲为。
我和育种专家聊了很多,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也在反观人的生命。我觉着,人真不用那么焦躁,那么傲慢,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人也就是一个生命。老老实实长,认认真真把自己长好,该来的,总会来的。
Q:您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杨沐:是这样。
Q:强子那一节,程相文说的话很有哲理。
杨沐:还有一个故事,我后来删掉了,跟育种没什么关系。一个年轻人想来农科所工作,没录取他,他怀恨在心,晚上往程相文家里投匕首。没伤到人,第二天查出来是谁干的。程相文没报警,他担心报警以后,给这个年轻人留下污点,以后的人生就不好过了。程相文让他写检查,告知他的父母,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工作,把矛盾化解。程相文在育种的过程中,也在培育自己,他在雕琢种子,也在雕琢自己。
Q:写书过程中,您觉得什么最难?
杨沐:书开始宣传的时候,开研讨会,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说:“杨沐的父亲也是农业科学工作者,她有农业基因。”我一听,我可吃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基因。
在此之前,我就觉得父母是大学老师,没觉得是农业科学家。他们回家很少谈工作,可能也谈,但我听不懂,就没在意。我确实是一个外行。关于育种的术语、理论要重新学,这是一个难点。如果我自己不信、不明白,就无法下笔。再一个就是,我并不知道,南繁的版图有多大,除了海南之外,和其他省的关系有多深厚。采访中,我就像慢慢学会一门新课。
书中涉及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是真实的,有资料佐证,或是有人证实。我写完的稿子,会给采访对象,或是相关人士核准,请他们批评。
Q:过程中,有一些事趣事分享吗?
杨沐:下印厂之前,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当时,我们在市政府开会,让市领导审读书里的重点人物。我就说,吃完饭,我们来拜访您。程先生可高兴。晚上9点多,我们出发,开了一个小时车,到了程先生那儿,聊了一会儿,11:00离开,回海口到家2点多。要改的是2个小问题,一处是水南村一队,不是村南村二队,还有一处是用“强子”当化名。之前,我取的化名带姓氏,程先生担心对号入座,建议把姓氏隐去。
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说,为了更正两个小问题,深夜开车拜访采访对象。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们都会很自豪,因为我们对待这件事很认真。车里还有海南出版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我们一起去的,都特别开心。
Q:《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得知消息时,什么心情?
杨沐:当时我在家里,写点东西。我们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出版社的几位编辑。编辑在群里发消息,我看到了,说好事,乐一乐,大家发了很多“鞭炮”的表情包。
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褒奖。我在写书的时候,没想过申报奖项,当时最渴望的是采访袁隆平先生。采访这两年,特别愉快,属于边走边唱,边采访边生活。我逐渐有了一种责任感,作为一个写作者,要为历史留下一份资料。每写一位老科学家的故事,就是在拯救一份记忆。为南繁写史,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在接到“南繁”选题之前,我刚给儿子办完婚礼,感到人生到了下一个阶段,想通过写一本书,把人生再拓宽一点,再踩实一点。这个时候,“南繁”的选题找到了我。当时我虽然对“南繁”了解不多,但判断这是个长期的大项目。筹备书的三年里,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小孙子出生了,生老病死,可以说都经历了。我的人生也更厚实了一些。
- 周习纪实文学《碧海金滩北戴河》出版发行[2022-12-17]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