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呐喊》:经典的诞生及辐射
原标题:《经典的诞生及辐射——<呐喊>初版百年纪念本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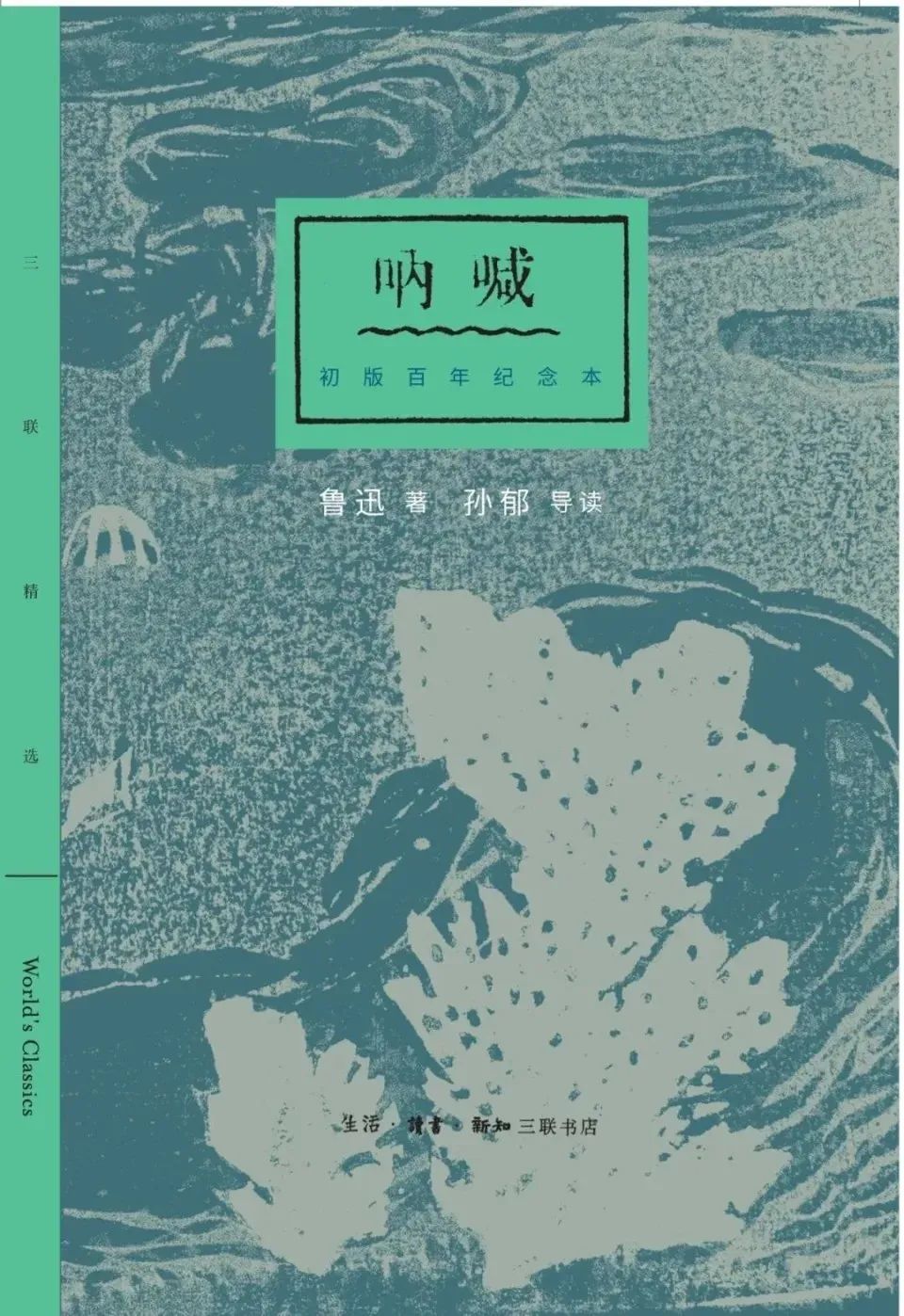
《〈呐喊〉初版百年纪念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一本书如果到了百年还被人不断阅读,那就有经典的地位了。《呐喊》之于文学史,就是一个例证。自从新文学诞生以来,翻译、改编和研究它的文本,已经汗牛充栋。而每个时期人们对于它的解析,似乎都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还引申出新的题旨。百年间,面对这奇异的文本,夹杂了无数不同的读者体验,各式理论也渗透其间。这在新文学史中,可说是十分少见的。
鲁迅最初的小说,发表于《新青年》,刚一问世,便被读者称赞,喜爱者甚多。那时候《新潮》《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都登载过他的作品,在文坛上是四面开花的。凡是接触这些作品的,都惊叹于那体例的别致和思想的异样,有一种意外之喜。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的同人写作,都是观念性的演绎,主要是确切性的思想的表达。而鲁迅的文字则沉潜在岁月深处,孤寂与热望的气流都有,流动着理性所难以描述的体验,旧中带新,暗中含明。那些不便说、难以说的隐秘,在他的文本里却一一出现了。
最早想出版鲁迅小说集的,是陈独秀。他在1920年9月2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就以赞佩的口吻说了许多自己少说过的话,并有意促成作品集的出版,那信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对于陈独秀而言,鲁迅的文本,拓展了汉语书写的空间,那画面传递的信息和背后的隐含,超出了他对于新文学的想象。这说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成绩,已经成为《新青年》同人值得夸赞的资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内心的喜悦都可以从他们的文字中看到一二。
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在北大新潮出版社出版,书的封面是红色的,毛边本,19.5厘米×13.3厘米。《呐喊》最初收小说15篇。它们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 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不周山》。1930年第13版时,作者抽去《不周山》,后改此小说为《补天》编入《故事新编》中。至今的篇目,一直保留着13版的样式,存小说14篇。到1936年,共印刷23次。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自己是被拉到新文学阵营的,写小说,也是别人催促的结果。在教育部时期,他绝望于故国的环境,对于以往的历史亦多有灰色的感觉,觉得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光明的地方。所以便一日日沉到时光深处,远去的历史也毒液般刺激着自己,精神是苦痛的。加入《新青年》队伍,他发现仅仅是悲楚地看人看事,与刊物氛围是不一的,便也将一种启蒙理念,偶带入文本之中。于是那文字就非笔直的延伸,而是弯曲的迂回。在迟疑中寻找着什么,荒诞里裸露着什么。那些无望的、冷意的原野的边上,也有花的抖动,预示着春的气息的存在。众小说幽深而扑朔迷离,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在凌乱的时空里,看得出,呐喊之声还是微小的。
这十几篇作品并非有意设计出来,而是随着自己的思绪慢慢流淌出的。彼此并无深的关联,题材也多样的,可以说是几十年经验的一种折射,还有研习国外艺术的偶得。只是它们都暗含在文本的后面,不易被察觉罢了。每一篇作品的审美背景,都含着不同内蕴,知识色调与诗意的符号是不同于旧派小说的。这里我们感受到了象征主义的晦涩,还有无数的写意之趣,内中有着无所不在的荒诞感,许多作品仿佛层层隐喻的叠加,在调子里多了变声。有的是乡村社会的聚焦,有的是知识人命运的揭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片影都有所呈现。作品集中还有些灵动超俗的主题,像儿时记忆的描述就让人想起童话的世界,清秀与微明间,闪动着夜间水乡美色。最为奇异的是还有着神话《不周山》这样的文本,茫茫洪荒里,流出灿烂的霞影,冰冷的世界诞生了未曾有过的灵光。天地万物,斑斓多姿地与读者见面了。
在从事小说写作之前,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精神准备。幼时读过不少古小说,后来还在大量的类书里钩沉旧小说片段,用力甚勤。留日期间,开始翻译域外小说,对于英法、北欧、俄国、美国、日本的文学都有所涉猎。不仅感动于域外艺术的特别,重要的是,摄取了近代哲学的许多营养。比如尼采思想,克尔凯廓尔生命意识,和托尔斯泰精神。以为惟有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才会有新的文明的出现。回国后,又多年沉浸在周秦汉唐遗物的趣味里,于出土文献和地方志中,体味到别样的审美传统。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思想发生着巨大的震动。挫折与自信,绝望和渴念,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既不像陈独秀、胡适那么慷慨激昂,也非章太炎、刘师培那么确然,而是在精神的荒原里流亡着。在小说的世界里,那些飘散于野地的气息,都聚于背景之中,而人物的气质里,多了士大夫们看不见的东西。
每读《呐喊》,都觉得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社会风俗的画家,描出了道道人间图景,也仿佛拥有上帝之眼的智者,透出世间的阴晴冷暖,晨风暮雨里,百物昭显。总体来说,这部小说集是鲁迅内心黑暗世界的一种释放,他早年对社会的绝望在此得以直观地呈现出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入木三分的写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在这些人物群像里,一切都是昏暗和无望的,人不像人,而仿佛是被驯僵的病者。作品背后,有一双通天之眼,看着凡俗间的不幸。比如《狂人日记》,就以疯子的口,说出仁义道德的背后是吃人。在《孔乙己》里面,写出一个被旧的教育制度所戕害的一个可怜的人,一些有趣的场景,里面是深层的悲哀,我们在这种简约的笔法背后可以感受到作者复杂的情感。《白光》延续了《孔乙己》的意象,但惊恐的气氛更浓了,那文字指示着旧式的文人之路无法走通。《故乡》写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流露出作者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渴望。《药》感慨于革命者与大众间的隔膜,解救百姓的人并不被百姓所理解。《明天》哀叹了小民梦境的无助,《风波》的风俗画面,惬意之笔下,有对于乡野之风的无奈。《一件小事》写出人力车夫心性的美,也衬托出知识人的“小”来。只有《社戏》辐射了一幅美丽的乡间图画,那里是有作家对古风的依恋和对童趣的依恋吧。
那些乡下人,无论是农民还是破落的读书人,心态都被奴隶式的病灶所染。鲁迅以医生的眼睛看他们,内心流溢着诸多悲哀。乡下人善良和麻木的表情,我们见了要倒吸一口冷气,美的陨落是人间大的不幸。鲁迅留日时代憧憬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情调,在此完全没有表达的空间,一切都还在古老的浑沌里。精神的痼疾乃人间大的不幸,在鲁迅看来,当这些痼疾盘踞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人是感受不到阳光的。
对于病态社会的描绘,在许多作品中是一个主调。小说集中表现了病、药、死的意象。在《药》中,华小栓已经病入膏肓,寻来的药竟是革命者的血染的馒头,但还是死掉了。这里,身体疾病和社会病,被鲁迅巧妙地置于一个故事里,作品就从旧文学里的一般性故事进入社会话题的隐喻性描述里。这个置放,是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研究会小说家所没有的,它不是一般性的技巧的问题,而是生命哲学的自如的流露,甚至多了迦尔洵、安特莱夫所没有的妙意。鲁迅把不相干的元素有趣地嫁接于一体,这是其审美思维的一种跨越。社会批判意识与审美意识的交接处,恰是其精神有机整体的一次诗意的绽放。
新知识人与老中国儿女的关系,在小说中也时可见到。与《药》比起来,《故乡》弥漫着最为动人的情愫。作者借着自己的经验,描述了回到故乡搬家的故事,少时的玩伴闰土已不复当年的英俊之气,而是被生活重压而变得呆滞,邻居杨二嫂的世故之影,衬托出故土本有的遗风。几个孩子的天然的样子,在此形成一种反差。以往美好的记忆被一种无可述说的悲哀代替了。每一个人物都很鲜活,而背后的沉重的忧思,则给我们无限的怅惘。这无疑是一首诗,离开故土的人,在少时的地方没有获得慰藉,反而生出悲哀之感。但那悲哀后的思考,对于人间希望的冥思,仿佛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带出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感悟。存在先于本质,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走,大约才是无意义的意义。
《呐喊》的讽刺笔墨,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也吸收了《儒林外史》的叙述笔法,对于人的存在的不确定性刻画得十分形象。有的作品也糅合进了作者自己的影子,比如《端午节》,就让人想起作者与胡适、钱玄同的关系,但主旨却是在写知识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尴尬。小说再现了新知识人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的无力感。《头发的故事》似乎不像小说,不过是杂文式的走笔,全篇都是对白,但对于国人的健忘的感叹,和辛亥革命苦涩记忆的表达,看出鲁迅在彼时的思想色调。对比作者批判愚民的语态,对于知识人的讥讽,也毫不弱的。《风波》将看似田园的乡下社会内在的暗流,很形象地点染出来。百姓价值观念系在皇权社会里,时光流逝着,不变的是人的奴隶意识,小说借着九斤老太太的口,也讥讽了进化思想对于古中国的不通。《兔和猫》《鸭的喜剧》在形式上都不太像小说,表面是童趣式的短章,其实也暗含着不少悖谬式的感觉。生命都有自身的限度,人的爱意可能也藏着残酷的东西,弱肉强食是生命界可怕的存在。鲁迅一面反讽,一面在荒诞的画面里照着自己的形影,内在的痛感,是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呐喊》中最有分量的无疑是《阿Q正传》。作品是发表于1921年《晨报副镌》一个“开心话”的专栏,这副刊原来是李大钊所编,后任者是孙伏园。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教过的学生,他搞了一个栏目“开心话”,找鲁迅来凑趣,《阿Q正传》就这样诞生了。开笔的时候,他说要写《阿Q正传》很久了,可见那形象在内心沉淀之深。作品始终带着幽默反讽意味,看得出对于彼时风气与环境的揶揄。高一涵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有人看《阿Q正传》连载,越来越担心,怕下一步该骂到自己了。小说发表时用的是笔名巴人,巴人是谁?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鲁迅以匿名的方式,快意地挥洒着笔墨,有意地与社会捣乱,和读者捣乱,忽地揭开被蒙在睡梦里的人们的被子,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出现在读者面前。
阿Q这个形象,用学界一般的看法,写了中华民族那种负面的东西。后来有人研究他,指出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这都不错,也符合鲁迅的思想。这个形象有朴素、勤劳的一面,也带着游民的劣态。他在未庄里没有地位,与人交往,既有朴实的一面,也染有狡猾与无赖气。不太会与人正常的交往,求爱的失败与在赵家人面前的失态,说明心智是扭曲的。他最大的问题是精神胜利法,欺人又自欺。在弱者的面前表现出主子的凶狠,在强人面前就是一个奴才。所以鲁迅最痛恨中国人多重角色和身份,在不同的环境下多没有定性,这是一种劣根表现。鲁迅写他,让人看到了人的奴隶相,自以为是,无特操,思维的模棱两可……这作品丝毫不是超功利的愉悦,也不是什么雅趣的散步,作者以大的悲悯之心,写出深的悲剧,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这样的吧。
小说有许多片段极为精彩,比如革命那一章,就赋予了小人物时代的元素,阿Q一看革命的风云起来,也要凑过去。但是他不知道那革命的指向是什么,朦胧地感到要打倒财主们,于是以为有了机会。不过他要参加革命的目的颇为可笑,暗想的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就是当年中国底层人的基本思想,千百年来农民起义的因由不过如此。可是几经变化,赵家的人和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便挨了哭丧棒。他回到土谷祠的时候,我们觉出了他的可怜,在这个等级制森然的社会,乡下的游民是没有地位的。小说的结尾,阿Q便被抓起来,最后被送到了刑场枪毙掉了。这个时候,在滑稽和可笑中,散发出强烈的哀凉感。怪诞的人以怪诞的方式生活,也以怪诞的方式死掉,世界不是为不幸者设计的。鲁迅写阿Q的革命,其实是对辛亥革命的一种回望,中国的革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可是在底层,参与者还是小农意识主导,充满了国民性的阴暗面。国民性不变,不管是共和还专制,照例不会收获幸福。
《阿Q正传》的笔法很有意思,作者用杂文的思维入文,传统小说的写意和现代小说的幽默之感交织在一起。结构不太讲究,却气贯始终。他用反小说的笔调为小说,就是让很多人想起了《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这样的作品。周作人说鲁迅的《阿Q正传》是受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日本的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影响,也不无道理。夏目漱石的小说是有反讽力度的,鲁迅延续了夏目漱石的某些思想,他们的作品是有相同的意义的。伟大的小说家都在司空见惯的人世间,见到我们常人不易见到的存在。阿Q是我们可怜人间的常态的人物,人们多视之不怪。鲁迅却写出其变态与可笑,在特定所指里,又多了发散性的隐喻。
《呐喊》是对于衰弱的民族的生活散点透视,不仅仅透出历史之影,也有指示着进化的艰辛。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生命被什么抑制住了。在这些风格并不统一的文字里,折射着作者矛盾而痛苦的情感,但有时候又能够以坚毅的目光,瞭望那些被遮蔽的领域。他笔下的未庄、鲁镇,成了老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集中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元素。作者画出了众生相,也描出各类人的心态。他移植了域外小说的心理描绘手法,也善于从中国古小说的笔调里吸收养分,叙述的方式灵活而多变。而他的审美意识也看不到儒家的说教气与道家的俗风,在入木三分的笔触里,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刺激了世人的思考。在那些不幸的、可怜的、无可救药的人物命运里,也镜子般照出国人自己的样子,但那镜子里的世界是破碎的,到处都是错乱与杂音,曾被扁平化的世界,第一次被立体化,且呈现出不同的侧面来。
鲁迅小说集一问世,喝彩者不计其数,很快就成了文坛的耀眼的存在。《呐喊》出版不久,《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媒体就作了报道。茅盾在1923年10月写下的《读<呐喊>》,就说了许多赞佩的话,认为作品奇异的文字背后的隐喻,超出了寻常小说的意味。他阅读《狂人日记》时,“只觉得受着了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徇绝的阳光”。同时又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这样的评价代表了读者的普遍感觉,内中充满赞佩与肯定的态度。1925年1月,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一文,对比了鲁迅与苏曼殊的作品,感到是全新的气流的涌动,文章写道:
我若把《双枰记》和《狂人日记》摆在一块儿了,那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前者是亲切而有味的一点小东西,第二,这样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呐喊》的地位。《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按:相)去多么远。两种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下来的人生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聚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但也有批评家对于鲁迅的小说提出批评。创造社的成仿吾在评价《呐喊》时,就以为过于写实,惟有《不周山》尚可,因为符合浪漫派的空幻之思。后来的郭沫若、阿英都曾对于鲁迅有些微词,说起来对于那文本有诸多隔膜之处。新文化人迷信自己所钟爱的概念,而鲁迅之于小说,恰是因了观念不能覆盖精神的非逻辑的一面。倒是审美的灵动的莫测之影,反到能触动存在的一角,那些被遗漏的图景,也被触摸到了。
创造社诸人疏远《呐喊》,有观念上的差异,他们视野里的文本,是被涂上主观的颜色的,客观性的眼光被遮住了。倒是一些了解鲁迅的人,看出那书里重要的隐含。在创造社成员中,只有郁达夫认可鲁迅,他曾说,“我对于鲁迅哩,也无恩无怨,不过对于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变的”。
而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于鲁迅的作品是十分入迷的。冯至《鲁迅与沉钟社》写道:
从《史记》、汉赋、唐宋古文转到鲁迅的《药》,是一个要费很大力气的跳跃。文字,当然比古文容易懂得多了,可是理解其中的涵义,并不容易(中略)此后,凡是鲁迅发表作品,我都找来读,有的自以为懂得了一些,有的并不懂。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小说中最短的一篇《一件小事》。我记得清楚,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寒冷的一天,我得到一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在课堂里听课时,我把增刊中发表的《一件小事》反复阅读,那人力车夫崇高的形象感动得我留下泪来。
这还是一般性的阅读感觉,尚没有上升到深入的思考里。许多年后,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就对《呐喊》中的十篇作品,作了专门的解析,每一篇心得,都有特点。他认为《呐喊》对于人的变态心理的描述十分深刻。《鲁迅先生的小说》写了笔下人物“被疯”“被禁闭”“被打”“被杀”“被吃”五个状态:
鲁迅先生用了上列的五项来说明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所身受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谁给他的呢?他们正是和他同国家同民族而且和他无仇无怨的大多数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苦难给他呢?因为他们愚蠢,他们受旧礼教的重压,年深月久,积非成是,生活得服服帖帖,根本不知道解放为何物,也根本不承认解放的可能,自然根本没有梦想到天下竟有人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为谋大多数人的解放而革命的事了。他们虽然和他无冤无仇,但是他竟要动摇他们服服帖帖的生活,他们于是要以上列五项办法对付他。
在表面上看,鲁迅先生用尽力是描写革命者的苦难,以反映大多数人们的愚蠢,伟大的同情似乎专注在革命者一方面。但是实际上,作者对于大多数受旧礼教重压的人们,只是客观地描写他们的愚蠢,并没有从心底里愤怒、憎恶、嫉恨的情感。反之,他的伟大的同情,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减少了分享的权利,也就是说,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贬损了他的同情的伟大。
鲁迅的被人喜欢,还因了那笔下的人物形象,与国人的日常所见所思相同,具有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身边的人物被那些文字召唤了出来。《呐喊》问世不久,大学生们就习惯于将小说人物与身边的人对应起来,一时形成一种风气。陆晶清在《鲁迅先生在女师大》一文就写道:
有些同学熟记了许多鲁迅先生的口语、名言、警句,常在讲话中引用,有时在和鲁迅先生讲话时也搬用态度语言。他笔下的人物,如七斤嫂、九斤老太、杨二嫂、闰土等等,我们选用作对几位同学戏称。阿Q的大名,常用来自称或称呼别人。
这也引起人们对于鲁迅那文本的好奇。胡适觉得是接受了日语、德语、文言的缘故,许寿裳感受到了野史的影子,周作人认为是域外作品影响的结果。多年以后,谈及那时的作品的出世,作者自己说,是受到域外小说的影响,那是夫子自道。从他的翻译历史看,译过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俄国的小说家的作品,尤以俄国小说最多。他受过托尔斯泰的影响,但在表现手法上,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对于他的影响更大。不过,那也是间接的影响,所以他自述时,认为尼采、果戈理、安特莱夫更让他注意。他说: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出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鲁迅的自述,也遗漏了知识库里另外的元素。郁达夫就认为,在俄国作家中,契诃夫对于鲁迅的影响也是大的。这是从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思想层面得出的结论。为什么说契诃夫对于鲁迅十分重要,而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含着不少未被注意的因素。通常的读者认为,鲁迅的精神气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更为接近。因为其叙述空间和时间观念,都是多维的,不确切性的。这也很像尼采所云的超人之眼。这里几乎看不到传统士大夫的目光,在陌生的笔触里,世界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但鲁迅身上的别样元素,郁达夫是感受到了,那就是与传统的关系存在一种纠结。纳博科夫就说,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传统的斯拉夫人,而契诃夫是与斯拉夫的传统是远的。端木蕻良在一篇文章里说俄国的一些作家像是病人,而鲁迅却是一名医生,这道出了鲁迅与一般作家的某些区别。从这个角度看,《呐喊》《彷徨》等作品所以有巨大的魅力,与那文字背后的非儒家元素有关吧。
1924年,鲁迅的小说就已经入选到中学语文课本,后来也成为大学教员研究的对象。但鲁迅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选入课本,有一种悲哀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是有毒的,对于孩子并非合适的阅读对象。可是那时候的新文学,多还在单一的逻辑里表现现实,可谓是一览无余。而鲁迅的作品则于凡俗里流出深渊的幽思,片段中折射着无量的悲苦。有时候似乎是一杯苦酒,传递到每个神经末梢,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让人在瞬间有了蠕活的感觉。北大的学生顾随在致友人的信中就说:
契霍甫(按,契诃夫)有云:人,谁也不是托尔斯泰呀!若在中国,则又当云:人才一作文,谁也不能立刻成为鲁迅先生也。
对于鲁迅的小说,翻译界的反映也是快的。1922年,《孔乙己》就被译成日文;1925年,敬隐渔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1926年美国华侨梁社乾将《阿Q正传》译成英文;1927年,朝鲜人柳树人把《狂人日记》译成朝鲜文;1929年俄国翻译家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在列宁格勒推出俄文版《阿Q正传》;1936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鲁迅建立联系,开始系统翻译《呐喊》,次年在布拉格出版。在众多的译介中,日本的译者人数最多,态度都很认真。日本学者、作家欣赏鲁迅者,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文字。比如作家佐藤春夫在1932年写下的《<故乡>译后记》中说:
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者生涯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诱掖指导建设新文学的运动,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中略)1921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在今天,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译本。鲁迅是世界的。
按照芥川龙之介的看法,佐藤春夫是一名带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他的文字有“世纪末的情绪”。他的看重鲁迅,也许是从作品中嗅出灰暗的气息,以及爱意的力量吧。而这背后还有穿越现象对本质的透视,这才是别人不及之处。日本人对于鲁迅的喜爱,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他们或许在这位中国作家的文本里,看到了岛国的某些影子,或者说,在那面镜子里看到陌生的自己。但中国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于《呐喊》的理解则是另一种样子。本土的纠结,一直没有散去。而日本人则感受到那文字散出的,东亚式的谶语。这是中国大陆学者许久没有意识到的。鲁迅的世界性意义,多年后才被国人一点点谈及。
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于鲁迅的评价,似乎都没有日本学者和作家那么深刻彻骨。罗曼·罗兰与法捷耶夫对于鲁迅的评价都是印象式的,但日本知识界发出的声音似乎缠绕着更为复杂的隐喻。这大概触及了东方人敏感的神经,帝国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之痛,于思想自新过程的艰难也于此可以见到许多。鲁迅翻译过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等人的作品,内心对于一些意象未尝没有亲切之感。这里涉及“文明”“开化”“现代”“解放”诸多话题,2008年,我在鲁迅博物馆与大江健三郎有过一次交谈,听他谈对《呐喊》的理解,才明白日本知识界欣赏鲁迅更为深切的原因。
无数的读者亲近鲁迅作品,不仅仅是那东亚式的困境的描摹,也非俄罗斯气息的流转。在鲁迅那里,外在于东方人的哲思是显而易见的。在无数可感的、悲剧性的画面外,站着一个清醒的审视者,那上帝般的眼睛穿过世俗社会,直逼精神的痛点。在《呐喊》的众生相里,少有醒来的个人,多是“无信者”的木然和病态。世界被舍斯托夫所说的“天然无知者”所充塞。但是鲁迅又克制着自我形象的过多投射,而是尽力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自己活动与说话。就如卡尔维诺所说:“以众多的主体、众多的声音、众多的目光代替惟一的能思索的‘我’”。这构成了个体的知识人与众生相的复杂关系,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记录,而是一种选择。是进入苦难者内心而拯救的悲悯。这种情调在儒家与道家的世界里没有,倒是与基督教与佛教的某些精神相近,但鲁迅又不是基督徒和佛教徒。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另一个审美意识的闪动,这是以往的中国小说家里没有的存在,而这些,恰恰镜子般照出灵魂里的原色。
新中国成立后,《呐喊》研究日趋深化,所涉猎的范围,既有辛亥以来的文化经验,也有对世界文学格局的思考。陈涌以苏联文学理论为参照,讨论的是鲁迅的现实主义问题;而王富仁的博士论文则受列宁对于高尔基评价的影响,认为《呐喊》是反封建的一面镜子,后来的汪晖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哲学的理念,从“反抗绝望”看出鲁迅的精神气质里诱人的动因;不久王乾坤在《鲁迅的生命哲学》里思考了有限性的问题,就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碰撞在一起。严家炎、高远东、吴晓东对于鲁迅的小说也做过不同的解释,其中高远东的《呐喊》研究说得颇为深切:
鲁迅的小说产生于文学和文化典范转移的革命时代,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不同写作规范的“两面夹攻”;其思想和心理发生的过去的经验与肩着传统文学的种种陈规“闸门”而从事新文学创造的矛盾,决定了他为现代小说乃至现代文学重建文学范式——作为经典的意义,主要表现于语言、思想、形式等方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创造性上。他的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品格和现代性正是这种创造力的结晶,这也是当今鲁迅小说的价值之所在。
当年出版《呐喊》,鲁迅不过是呼应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希望以此敲敲边鼓,让更多的人醒来。虽然后来说,自己的写作,是反映人生,而目的在改良人生,但他对于文字的效果如何,并无把握,他也曾表示,并不奢望那些作品永传于世,希望它们能够速朽。倘若自己攻击的对象与那文字一同消失,其任务也算完结了。可是时光过了一百年,《呐喊》依然是不断被阅读和叙述的文本,一些人物还被标签化于日常的口语里,因此,说他的文字已经融化于国人的血液里也是对的。先生曾希望燃烧后的灰烬永逝,但那光泽却在广远的地方扩散着,依然呈现着存在的不可思议之状。这是怎样的耐人寻味。鲁迅的形影伴着数代青年,迎着浪头赶去。那路有多长,先生的影子就有多长。一个敢于喊出自己心音的思想者,是无所畏惧的,《呐喊》就这样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勇于寻路的人。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