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家访谈|刘亮程:穿过史诗的丛林,说出自己的第一句话
编者按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旨在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四十余年来,茅盾文学奖高扬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持续奖掖中国当代文学杰出作家作品,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恢弘的发展历程。2023年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将陆续推出五位获奖作家的访谈,敬请关注。
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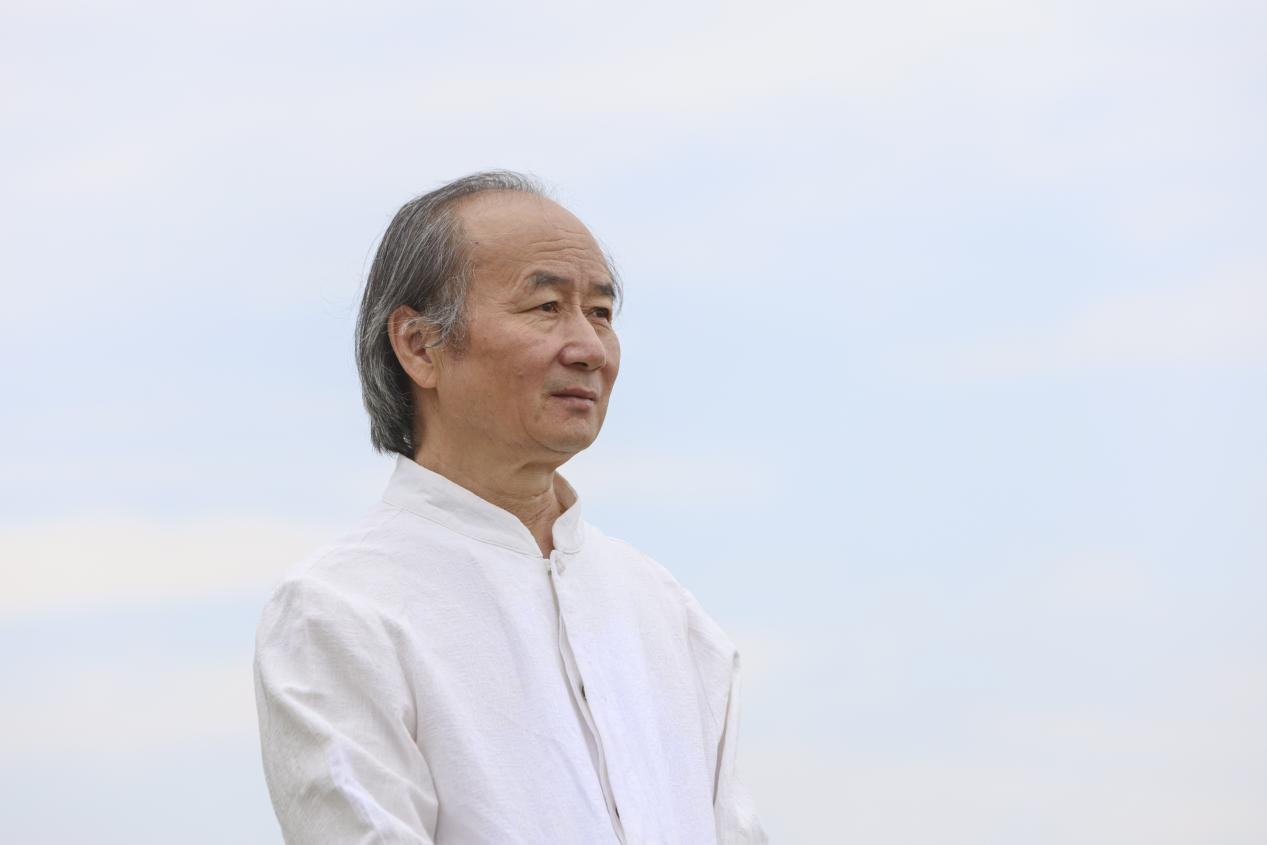
作家刘亮程
接受采访时,刘亮程反复谈到“故乡”。
“本巴”在藏语中意为“宝瓶”,是每个生命的故乡:是史诗英雄们要回归之处,也是小说中为救哥哥被迫降生的赫兰一心想回到的母腹。在小说《本巴》的设置中,“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醒来是我们可以随时到达的家乡”,人们在梦醒之间不断回乡。刘亮程的《本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三个意象:时间、游戏和梦境。史诗中原本残酷的战争和波澜壮阔的东归历程,在《本巴》里更多呈现为过去和现在、梦醒和虚实之间的穿越、融合,在现实经验、史诗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天真且富于哲学意味的本巴世界。
对刘亮程来说,故乡必然也指向他所生活的新疆多民族文化传统,是他脚下所立足的土地。在史诗发源地,他听着年迈的江格尔齐苍老的说唱,萌生创作的念头;在史诗结束的地方,开始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讲述。他更强调作家要认真面对家乡、土地和其中的生活,那是对作家影响至深的地方,也是他们通往世界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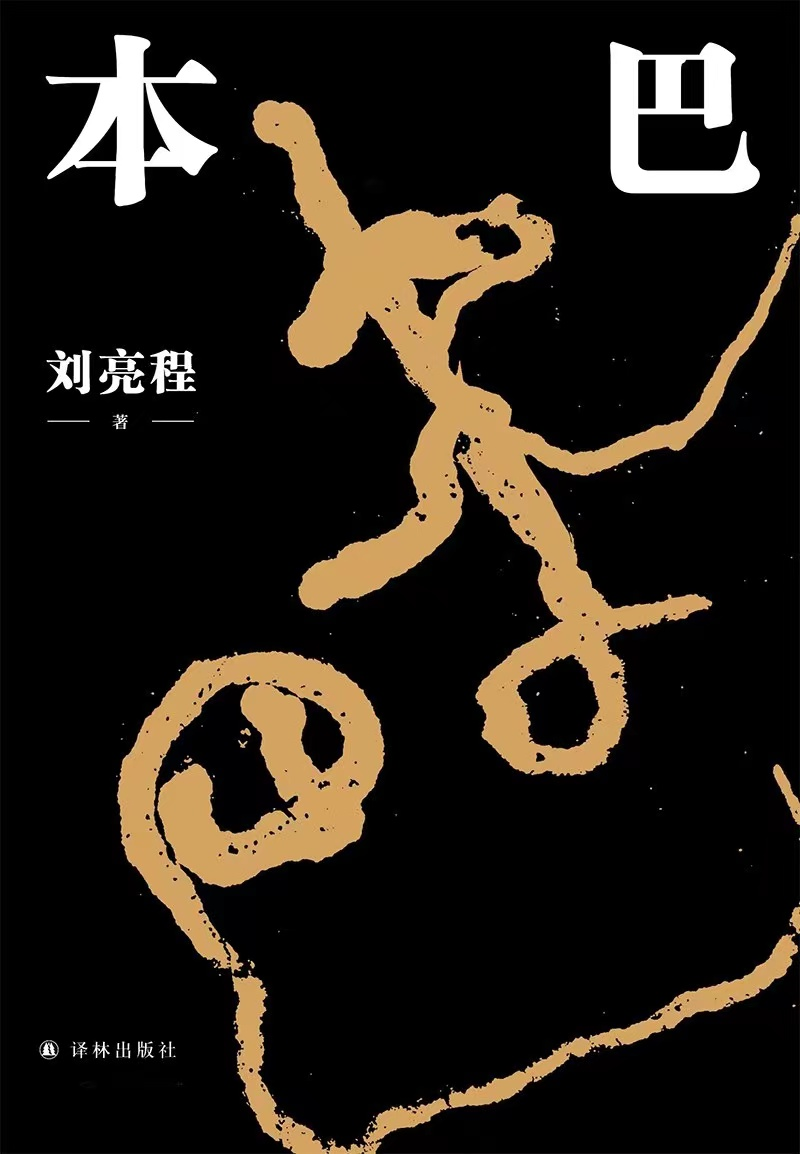
现代小说面对史诗是有难度的
中国作家网:《本巴》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会对史诗传统情有独钟?
刘亮程:我跟《江格尔》史诗结缘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我的工作室获得了一次到史诗传承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旅游文化的机会。《江格尔》《玛纳斯》等史诗很早就被翻译成了汉语,我们也有机会阅读,但正是这次田野调查让我有机会与史诗传承地的那些江格尔齐见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草原之夜听江格尔齐演唱《江格尔》。黄昏时候,远远近近的牧民骑着马缓缓而来,围坐在毡房中,簇拥在江格尔齐身边。江格尔齐操着苍老的嗓音,开始颂唱。在那样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虽然读了很多遍《江格尔》史诗,但我都没有走到史诗世界中去;而老江格尔齐的颂唱,瞬间就把我领进了辽阔遥远的史诗故事中。那样的时刻,《江格尔》史诗中所讲的一切都浮现在我眼前:人的影子和远山的影子走到一起,天黑和大地融为一体,人坐在漫天繁星中间,坐在虫鸣四起的草原上,你可以跟遥远的祖先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万物神灵沟通。
我写《本巴》时,脑海中常常想起的是那个老江格尔齐在草原之夜说唱的情景,一段一段,一句一句,把天说黑,又把天说亮。《江格尔》史诗所以传承数百年,是因为其自身的魅力。在创作《本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民族的说唱空间。但作为一部现代小说,我又必须要穿过《江格尔》的丛林,在古人想象力的尽头展开自己的天地,在那些百万行史诗的尽头,说出自己的第一句话。这是现代小说面对史诗的一种难度——我们不能重述史诗,她已经是神圣的存在了,但作为现代小说家,我们必须在史诗之外找到自己的语言、想象和结构一部小说的方法。
比如,如何重构史诗中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江格尔》中,人人活在25岁,但是如何让人人活在25岁?史诗属于神构,它言出法随。而作为小说家,“人人活在25岁”必须有其内在逻辑。我在《本巴》中通过“搬家家”“捉迷藏”“做梦”这三场游戏来“改变时间”:如果一个人不想衰老,可以在搬家家时一路走回童年;也可以在捉迷藏游戏中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本巴》本身就是一场梦,如果你觉得生活过于真实,那么最后你应该知道,你所在的世界其实就是一种讲述,是一种讲述中的生活。这就是本巴的缘起。
中国作家网:《本巴》从民族传统出发,讲述了关于时间、生命的故事。您常年生活在新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亮程:《本巴》是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创作的一部现代小说,它也是对江格尔史诗的致敬之作。本巴的语言之所以有如今的面貌,也是受到史诗说唱的启发。这种致敬也包含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致敬。我只有在新疆这样的环境中可能才会写出《本巴》。新疆多民族的文化生活滋养了我,多年来也滋养了我的文学创作。《本巴》就是对这种滋养的回馈。我最喜欢读《江格尔》《玛纳斯》等民族史诗、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哈萨克族的达斯坦长诗等。这些各民族文学传统作品中,有我们感受到的生活,看到的山河。所有属于新疆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那片土地上的原生故事,在那样的故事中我读到了现在依然流淌的河流的名字,看到一代代故事所发生的辽阔的草原、戈壁、沙漠和几百上千年的历史。
“面对半睡半醒的童年之梦”是我小说的主题
中国作家网:有评论认为《本巴》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体意识,您怎么看?
刘亮程:《本巴》是梦幻主义。《本巴》出版后还曾获评科幻小说的奖项,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梦幻的小说,从头到尾写的都是梦。讲述本来就是梦,被江格尔齐讲述的那个史诗世界也是现实世界对面的一场梦。在讲述的世界中,人们仍在做梦,是一重又一重的梦构筑起了本巴世界。
这么多年来我的小说都在写梦,写童年之梦。《本巴》也是这样,营造了一个梦的世界。一个5岁的江格尔齐,在东归途中惨烈的一场场战争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部族正踏上漫长的充满血腥和屠杀的回归之路,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但他不想再重复原有史诗中的英雄征战故事,因为战争就发生在眼前,他的部族正遭受战争屠戮。在这种情况下,他讲了另外的故事——一个童年的故事。故事中人人活在25岁,如果不想生活在此时,便可以退回到童年,用一场又一场的游戏去改变世界。讲述变成了一种手段和工具,一种面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小江格尔齐的讲述鼓舞了战士们,讲述改变了现实。那个史诗中被虚构的英雄,帮助现实中的人们走出绝境,回到了故乡。
在《本巴》的设置中,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醒来则是我们可以随时到达的家乡,当我们清醒时,那个遥远的梦成为了一处人人都渴望奔赴的故乡。在梦与醒之间往返的“回乡”,便是《本巴》所营造的梦幻世界。
中国作家网:读《本巴》时能感觉到它的浪漫主义和梦幻的一面,我在阅读时想过,或许它也很适合孩子,您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一种属于人类童年的天真。
刘亮程:“面对半睡半醒的童年之梦”,是我几部小说共同追求的主题。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塑造的是一个5岁的孩子在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一生都被整个村庄的人所过了:那些六七十岁的人过着他的老年,四五十岁的人过着他的中年,二三十岁的人过着他的青年,连出生和死亡都被人过得干干净净,只给他剩下了一场场的梦。《本巴》延续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童年的关注。
童年是我们的陌生人,因为它越来越远。但是人生的许多记忆,比如我们对世界的第一次感受——当我们睁开眼睛,降临人世的瞬间看到的太阳,领受到的清风,以及月光、花朵等等,这些人世初年的感受都储藏在童年中。还有我们在童年岁月中所经受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恐惧、惊喜、欣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这样的作家着迷。每当我写作到极致,或者写到最深情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是在为童年写作。我内心中一直养着一个未长大的孩子,每当我进入最深入的写作时,他就会醒来,从内心中浮现,左右着我的思想。
诗意地构筑所在土地上的故事,它就具有了世界性
中国作家网:《本巴》在语言方面也明显体现出吸收民族文化养分的特点,适应民族史诗为背景的故事,有一种创新性和异质性。请您谈谈在不同文体的写作中对于语言的探索。
刘亮程:我最早是一个诗人,后来创作散文时,其实是在用诗歌的语言写散文。再后来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才发现,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写诗时都没完全找到的无边无际的诗意。可能我跟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就是,把诗歌意象经营成了小说故事,用诗歌的语言写小说。
在我看来,万物有诗意才有文学,我很难去写一个没有诗意的故事,诗意是我对文学的最低要求。
中国作家网:您怎样看待文学与故乡和世界的关系?
刘亮程: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没有世界文学的概念的。我仅仅是在写我的土地上我的故事,这块土地和我的故事自成一个世界。一个作家所需要面对的恰恰是这些而不是整个世界。当你认真地用想象和文字构筑一个完整的自己所在土地的故事时,它就可能具有世界性。
我们不会单独去面对整个世界。每个人所面对的家乡都是小的,但这个家乡连接的是整个大地。当你从这个角度去书写时,故事可能就有了无限的延伸意义,它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语言中。
我也读过很多被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后来开始写作时我发现,所有这些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的影响加起来,可能没有家乡的一场风对我的影响大。你最终面对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会发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那里的生活,包括一场风,呼啸着从远处刮来的时候,那场风其实已经跑遍了世界,然后吹过你,又带着你家乡的声音,朝着世界他处呼啸而去。这是文学,也是一种传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世界中——一场风就把我们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受访者简介:
刘亮程,作家,新疆作协主席,居新疆。
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本巴》等,有多篇文章收入全国中学、大学语文课本。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013年入住新疆木垒,创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任院长。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