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情感和想象驻留在密林深处 ——访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童年生活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受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滋养。1968年底,他回到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分支,在长达十年的森林狩猎生活中造就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知世界的能力。这片土地也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沃土。《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老人与鹿》获得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0年,他返回呼伦贝尔生活。1990年代末开始,乌热尔图及其创作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乌热尔图被评论家称为“鄂温克族的第一代作家”“聪慧的文学猎人”……他出版多部中短小说集、随笔集及文史类作品,其作品被译为日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近日,内蒙古民族大学教师王妍对乌热尔图进行了专访。

《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
“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只要你说出一条小河的名称,鄂温克人立马就会知晓你的具体方位”
王 妍:从1976年开始,您用原名发表处女作《大岭小卫士》,至1993年发表《丛林悠悠》后终止了小说创作。其间,小说书写多围绕鄂温克族“森林狩猎生活和人民的历史命运”,以及森林中的生灵。王愿坚先生也曾评价您“把诗的意境、画的气韵和音乐的旋律都溶进了小说”。您能谈一谈当时的写作状态吗?
乌热尔图:我在森林里生活多年之后,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猎手。到了1973年,我担任了敖鲁古雅乡的宣传干部,这期间接待了许多来此采风的记者和作家,他们鼓励我把鄂温克猎人的故事写下来,于是我开始尝试写作。当时能找到的书刊很少,我先是读了一部童话,后来是一些短篇故事,这段阅读经历影响了我创作之初的结构方式,我喜欢用短小精悍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回顾当时的写作状态,实际上有很多潜在的东西,譬如情感的来源和生活经验的累积,这些都与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嫩江河畔长大的,小时候非常贪玩,整个小学期间每天都要到河里去游泳。那时候,我迷恋荒野山川,整日到河套里玩耍,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这种忘情地玩耍,对早期智力的发展十分重要。
王 妍:是的,与大自然建立情感联系的奇妙感受,延续到了您的小说创作中,构建了一个迷人的天地。当时您除了玩耍,也特别爱读书吧?
乌热尔图:读小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什么藏书。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认了一些汉字,可以自主读书了,便把阅读的愿望告诉了父亲。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父亲领我到旗里的图书馆去借书。到了那我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要看什么,只是随便找了一本儿童故事书,书名早就忘记了。虽然我阅读愿望是挺强烈的,但不好意思再麻烦父亲,毕竟他工作很忙,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去借过书。到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造句和作文竟得到班主任的夸奖,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王 妍:对于研究者而言,作家的处女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您的处女作展示了森林中狩猎民族的生活细节,语言也很有诗意。那篇《大岭小卫士》虽围绕抓特务的主线,但不乏灵动的童趣,为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我发现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具有标识性或充满象征意味的动物意象。例如,您刚开始写作时,多次出现小鹿、松鼠、狗这些比较柔软、灵动的小动物,而且您对驯鹿和熊也显得尤为钟爱。这些动物意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乌热尔图:在我看来,写小说要把文化的厚度和独特性表达出来。在初次写作或描述具体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写到一些动物,小动物以及大的野生动物。事实上,民族题材是有其特殊性的,鄂温克族的文化属于狩猎文化,与游牧文化有些区别,我们离不开森林里的动物,所以特别在意挖掘和利用动物的象征意义。细说起来,首先关注的是鹿,这里指的是野生马鹿,例如鄂温克萨满头上佩戴的就是鹿角。在鄂温克语中,如果直译过来的话,是把雌性驼鹿称为“母亲鹿”。其次是熊,鄂温克族人有时借用祖父、祖母的称呼来指代公熊和母熊。在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中,这些动物都是被尊崇的对象,而这些传统的习俗已经十分古老了。
王 妍:此外,森林、小河、雪也是您小说中常见的自然意象,尤其是“河”在您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森林里的孩子》里的小孩、《鹿,我的小白鹿》里的老人,名字都叫“别日坎”(鄂温克语“小河”的意思);在《琥珀色的篝火》里,您写到小河旁边就是“家”,在《越过克波河》中两个猎人以克波河为界,来划分狩猎的区域。河流在鄂温克人心中有什么特殊意义?
乌热尔图:河流在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过去他们是沿着河流往返、迁徙,认为自己是被河流养育的。因此,鄂温克人习惯使用居住地的河流来区分彼此,例如,他们喜欢用“雅鲁河的”“辉河的”“根河的”来称呼自己、区分彼此。鄂温克人常向河流祈祷,并向河流祭拜,沿着河流迁徙,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来定位,比如“克波河左岸”“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只要你说出一条小河的名称,鄂温克人立马就会知晓你的具体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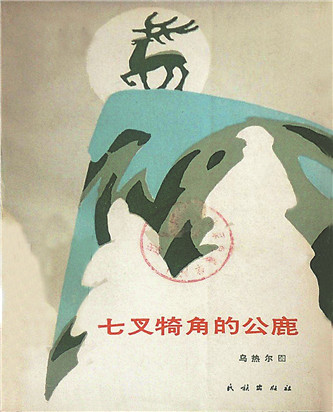
《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著,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
“那十余年的猎民生活不仅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也铸就了我观照世界的视角及思维方式”
王 妍:您的名字乌热尔图是鄂温克语“森林之子”的意思,您的小说多是写那片神秘的森林,以及淳朴、善良的猎民,却对自己的家庭、父母,还有童年生活涉及得不多,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乌热尔图:我是在莫力达瓦一个半山区的城镇里长大的,又在草原城市海拉尔待了几年,由于特殊的原因突然回到森林里生活,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那里的猎民不太会讲汉语,有的会说一点也是磕磕巴巴的,当时我又不太会说鄂温克语,交流有些困难。但他们都非常善良,不但不嘲笑我,反而手把手、耐心地教我。这一切都促使我要读好狩猎文化这本大书,而森林确实也是一个博大的母题,一般人很难踏足密林深处,更不用说把森林琢磨透彻了。所以像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能把西伯利亚森林描述得如此形象、写得那么有深度,就很难得。
父亲和母亲的教诲,对我而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作为我身后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的生活与创作。我的性格、人生的追求,还有精神气质一类的东西,比如坚韧、不怕吃苦这些品质,大多源自我的父母。回过头来看,我描述现实生活的作品确实少一些,不是我回避书写自己的家庭,其实我做了一些准备,但一直没有琢磨好切入的视角,再后来我的小说创作中断、兴趣转移,一些写作计划也就放弃了。
王 妍:您说到“回到森林生活”,“回”字这一深情的词汇体现了您对森林的归属感。事实上,那个时候您是作为知识青年去了陌生的环境,但小说中没有身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很多作品中主人公就是一个猎人。在同时代的作品中,很多作家都表现出摆脱乡村、走出山野的愿望,以及衍生的“出走”“追寻”的主题,但您在作品中从来没有表现出走的意向,似乎您从未想过离开那片森林。
乌热尔图:是的,我之前没想过要离开森林。17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所有、茫然无知的青年,在外面已经找不到一条生路,只能退守到父母的身边,我当时只有求生的强烈欲望。那个时期我虽然被当成“知青”,但我知道自己的脑袋里什么知识都没有。我作为“返乡”的青年,被分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狩猎生产队,它的名字很响亮,叫“东方红猎业生产队”。这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鄂温克族的生产队,之前没有接纳过知识青年,他们却破例接纳了我。接纳我的原因,无疑是因为我是鄂温克人的后代,虽然父亲那时还没平反,但他在这里工作多年,留下了很好的声望。
回到鄂温克人的怀抱,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磨炼和考验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没有退路,更无从逃避。在很短的时间里,严酷的自然环境就让我脱胎换骨,让我感觉犹如重生。而那些淳朴善良的猎民们,他们对我的呵护和厚待用语言难以表达,真是让我永生难忘。在短短的几年间,我长大了,并学习和掌握了在林中生存的技能,变成了一名手持猎枪的、真正的猎手。之后,那十余年的猎民生活不仅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也铸就了我观照世界的视角及思维方式。时至今日,我仍然保持着一个猎人的心态,让自己的情感与想象驻留在密林深处。
说到底,在那个年代,生活中给你的感受和启发,要远比书本上的东西深刻得多。那段时间,敖鲁古雅密林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故事,我都目睹、亲历,并身在其中。虽然,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段经历的价值所在,当后来借用文字来搭建自己的小说世界时,这段经历就成为我的“大矿”,我的小说素材实际上就是从这“矿道”里挖掘的。我有关大自然与森林居民的描写,虽说有点与众不同,却不是凭空想象的,那是以真实生活的体验为依托的。

《沉默的播种者》,乌热尔图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
“通过文学来把握和表现人的心灵,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寻求心灵之间的契合”
王 妍:如果我没有记错,《七叉犄角的公鹿》的结尾,应该是改过的,对吧?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总觉得前后的情感基调不太统一。可能最后是为了凸显人性的光辉,还有自然与人之间、尤其是鹿和人之间相互感召的力量。但我感觉继父性格转变得过于突兀,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原本的结局是什么。
乌热尔图: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从特定年代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在故事的原稿中有情感宣泄的因素。前面我们说过鄂温克民族对鹿、熊的特殊情感,但对初学打猎的人而言,狩猎过程也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过程。我个人积累了一些打鹿的经验,对生活在密林中的鄂温克人来说,这是生活的必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跟一位成熟的猎手学打猎,那是一个秋天,天地间一片黄金色。那天晚上我们在山脚下休息,就听见野鹿在山顶上叫唤。第二天早上,我俩拿着枪悄悄地往前摸去,他还不时模仿着那头公鹿的叫声,刚踏进一片敞亮的桦树林,猛然间迎面窜出一只野鹿,对着我们狂奔而来。只见它四肢强健,扬着高高的大犄角,浑身的皮毛油光闪亮、泛着红光,就像一团闪电。它奔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来不及反应,呆呆地愣在那里。但这头鹿冲到离我们十来步远的地方,却猛地停了下来,来了个急刹车,随后就地180度大转身,向我们相反的方向逃走,那动作太美了……
王 妍:那就是一瞬间。
乌热尔图:是的,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说起来,《七叉犄角的公鹿》的第一稿,是1981年在文学讲习所当学员时完成的,那也是我交的第一个作业。小说原稿的结尾,写的是一个深秋,主人公“我”躲在一旁偷窥两头公鹿的决斗,不幸的是那两个大家伙把鹿角紧紧地别在一起,分不开,最终一同跌落山崖惨死。我当初为什么要以这一悲剧的场景来结尾,现在看来,那都是特定时代留下的阴影,它噩梦一样罩在我的心头,驱之不散,影响了我创作上的立意与构思。好在,在追求文学的旅途上我算是幸运的,我遇见了王愿坚先生这位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家。在我入学进修之前,王愿坚先生已被聘为文学讲习所的创作辅导老师,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进修的学员有了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审读我们手稿的过程中,王愿坚先生一眼就发现,我这篇东西的结尾存在缺陷。后来在面对面辅导时,他耐心地例举生活中的细节,一遍遍地启发我,并给出创作上的一些忠告。先生认为,这篇作品的结尾涉及人格分裂的问题,从整体看是缺少铺垫而且难以把握。他认为那样的思路,可以通过另一篇作品去完成。我默默地记下了他的分析与评判,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和理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来了灵感,就重新构建了故事的情节和场景,整部作品也变得顺畅而有力度。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正式推出这篇作品不久,王愿坚先生随即发表了评论《一支关于心灵的歌》,他用热情、真诚、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肯定了我的这篇作品。
回过头来看,王愿坚先生让我领悟了文学创作的真谛,就是要通过那些看得见的文字和细节,写出那看不见的内容,也就是展示心灵的过程。按照我的理解,就是通过文学来把握和表现人的心灵,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寻求心灵之间的契合。这些精神层面的指导、提携,对我来说非常及时,而且十分必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特殊的历史,积攒了不少的情绪,这些都需要化解、转化和升华。因此,我对这位有着炽热心灵、修养高深的文学前辈,一直怀有无法忘怀的感激之情。
王 妍:《七叉犄角的公鹿》中的继父、《琥珀色的篝火》中的父亲尼库,都是那种很“坚硬”的猎人形象。而且您在文中多次写到“他是一个硬邦邦的猎手”“一个硬邦邦的人”,在情感表达和行为方式上,“他们”也都是硬邦邦的。此外,《七叉犄角的公鹿》跟《琥珀色的篝火》的结尾也有一些类似,都是父亲背着儿子离开。
乌热尔图:是的,其实鄂温克民族情感表达的方式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内敛。有位鄂温克族的老人读了《琥珀色的篝火》,对尼库抽打儿子的细节很有共鸣。在父亲看来,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应该能够掌握更多的生存技能。简单一点说,在那个急迫的环境中,父亲这一不轻不重的抽打,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爱的宣泄,同时也是作为丈夫的尼库对自己重病妻子的歉疚。
王 妍:《你让我顺水漂流》这部作品让我非常震撼。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萨满卡道布老爹,他预测到自己大限将近,找了一片茂密的白桦林,然后在林子上搭个台子,盖了桦树皮,躺在上面等待死亡。他预感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结,也感受到这片跟他生死攸关的森林将要遭受厄运,所以他选择在森林消失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乌热尔图:写这部作品时我想表达的东西比较复杂,主人公如果是普通人就会显得不伦不类,所以我把主人公设定为一位萨满,他有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与众不同,行为上包含了一些非理性因素,这就显得有点意思了。
“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说到底,主要还是对生命体的尊重,包括对人类个体的尊重”
王 妍:阿来的《空山》里也写了一个叫多吉的巫师,他也写到生态破坏、森林消失,多吉用自己的牺牲阻断了大火。而《你让我顺水漂流》中的卡道布大喊大叫了三天,那是在宣泄愤怒,也是在警示告诫。三天后,森林起火了,把动物、植物都烧毁了。那种在告诫中爆发的毁灭力量,非常震撼。但我发现,您是在作品越写越厚重的时候,突然不写小说了。1993年,你转向文化随笔写作,所以有评论家称您的《丛林悠悠》为“天鹅绝唱”。我个人感觉,您的创作是戛然而止。
乌热尔图:你的感觉很对。当时我读了威廉·福克纳的《熊》,这让我想起我们民族中流传的一个有关熊的古老传说,随即我有了创作的冲动,并很快为读者虚构出了这个故事。《丛林悠悠》也是我在考验自己,大胆地运用了想象与虚构。当确立了一个想象的目标,思绪就像野马在狂奔,那林中的感受几乎是奔涌而出。我把那些复杂的、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一股脑地表达了出来。但当我后来远离了森林生活,这一感觉的链条就断掉了,想象力也开始减弱。
之前,我的文学创作也有过中断。那是在198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得了癌症,他把我叫过去,希望我为他写一篇自传,我没有理由拒绝。后来我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以几十位鄂温克族的代表人物为采访对象,采用口述史的方式追忆他们的人生历程,记述他们与鄂温克民族发展相关的经历,结集出版了《述说鄂温克》。1993年之后的中断,是因为老朋友李陀约我为《读书》写随笔。虽然我写小说的时候阅读面比较宽,常翻阅民族学方面的专著,但要写好文化随笔,还要提出问题,要有理性的思辨,那就必须要静下心来思考,我只能把小说创作暂时放一下。2000年前后,我几次邀请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来呼伦贝尔,请他研究及解读本地的古地名。在这项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先生突然因病去世,他女儿将父亲所有的遗稿、常用的工具书,一并转交给我,我默默地收下了。之后,我没有躲避,而是放下手中的写作计划,来吃力地研读他的遗作,分析和把握他的学术观点。后来,我编撰出版了《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专著,都是在传播乌云达赉先生的学术观点。那时我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我意识到一个具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的人,置身于人口较少的族群,多年来一直被其呵护、滋养,他是不能逃避所要承担的文化责任的。后来,我转向了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慢慢地与森林生活脱节了,离现实生活也越来越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找到了提升自我并充实人生的一种方式。
王 妍:您对森林的那种归属感,对自然万物发自内心的敬畏、尊重、爱护和顺从,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这些年来,自然生态文学比较火,作品主要围绕逝去家园的“挽歌”、对人类掠夺行径的“控诉”,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唤”等几个类别,您怎么看待生态文学?
乌热尔图:时代在快速变化,我之前描写的森林其实也变化了,已经不再是昨天的森林了。如今,在我们的视野范围,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开始兴起了,正在形成创作上的一股潮流,或者说开始形成文学创作的一个流派,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准确一点说,这是对进程之中的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回应,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我们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身边的生存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要具有一种识别的能力,还要保留对生态环境衰变的痛感,为了子孙后代必须要保持这份敏感,这样才会获得改变恶行并与之抗争的主动性。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说到底,主要还是对生命体的尊重,包括对人类个体的尊重,因此这是一个无法割舍的文学主题。
[王妍系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当代汉语小说创作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3XZW038)、内蒙古文艺创作基金项目“内蒙古新时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研究(2012-2022年)”(项目编号WCJJ-2023-YJ40)的阶段性成果]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