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藤: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作家老藤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中,以与人物对应的三十多种植物为章节结构了全篇,仿佛他自己正是一株有心灵感应的草木,与这些老友促膝恳谈,谈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谈中国乡村的未来。
小说围绕由古驿站演变而来的村庄——墟里村的振兴发展,讲述了驻村干部“我”、村主任邵震天等人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终于让该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写自己,我也不能例外。”乡村是老藤的精神原乡,小时候生活在胶东和北大荒乡村的他,看到了几十年来乡村变革的全过程,乡村生活的积淀发酵出创作的冲动。于他而言,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作家 老藤
记者:《草木志》引子即点出了小说的结构,主人公“我”探究人与植物的关系,从植物的角度比喻人、观察人,由此将小说以植物分章节进行叙述。我想,读者所好奇的恰是这一点,为何选择了这样的结构方式?
老藤:长篇小说的结构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决定了长篇小说的成败。我这个人喜欢胡乱联想,有段时间我把人和动物联系起来,写了驴、猞猁、鹰等十几种动物,这一次,我决定把人和植物联系起来,打通人与植物的精神关联。这种想法不是我的发明,《诗经》中写到了152种植物,《红楼梦》中出现的植物有242种,《西游记》中的植物多达253种,可见,作家喜欢写植物再平常不过。我很喜欢这样一首诗: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佛教有句话也很有意思: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母亲有句口头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等等,这些都让我觉得在一部作品里,把人和植物联系起来加以呈现的想法是可行的。我对东北乡野中的各种草木比较熟悉,我在《草木志》背景地小兴安岭一带生活过,上山采过山里红、猴头菇,下到湿地里钓过鱼,采集过都柿、黄花菜,也打过苫房草、乌拉草,这些植物在我的《北地》《北障》两部长篇小说中多有描述。感情生于熟知,写到这些植物时,我有种与老友促膝恳谈的亲切,那一刻,我理解了庄子为什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感觉我就是一株有心灵感应的草木,草木即我,我亦草木,这种感觉很微妙,写作灵感会像草木上的露珠一样不断滴落下来,变成一串串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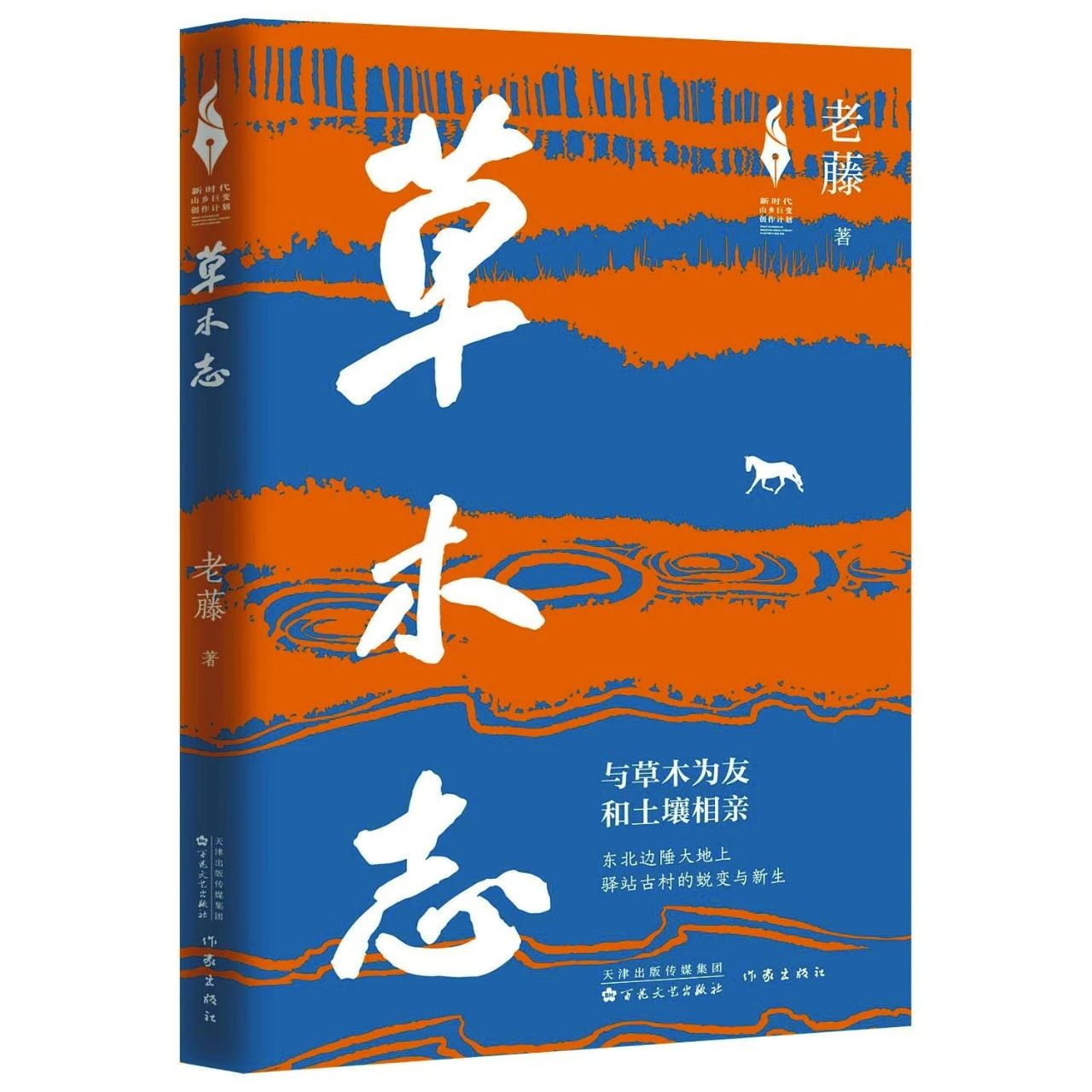
《草木志》
记者:所谓“草木志”,也是人物志,小说中共有三十多种草木,草木的特性与人物的性格对应,但在将植物与人相连时,人与植物的内在关联又如何打通?
老藤:在东北一些农村有种习俗,当家里孩子生病时,老人会选择一棵树让孩子认作干妈,然后抱着孩子到树前祈祷,希望树能给孩子以庇佑。村民觉得有些老树具有神性,会给它系上红布条,祭拜祈愿。且不说这种习俗有没有道理,至少在心理上对人是一种慰藉和寄托,这是北方萨满文化“万物有灵”观念的延展,是普遍存在的民俗。我写过一篇叫《杏树的脾气》的散文,这是我在前两年的切身经历,写了小区里一棵杏树的遭遇。我的结论是杏树是会发脾气的,杏树一发脾气,人就没有好果子吃。我对植物的观察颇有心得,当你留心某一植物时,一定能与认识的某个人找到关联点,这绝非牵强附会,人与物的精神特质是相似的。我在写某个人物时,一旦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特征确立后,我就会寻找他应该与哪一种草木相对应,一旦认领成功,思路就会豁然开朗。比方说枝干上带刺的树木,要么果子好吃,要么果子有毒,它长刺,是对觊觎者的警示,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再比如书中写到的狼毒草,这种花朵鲜艳的植物叫狼毒再贴切不过,它若好,周围别的植物就不能好,因为它把周围的水分养分都攫为己有。《草木志》中的马桑就一个例证,此人是“微腐败”的范例,让基层的执法生态变得恶化,东北的营商环境要想根本好转,必须治理这些“微腐败”。
记者:“我”是因为参与省里的一项驻村工作计划到了墟里村工作,这个由古驿站发展而来的村落,有其传统,当它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之时,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村主任哨花吹与“我”各司其职,前者处理的是墟里村的历史问题,而“我”更多面向的是墟里村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共同面对的是东北乡村的未来。
老藤:乡村振兴,关键靠内生动力,外力的推动作用固然重要,但很难持续,因为外力总有离开的时候,村庄永远是本村人的村庄。创作这部作品之初我告诫自己,不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一个能人、一个钦差、一个所谓精英,振臂一挥就能山乡巨变的“套路”作品,要重点写墟里土生土长的人。哨花吹就是墟里一个为红白喜事服务的喇叭匠,“三老”也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墟里的人,这些村民身上有无穷的潜力,“我”的作用更多是挖掘和激活这种潜力。当然,“我”这个角色更多是一个见证者,见证墟里乡亲面对古村生死存亡的命运选择,如何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打了一场故乡保卫战。我认为乡村未来不是简单的城镇化,城市扩张对乡村形成碾压之势的状况并不令人欣喜,消亡绝不等于振兴,乡村振兴应该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地推进,一刀切、一个模式去框定,会对乡村形成无法估量的伤害。每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都渴望留一点乡愁,留几块能够指引回家之路的路标,回不去的故乡,会成为精神上的一道疤痕。
记者:在首发式上,你提到一点:《草木志》虽聚焦于山乡所发生的巨变,却并非一部仅限于单一主题的创作。事实上,“巨变”的基石恰恰在于“守正”。对于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古村落而言,单纯的焕然一新未必就是最佳选择,新农村建设应该是经济与文化相统一的振兴。事实上,文化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你如何看待文化之于当下乡村建设的意义?
老藤:你问的这个问题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的确,城市和乡村各有自己的功能,城市的功能是集聚和创新,乡村的功能是传承和守护。城市和乡村让人的生活有了两种选择,如果你希望竞争进取,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种种好处,你可以选择城市;如果你喜欢恬淡安静,回归自然,你可以选择远离喧嚣的乡村。“巨变”的基石的确是“守正”,遵循乡村功能,赓续传统文脉,就是“守正”。我国众多的古村落保存着民族成长最纯粹的基因,这个基因如果遭到损害,是对民族成长的极端不负责任。经济是基础,文化才是核心,人类能够留给未来的只能是文化。乡村在产业、文化、人才和生态四个方面振兴中,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文化是留住人、吸引人最重要的元素。最近,媒体报道了湖南益阳清溪村靠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这就是一种可以复制的振兴模式,既守护了传承,又实现了文旅融合发展,让村庄有了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先后三次到清溪村,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了,他们在清溪村安居乐业,享受着乡村生活的闲适和美好。乡村有了人气,尤其有了年轻人,乡村的活力自然就体现了出来,一个只有老年人留守的村庄,靠谁来振兴?振兴又是为了谁?此外,把本该恬静的乡村弄得像城市那么竞争和“内卷”,乡村就失去了作为乡村的意义。
记者:“我”在到墟里村之前,老雷给我的建议是做无形之事,但面对乡村的实际情况,“我”却做了许多有形之事,作为一个乡村的“外来者”,“我”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老雷这个人物形象值得仔细分析,他见证了什么?又参与了什么?他又对应着何种植物呢?
老藤:在老雷这个人物身上我是下了些功夫的,这种人物在大机关里并不鲜见,他们靠下面报上来的总结、信息、经验,综合成文件报给领导,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至于这些报上来的材料可信度有多大,他们很少做分析,反正有出处就行。我们有很多研究者,连到农村走马观花都不去,仅靠梳理二手材料就自诩为专家,在媒体上大言不惭地夸夸其谈。作为厅领导智囊的老雷是个受人尊敬的“笔杆子”,他对农村的认识还局限在农民“喜欢跟着走”的时代,不知道在信息社会,封闭的边界已经被互联网消弭,看似其貌不扬的一个老农,竟然喜欢谈论国际大事(小说中石国库便是这样一个人)。网络改变着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有网,农民也可以直播带货,这种变化是颠覆性、变革性的。当然,老雷也在成长,事实上“我”坚持不懈要做“有形之事”的努力也逐渐影响了老雷,让这个整天在大机关里游刃有余的笔杆子开始注重实际、注重乡村,通过“我”知道了真实的乡村,也理解了“我”为什么要做有形之事。至于“我”的见证,有明有暗,总体上说,“我”在墟里见证的是一条断掉近百年的驿路如何被连接起来,见证的是古老的驿路文化如何得到了赓续,见证的是一个撕裂的村庄如何被弥合,也见证了乡村草木一样的芸芸众生只要不折腾、不践踏就会葳蕤起来,等等。见证本身就是参与,作为见证者,“我”是多角色的集合体,无法对应某一种植物,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我”应该是驿路上的一棵牛筋草,以匍匐的姿态看着墟里发生的一切。
记者:这也不得不更牵涉起更多的人物,哨花吹也就是邵震天在墟里村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自不必说,他的人格魅力让人由衷喜爱这样的人物,一金三老,包括石锁、方世坤等,都鲜活无比。你在一个创作谈中说,“我选择温情的剖面来描述和解析,更多地诠释人性中闪光的元素,目的不是掩饰,而是给人以生的热望”“我作品中恶人很少,尽管生活中从来不乏恶人,但我内心里有一种屏蔽恶人的本能”“我在写作中比较注意人物内心纹理的刻画,努力让人的心理活动符合生活逻辑”。在《草木志》中,确乎如此,墟里村都是可爱的人,他们认真生活,去往自己该去的命运。关于这些人物,你是如何塑造,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老藤:《草木志》中的人物之所以鲜活,很大程度得益于东北原生态农村生活对文学的供给。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幽默,这个结论有些以偏概全,如果你到东北农村住上几天,和村子里各色人等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幽默令人称绝。说东北人人都是活雷锋是调侃,说东北农村人个个都是段子手并不夸张,他们的段子诙谐、风趣又不失辛辣,如果当代也有采诗官的话,东北乡村肯定是他们乐不思蜀的宝地。我和他们交流,觉得一个专家费劲巴力解释不清的问题,农民一个歇后语就说得明明白白。由此我觉得,真正的人生哲学不在庙堂,而是在乡间,庙堂只是总结和提炼了乡间的经验而已。哨花吹之所以成功,是墟里人需要他,生活过日子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办红白喜事自然少不了哨花吹的助力,尤其在有鼓乐需求的墟里,哨花吹的出现绝非偶然。需要,是构成崇敬和信服的前提,没有人会服从一个与己无关的人。从这一点看,哨花吹是靠无差别地为村民服务才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金三老”也是如此,他们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的见识、给村民出的主意、遇到大事时出头露面的担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形象力。哨花吹的前任齐满囤其实是个大好人,而且是公认的大好人,但好人不一定就是好官,让齐满囤这个老实人做官确实是勉为其难。齐满囤当主任只会鹦鹉学舌,只会按上面要求照葫芦画瓢,他一没化解村民矛盾纠纷,二没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这样一朵“打碗花”被村民抛弃就在所难免了。总的来说,这些人物都像他们所对应的草木一样,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的命运轨迹,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各自不同的存在,构成了驿路都柿滩的风景。
记者:在阅读小说时,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你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人情、乡村、生活之熟悉,思考之深入,跃然纸上。你的几部长篇小说多聚焦于乡村题材,你也曾提到最喜欢写的正是乡村。在我看来,对于乡村的思考,一直在你的内心激荡。那么,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疑问是:乡村何以对你的写作如此重要?
老藤: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写自己,我也不能例外。乡村是我的精神原乡,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胶东和北大荒的乡村,乡村生活的积淀发酵出许多创作的冲动。我关注农村是一种下意识的自觉,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我看到了从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到今天乡村变革的全过程,看到了许多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那种经济上的大起大落和精神上依附寄托的改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温饱不成问题后,其它问题便接踵而至。我到一些乡村走访,那种十室九空的状况令我伤感不已,你不能说农民离开土地不对,谁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是,人都走了,乡村靠谁振兴?能不能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振兴途径?乡村是湿地,随时准备着非常时期城市的泄洪,当乡村消失后,滔滔洪水该往哪里流?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个中篇《陷牛沟》,是通过一个镇长的无奈反映了这种乡村的困惑。那个时期因为新旧体制转换,生产粗放、生态破坏、精神生活贫瘠等问题管涌一样冒出来,导致这个镇长最后一事无成地离开了陷牛沟。有位领导同志说,发展起来后问题会更多,当时不太理解,现在看来领导同志已经洞察出经济发展后要补齐的弱项,那就是人的精神需求问题。《草木志》中的方大珍,因为精神生活得不到满足,竟然像抑郁症患者一样萎靡不振,整天坐在炕上数手指头,当村里组建了鼓乐队之后,她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恢复了昔日的精神头儿。所以说,乡村振兴,一定是两个文明相协调的振兴,而文化赋能是振兴的不竭动力。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从这意义上看,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