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犬》:当母性成为暴力
《雌犬》是哥伦比亚作家皮拉尔·金塔纳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拉丁美洲海边丛林的故事。这篇小说篇幅不长,节奏紧凑,极具张力。精彩而集中的笔触让这部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主人公达玛丽斯的形象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本百余页的小说获得了2018年的哥伦比亚叙事图书奖,在2020年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作品奖,并赢得了2022年的都柏林国际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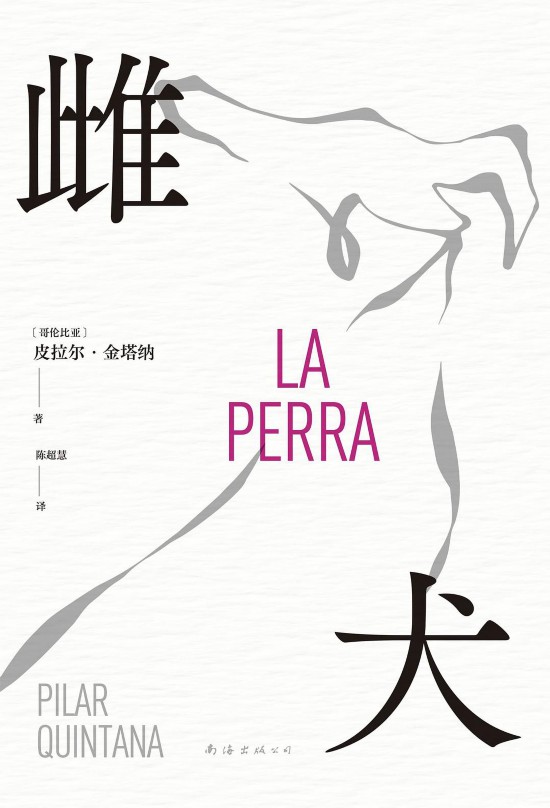
《雌犬》书封
故事背景设在拉丁美洲海边一个破败的村庄。这个看似简陋的地方却是富裕白人的度假胜地,他们在悬崖上兴建豪华的度假别墅,配备精美的花园和游泳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人公达玛丽斯和丈夫罗赫略的生活。这对夫妇栖身于悬崖上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中,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罗赫略以捕鱼为生,勉强维持生计。达玛丽斯曾靠为一户富有的白人家庭看管荒废的房产谋生。
达玛丽斯的人生充满了艰辛。15岁时,她的母亲因意外去世。随后,她唯一的亲人——舅舅——给她带来了折磨和鞭打。成年后,她嫁给了以打鱼为生的罗赫略。
三十多岁的达玛丽斯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尽管尝试了各种方法,她始终无法怀孕。一天,达玛丽斯得到了一只小母狗。她全心全意地照顾它、爱它,甚至给它起了本想给自己女儿的名字——绮里。然而,好景不长。这只狗总是逃进丛林,让达玛丽斯担心不已,到处寻找。奇怪的是,狗总能在几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达玛丽斯试图控制住母狗,但都无济于事。它总能顺利逃脱,在它怀孕之后更加肆无忌惮。母狗的行为最终令达玛丽斯无法忍受。在一次极度失控的情况下,她用绳子勒死了这只曾经深爱的宠物。
《雌犬》能够成为众多人喜爱的作品,这一点出乎原作者皮拉尔·金塔纳的预料之外。在一次访谈中,她诚恳地谈到,最开始她只是觉得这本书会在她丈夫或者少数几个朋友中间传阅,没想到这本书却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英国《卫报》评价这部小说:“这部广受赞誉的中篇小说对丛林的描写令人难忘——数不尽的暴风雨、昆虫,以及被海浪冲刷到沙滩上的垃圾。这是一个关于阶级、母性和愤怒的强有力的、令人震惊的故事。”
这部小说中探讨了阶级、母性和暴力的主题,也探讨了艰难环境中的人性裂变。可以说,母性与暴力是这部小说的双调。据作者自述,她曾经与恋人一起在太平洋的岸边过了十年的丛林生活,他们一起在悬崖上建造小屋,但金塔纳终究因家庭暴力而选择离开。这是一部自传小说吗?我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小说家一向擅长隐藏,在《雌犬》中,皮拉尔·金塔纳也将诸多问题隐于小说当中。
母性:一种不被定义的复杂生物性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论及“分娩”:“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但是单单作为一个妻子,她仍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作为母亲,她才能在社会方面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正是通过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义,达到它的目的。”小说的主人公达玛丽斯正是在这样的对于完整性的焦虑中希望得到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母亲。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雌犬是主人公达玛丽斯同构性象征,这条狗从一开始作为达玛丽斯“失落母性欲望”对象的客体承接者,无辜地承载和实现着女主人公达玛丽斯的情感替代。但是未知力量驱使着它不断想要逃向丛林,挣脱束缚。而随着女主人公对于雌犬的操控意志的加强,雌犬又因为怀孕和生崽不得不重新寄生于人的手下,成为人的宠物,但是自然的宿命让它重新逃脱管束冲进未知的丛林中,寻求自由。雌犬身上的一些生物本能是达玛丽斯无法控制住的,这让她的母性投射无所依托,变成了荒诞。即使她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将雌犬拴住,可是一种更大的神秘吸引力总会将它再一次引向危险的丛林。最终,达玛丽斯失去了耐心,她决定杀死再次怀孕的雌犬。
“……达玛丽斯用力扯着绳索,收紧活结。她没有停手,也没有把活结打开套在狗的腿上,而是用尽全力继续拉紧绳子。母狗就在她眼前挣扎着。她的眼睛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只看到母狗那胀大的乳头。‘它又怀上了。’达玛丽斯一边对自己说,一边更用力地拉着绳子,活结越来越紧,直到母狗奄奄一息地倒下,在地上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一摊散发着呛人气味的黄色尿液漫漫流向达玛丽斯,在地面留下越来越长、越来越细的痕迹,一直淌到她的脚边……她惊慌失措地丢下绳子,盯着死去的母狗和那摊黄色的尿液……内心又有一种不敢承认、想要掩埋在其他情绪之下的满足感。”
这段刻画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说达玛丽斯勒死母狗从开始还是一种“惊慌失措”之下的冲动所为的话,那么,作者对于她的一个情绪转折的刻画则将所有的问题明朗化了。“它又怀上了。”这件事让达玛丽斯拉紧了绳子。这一刻,她想要杀死母狗的意愿是如此强烈和决绝。她杀掉的不只是母狗,她真正想要杀掉的是尤其是狗身上的“母性”。也就是说,相对于痛恨狗,她更加痛恨的是“那胀大的乳头又怀上了”的“母”之狗。
这只小狗刚到这位女主人家时,达玛丽斯是那么喜爱这只狗啊:“这是她的狗”她不止一次地说。甚至不会让丈夫罗赫略朝它摆脸色。即使再艰苦,她都想要养活这只小狗,她亲切地给小狗用从商店赊的注射器喂牛奶;夜里达玛丽斯睡不着,她就会去抱起小狗,“陪着它”“抚摸它”,她甚至给小狗取了一个她原本打算给她要未来的女儿取的名字“绮里”。
与此同时,她对小狗的爱伴随着她酝酿怀孕的过程——她开始喝一种促进怀孕的草药。当草药不灵之后,她又做了一个手术来清理自己的输卵管,可那又是一个不灵的巫术,其结果可想而知。沮丧之余,他们彻底放弃了想要怀孕的念头,达玛丽斯觉得自己是“自然进化的残次品”。除了不能怀孕的折磨,他丈夫罗赫略也对她也实施了精神上的暴力:当她不小心打碎东西时,他就冲她嚷嚷:“下次再摔东西,我就要你付钱了,听到没?”这样一来,她对于小狗的依赖更加剧烈了,她甚至表示,如果罗赫略想对它做什么,只要他敢举起手,她就会杀了他……小说家一步步推进主人公的情绪和意志变化,达玛丽斯对于小母狗的爱当中已经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
小狗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到丛林中,达玛丽斯的耐心也到了极限。她开始捆绑这只狗,限制它的自由。但是狗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趁机挣脱逃走。“达玛丽斯开始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她开始怨恨它。”慢慢地她开始希望狗赶紧跑掉甚至死掉。
在这之后,她和母狗之间的关系有过一次关键的转折——母狗第一次怀孕了。达玛丽斯是通过丈夫的提醒才得知此事。作者写道:“达玛丽斯觉得自己的腹部仿佛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之后她陷入了深重的悲伤,“她觉得生活就像是那个小海湾,而她的命运就是要孤身一人走过去,……她困在这具躯壳里,这具没法怀孕、只会打碎东西的躯壳里。”此处,“没法怀孕”与“打碎杯子”并列在一起,而“打碎杯子”要她赔偿的,正是自己的丈夫。母狗的怀孕令达玛丽斯的自我再一次碎裂。这里表面上的叙事是在说达玛丽斯是在自我怨怒,实际上不如说她在将丈夫对她施加的暴力加倍施加回自身。
接下来,达玛丽斯与狗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从嫉妒到憎恨的关系。“滚开”她开始对着它喊,并“作势要打它”,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母狗生育完四只小狗之后竟然吃掉了自己的一只幼崽,并对“孩子们”不闻不问。在罗赫略踢了一只趴到他身上的狗崽之后,达玛丽斯开始给这些小狗崽找收养人。而这个地方的人的习惯却是,养不起的时候,就“把一整窝狗崽儿或者猫崽儿丢下悬崖,让海浪把它们卷走。”当达玛丽斯将所有的小狗都找到收养的人家之后,她与狗的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在一次对峙当中,达玛丽斯将水泼在了狗的身上,而狗也极力想要躲开这位逐渐失去理智的主人。作者写到:“这一次,她们之间的纽带彻底断裂了,再也无法挽回。”这是达玛丽斯杀狗之前的一切心理变化和情节推进过程,小说作者着重刻画了达玛丽斯与母狗之间情感关系的恶化和裂变,而这也是这篇小说的重点。至于书中其他的关于哥伦比亚丛林中村落的落后的、近乎原始的人的生存状况与阶级等问题,在我看来都是小说展开的背景。小说真正的主题是母性与暴力问题的探讨。
如果小说没有对于母性的矛盾复杂的心理揭示,就会变得平平无奇,正是这一点的发掘才使得小说的心理机制走向更深处。达玛丽斯们抗争的不止是自然和男性世界,还有自我归顺之后的个人意志。让她们形成困境的,除了与男性共同面对的恐怖而变幻莫测的自然,还有男性世界和社会的规训。小说的西班牙书名为la perra,意思就是“母狗”,中文翻译雌犬将其中的粗野意味去掉了。
“有什么东西在攻击她,是丛林……丛林偷偷潜入茅屋,将她包围,缠绕,地衣覆盖了她的全身,丛林中所有生物共同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叫声灌入她的耳中,直到她自己也变成丛林,变成木桩,变成苔藓,变成烂泥。”这里的丛林不应当单纯被看作是自然环境的实写,而应当看作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众多在达玛丽斯和罗赫略等周遭干预、规定,甚至抉择他们无可逃脱命运的因素。这本小说中,与达玛丽斯相较量的“海”与“丛林”既包括险峻严苛的自然环境,同时丛林当中她的丈夫和其他人同时构成了新的社会性的“丛林”。他们与“丛林”和“海”一起构成了那个幽深复杂充满危险和未知地域,正是在这个地域中,达玛丽斯们才一步一步走向崩溃和异化的边缘。
作者金塔纳解释道:“我对达玛丽斯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是,要一直与自然的残酷抗争,要始终保持清醒,才能存活下来。我很喜欢海明威《老人与海》,我也想写一部‘女人与海’,所以《雌犬》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女人与海,以及丛林’。”
暴力:隐蔽的复仇
小说家必须将她的故事嵌入到一个结构中,以完成虚构和真实的嫁接。杀狗是这部小说的情节关键点与高潮,但是这部小说所讲述问题却远不止于此,小说的内部映射揭示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诸多事实。
小说中关于堕下悬崖的白人——雷伊斯一家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可以看作是小说丰富向度的另一个参照。这是命运悲惨的一家,虽然拥有豪华的别墅,但是其家庭因为小尼古拉斯的偶然死亡而蒙上了一层阴霾。多年以后,又一位照看这所别墅的流浪汉因猎枪走火而死去。这座遭遗弃的白人宅邸给读者留下了哥特般被诅咒的古堡的印象,接二连三的死亡仿佛暗示着这里是因为某种原罪而屡次遭受诅咒。
除了小尼古拉斯一家的厄运之外,皮拉尔·金塔纳还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一个用斧头将丈夫肢解,并将丈夫的尸体喂给豹子的女人。在小说的结尾处,当达玛丽斯勒死母狗之后,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又是这一桩事件。达玛丽斯杀狗之后,去洗衣池旁舀水,她“想看看自己的眼神是不是变得和那个将丈夫肢解的女人一样。她觉得是,人们会认出她来,会知道她做了什么……”达玛丽斯杀狗,既是杀死狗的母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完成她对男权所加之于她的暴力的反扑。虽然这种方式看似隐蔽,但它确实还原了达玛丽斯脑中反复出现的暴力幻想。通过这种方式,她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完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复仇和杀戮行为。
在这部小说中,皮拉尔·金塔纳尽可能地进行了多重意义的建构。《雌犬》虽然不是典型的哥特小说,但作者巧妙地融入了哥特元素。传统哥特小说通常以古堡或庄园为背景,充满黑暗、恐怖和超自然元素,预示着厄运、死亡和诅咒。《雌犬》这部小说中,拥有巨大宅邸的富有白人家族接二连三的悲剧命运、主人公达玛丽斯家庭连续遭遇的不幸与死亡;作者反复提及的女人“杀夫喂豹”的情节点,以及达玛丽斯勒死狗的可怕肮脏的过程,都处处彰显了哥特小说的特质。
另外,小说还存在着与《圣经》故事的某种同构性。小说作者金塔纳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一个仿佛独立于人类社会孤独存在的海边丛林地带,作者并没有花过多笔墨描摹该地区的风土人情,而是直接切入到主人公达玛丽斯与丈夫罗赫略的生活中,聚焦于雌犬与主人达玛丽斯的关系演进,建构了近乎《圣经旧约》中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原始情景。其中男耕女织般的生活状态加固了这一同构模式。在《圣经旧约》中,耶和华神因为禁果被偷吃而对亚当和夏娃进行了惩罚。“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圣经旧约·创世纪》)夏娃的生育是被诅咒的,而达玛丽斯是无法生育的,由此她自然不会遭受生育之苦了,但无论是社会规约还是达玛丽斯自己都要求生育,她渴望生育,这种生育之苦转而变为“无法生育的痛苦”。这是一种变形的痛苦,是生育痛苦这面镜子的反面,但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生育似乎是神定的女人性,而在此处被剥夺的这种属性成为一种“新的缺陷”。我们自然可以说达玛丽斯的痛苦有某种“自我施加”的成分,但结合她所在社会形态环境,她对于生育的渴望,既受到周遭环境即社会陈规的规训,同时也在完成着男权对于她的自我的规训,进而发展到自我的惩罚。皮拉尔·金塔纳利用《雌犬》这部小说为我们揭示了这一人类普遍的艰难窘境,让人如鲠在喉。如同那只被主人勒死的母狗,它从一开始被好奇和温柔对待,最终逐渐变得丑陋难堪无法收场的命运,值得我们深思。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