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否有“定则”? 《晨报副镌》“爱情大讨论”始末
百年前的现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大讨论”。那是在1923年初,北京《晨报》连续刊登了《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两封读者来信,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读后有感而发,撰写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经《晨报副镌》主编孙伏园在该报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由此掀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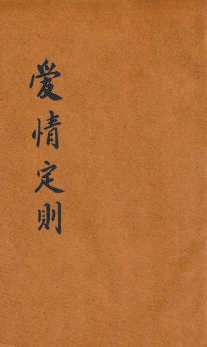
张竞生《爱情定则》1928年4月出版
两封读者来信 引起教授关注
1923年1月16日,《晨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沈厚培的“读者来信”。投书者反映,陈淑君是自己在广东时的未婚妻,与他早有婚约,然而,北大教授谭熙鸿(字仲逵)丧妻后,强迫妻妹陈淑君与之结婚。沈因此谴责谭道德沦丧,夺其所爱,吁请报社主持公道。不意第二天,陈淑君也致函《晨报》,指出沈所述与事实不符,自己与谭结婚系双方自愿,完全是个人自由。
两封来信,各陈其词,针尖麦芒,各不相让。由于当事人为社会名流,谭熙鸿是北大教授,陈淑君是陈璧君(汪精卫之妻)的三妹,所以格外引人瞩目,一时舆论哗然,社会热议,更引起了对爱情、婚姻素有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的高度关注。
张竞生与谭熙鸿同为留法同学,又是执教北大的同事,所以二人非常熟悉。1922年3月,谭熙鸿之妻陈纬君因产后感染猩红热症,3月18日在医院病逝,时年26岁,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同年秋,因陈炯明叛乱,广东局势混乱,在广州就读的陈淑君辗转北上,寄居亡姐的家中,在北大当旁听生之余,帮助姐夫照顾两个痛失母爱的孩子,两人日久生情、相恋并结婚,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获悉后从广州赶到北京兴师问罪。
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镌》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以“谭陈事件”为例,阐述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提出“爱情有四项定则”: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他在文中为陈淑君辩护:“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据她所说,见了谭宅亡姊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所能及。这些条件均足左右陈女士对于沈谭的爱情。”张竞生高度评价陈淑君的心灵解放和精神觉醒:“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种朋友,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可专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或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还突出强调:“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时满城风雨。
围绕“爱情四定则” 社会各界展争鸣
五四时期,在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引领下,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华大地狂飙突进,人们也热切呼唤自由的、幸福的恋爱婚姻生活。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振聋发聩,一场由一则“社会新闻”引发的“爱情大讨论”呼之欲出。
《晨报副镌》主编孙伏园敏锐地感知这是一个重大社会话题,于是策划了一场系列讨论。5月18日至6月25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在《晨报副镌》连续刊发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少数作(读)者支持张竞生的主张,绝大多数作(读)者站在维护旧礼教的立场,且多是青年学生。
其中,北大教授梁镜尧的反对声音最为响亮,提出了与张竞生截然相左的“爱情定则”:爱情是无条件、非比较的、不变迁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种。
更多的则是各有选择、各有取舍。譬如,北大教员冯士造认为恋爱与婚姻,本是由友谊进步来的,因此,赞成“爱情四定则”的第四项,但对于爱情可以随条件、经比较、可变迁的主张,他则极力反对。北大学生章骏锜也持相同意见:“除第四项我完全赞同外,其他三项与我的意见不合。”读者丁勒生表示:“爱情可以比较,可以变迁,我全承认”,但“根本就怀疑有条件的爱情”,指出“我的意见是:爱情就是爱情,恋爱就是恋爱,绝不应掺入旁的一丝条件,不然,便不能算真正爱情、纯正恋爱”。
一些反对者承认爱情有条件、可选择、可变迁,这在婚前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一旦已有婚约或已结婚,就不应该再进行选择,反映了在爱情、婚姻观念转型期的一种双重标准的爱情选择。例如,读者世良指出:“我对于竞生君的‘爱情的定则’的适用,要加一点限制,就是:‘爱情的定则,多半适用于未定婚约之前。’”
此外,一些反对者不仅对“爱情四定则”作了学理分析,还对谭仲逵的“不道德”、张竞生的“偏袒”,提出了尖锐的嘲讽。读者张畏民认为:“谭陈的知识、年龄、情形……不相当,他们绝对谈不到爱情——狭义的——这是不用说的;就是以谭君处大学教授的地位,丧妻未久,同一个与他人已有婚约的女子去结婚,不能不受言论的制裁,张君偏要为一二人之私,破坏质朴的风俗,还要说什么‘爱情定则’,真正可叹。”
孙伏园对于参与大讨论的青年学生成为旧礼教的代言人,颇感失望。5月18日,他在《晨报副镌》编前“按语”中表示:“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流露出满怀的无奈和深深的失落。
周作人三撰文 一人演“双簧”
6月20日,《晨报副镌》在“杂感”栏目刊登署名荆生的短文《无条件的爱情》。“荆生”者,乃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周作人的笔名。周作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里,近来很流行什么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
于是我不禁记起什么笔记上的一条故事来。有一个强悍放纵的无赖独宿在一间空屋里,夜半见有一个女子出现,他就一把拉住,她变了脸,乃是吊死鬼!他却毫不惊慌,说他仍是爱她(原本的一句话从略)。
这似乎可以算是无条件的爱情的实例了,但总还有一个条件,便是异性。——倘若连这个条件也不要,那不免真是笑话了。
或者中国人大抵和我一样喜欢说说笑话,所以那样的主张也未可知。
作者以幽默的笔触,讽刺了“爱情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论调,赞同张竞生“爱情四定则”中爱情是有条件的观点,支持陈淑君的选择。周作人的短文,作为讨论的接续和延伸,不失为激烈论战中一个巨大的正面回声。
事实上,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旗帜鲜明地抨击旧礼教对爱情、婚姻的束缚,维护妇女权益。他在6月6日、6月15日,曾先后化名“钟孟公”和“曹叔芬”,致书《晨报副镌》,参与“爱情四定则”讨论。其中,“钟孟公”向“副刊记者先生”指出:
我现在以读者的资格,对于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一件事,想进一句忠告的话。那些文章初发表的时候,我很有兴趣的期待着,但到了现在读过二十篇,觉得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先生还想继续登载下去么?我想至少您也应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是这样的胡乱尽登下去了。
而“曹叔芬”则向“记者先生足下”主张表示:“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发表,不但可供小说家、医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浅鲜。”
“两人”观点一红一白,截然相反。一人分饰三角,更是催化了一波继续讨论“爱情四定则”的争鸣。
许广平与鲁迅 前后参加讨论
在“爱情四定则”讨论中,许广平和鲁迅也不约而同地关注并参与其中,而那时他们还素昧平生。
鲁迅和许广平都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1906年,鲁迅迫于母命,与无爱的朱安女士结婚后,长期身受旧式婚姻的煎熬。许广平出生仅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香港一马姓人家,20岁那年为抗婚,她北上天津入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5月25日,许广平以“维心女士”为笔名,投稿《晨报副镌》,提出了不认同谭、陈结合,不认可张竞生“爱情四定则”的看法,表现出一种与实际情形颇为迥异的角色冲突和观念矛盾。
6月12日,《晨报副镌》刊登陈锡畴等人的三封来信,他们一致要求停止“爱情四定则”讨论。当天晚上,鲁迅写信给孙伏园,表明自己的立场:建议继续讨论下去。6月16日,《晨报副镌》登载了鲁迅的来信:
……钟先生也还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
虽然鲁迅没有直接回应“爱情四定则”的讨论,但可以看出他对张竞生的主张持赞同态度。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命题,与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异曲同工。
张竞生“答复” “大讨论”收官
这场大讨论中,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谭熙鸿、陈淑君夫妇。然而,谭熙鸿并没有因为所谓“绯闻”的影响而懈怠自己的工作,他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履行教授治校职责,负责筹建北大生物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经过前后一个多月时间的论战,最后,张竞生撰写了近2万字长文,发表在《晨报副镌》,予以回应。
这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上篇的开头,张竞生重申:“我在数年前已经留心研究爱情的问题了,但所拟就的爱情上几个定则,终未拿出来向人讨论。及到近来感触了陈淑君女士的事情,使我觉得有宣布的必要。可是,处在这个不懂爱情的社会,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见的先生们,讨论一个真正的改善和进化的爱情,使他们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属为难。又要将一个被嫌疑的女子作为举例,使他们不生误会曲解,当然是更难之又难了。”同时,郑重声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随后,围绕与他讨论的文章、向他提出的问题,从四个方面一一分析阐述:“一、爱情是无条件的;二、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为爱情的条件,但名誉、状貌、财产,不能算入;三、爱情条件比较上的标准;四、爱情定则,适用于未订未定婚约之前,但不能适用于已订已定婚约,或成夫妻之后。”最后,张竞生向青年朋友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你们如不讲求爱情那就罢了,如果实在去享用真切的完满的爱情,不可不研究爱情的定则,不可不以爱情的定则为标准,不可不看这个定则为主义起而去实行!”
持续一月有余的“爱情四定则”讨论,至此偃旗息鼓。尽管张竞生的理论有流于简单化、绝对化和教条化倾向,然而,由此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却是一场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全面启蒙,昭示着时代的巨大进步。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