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小约翰》:“准中期”鲁迅的形成
原标题:《小约翰》与“准中期”鲁迅的形成
简单缕述一下《小约翰》和鲁迅的事实关联:荷兰作家望·蔼覃(Frederik van Eeden)在1887年发表了一部童话小说《小约翰》。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一家德文杂志《文学的反响上》(第1卷第21期)上读到了这本童话的部分章节以及波勒·兑·蒙德作的作者评传后,就被吸引了。后来他通过东京丸善书店,从德国订购了《小约翰》的德文本,颇为喜爱,想译却因为力有不逮而未成功,将之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1926年7月,他才和友人齐寿山开始正式动笔对译,将其译成中文(鲁迅,第三卷353)。是年8月13日,初稿大致成型。《小约翰》的中译本出版于1928年1月,由未名社推出。

F. 望·蔼覃著,鲁迅译,未名社,192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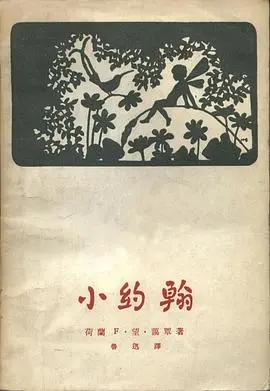
1929年5月《小约翰》中译本再版,鲁迅设计封面,选用勃仑斯《妖精与小鸟》作装饰。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约翰》之于鲁迅的意义超出了我们对它的认知。从其翻译过程来看,从1906年东京首次遇见,到鲁迅的中译本最终面世,历经20余年,可谓有始有终;而从鲁迅先生对其屡屡褒扬来看,可谓不遗余力,翻译和修订过程中即是如此,比如1927年9月25日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言及自己不够格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对理由的思考加以说明时写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第12卷73)而到了晚年时亦然,比如1936年2月19日鲁迅致信夏传经说:“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鲁迅,第14卷33)鲁迅常作谦虚之语,对自己有所贬抑,但其褒扬之词更须注意。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小约翰》对鲁迅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潜移默化的部分或许难以描述,笔走龙蛇中的草蛇灰线与直接影响似乎更期待有心人揣摩。
前人对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不乏敏锐洞察,比如王瑶先生就指出:“他一贯注意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还翻译介绍了《小约翰》、《表》等著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这当然也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总之,对于鲁迅生平传记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从《朝花夕拾》中找到渊源或解答。”(王瑶13)但其侧重点却是在《朝花夕拾》。孙郁先生亦有洞见:“《小约翰》对鲁迅的影响,是潜在的。这一本书,直接催生出他的《朝花夕拾》。我甚至觉得,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便是译过《小约翰》后的一种自我追忆。其中一些名词、意象,和望·蔼覃的小说颇为相近,比如对读书的厌倦,对草虫的喜爱,以及神异的传说,等等。1926年的鲁迅,笔下常出现孩提时代的鬼怪,像‘无常’、‘美女蛇’、‘二十四孝图’。倘若将《小约翰》与《朝花夕拾》对照起来,西方文人对东方文人的心灵碰撞,是可看到一二的。鲁迅是个很会吸收别人营养的人,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精神来源,并将一本感动过自己的书,译介过来,那境界是很高远的。”(孙郁63)其中对有关影响篇目进行了细化,引人深思。不少论者一再指出《小约翰》与鲁迅的创作关系密切,比如它与《野草》的复杂关联:贺琴认为《小约翰》与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有诸多相通之处,“《野草》所蕴含的鲁迅的哲学思考,如梦、存在、希望、对人类的爱与恨等,在《小约翰》中也有着相近似的体现”(贺琴94)。杨炀认为《小约翰》与“过客”有相通之处,后者的人物有前者的影子(杨炀5)。郭梦莹则认为:“在《秋夜》里,鲁迅借用童话之笔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气质和人生价值观。此文在童话色彩创作手法的观照下,阐释《秋夜》中别具一格的灵动与睿智。”(郭梦莹21)而张芬则考察了《小约翰》对鲁迅小说《铸剑》的部分影响。(张芬58—64)毋庸讳言,上述研究一方面开拓了我们的认知和思考视野,另一方面相较而言,还是相对窄化了《小约翰》与鲁迅文学创作的繁复关系,尤其是前者对于后者的更大范围的直接、深刻和全面的影响。
在我看来,《小约翰》对“准中期”鲁迅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鲁迅的某些文学生产和它有高度的关联性乃至契合性。这里的“准中期”相对于中期鲁迅(1918—1927年)①而言,主要是指鲁迅开始创作《野草》的1924年北京时期至1928年1月《小约翰》出版的时间段:跨越了北京鲁迅、厦门鲁迅、广州鲁迅②以及上海鲁迅初期:鲁迅在1927年5月30日书写的《译者序》中对在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的翻译情况有所描述:“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这样地约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门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没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望·蔼覃132—133)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此一时段恰恰包含了鲁迅相对珍重的五书中的《野草》《朝花夕拾》和部分《故事新编》,它们也正是鲁迅诗学最为浓烈与集中的文本,值得认真探勘。接下来我们不妨集中讨论它们文本内外彼此最为契合的层面。
一、 童话风格及其转换
尽管《小约翰》指涉丰富、涵容宽泛,但它首先依然是一部童话小说(虽然不无成人意味),而且是令人眼界大开的童话。从主人公小约翰的视角来看,至少包含了三种世界:一个是与旋儿有关的美好自然世界,其中既有动物们的伊甸园,也有动物视角反观人类的缺陷与残暴;一个则是将知/穿凿们的半知识化的世界,经由探寻自然会得到更多知识收获,但也会失去“妖精性”而变得不再梦幻与童话;最后一个则是人间(含阴间)的悲惨世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不自知,也是号码博士研究的对象世界。
(一) 童话风格
《小约翰》中呈现出相当繁复的童话话语形构,其中既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动植物世界,又有根据动植物成长科学原理推演的拟人化再现(当然更是让人类靠近自然的方式展开),同时又有人兽对照与冲突。而这些也往往影响着鲁迅,也为论者所洞见:“其中,人与兽(‘妖精’)对话、人不如兽的思想,很接近《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小约翰’每每醒来都不敢相信梦中那些神奇经历是真的,也仿佛《好的故事》。甚至一些修辞上的细节,比如‘大欢喜’‘奇怪而高的天空’这样特殊用语也为《野草》和《小约翰》的鲁迅译本所共有。”(郜元宝13)
1. 和美自然再现。《小约翰》中书写动植物都有相当令人着迷的风格,如柳树相当优雅:“柳树沿着岸站立成行。它们不动地将那狭的、白色的叶子伸在空气里。这垂着,由暗色的后面的衬托,如同华美的浅绿的花边。”(望·蔼覃6)这样书写小飞虫旋儿,宛如电影镜头特写:“指环只是增大起来,它的翅子又抖得这样快,至使约翰只能看见一片雾。而且慢慢地觉得它,仿佛从雾中亮出两个漆黑的眼睛来,并且一个娇小的,苗条的身躯,穿着浅蓝的衣裳,坐在大蜻蜓的处所。白的旋花的冠戴在金黄的头发上,肩旁还垂着透明的翅子,肥皂泡似的千色地发光。”(6)类似的,这种美好在鲁迅的文学创制中不乏借鉴。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关于百草园的植物书写,气势酣畅淋漓、动植物和谐并存怡然自得;《秋夜》中的小青虫自有一种固执的勇猛;而《好的故事》中富有层次的和美故乡状描,完全可以理解为现实中讨厌故乡的鲁迅的精神原乡和回归母体(朱崇科,《原乡》100—104)。如果往前推演,《社戏》(1922年)中亦不乏此类追求,鲁迅企图借力于被物质、伦理与成人文化(糟粕)荼毒之前的赤子之心与自然状态加以反拨。
2. 造物的规律/尴尬。《小约翰》中人兽之间的对比耐人寻味,而在动物眼中,人类显然低人一等,比如通话中提及了蟋蟀学校的动物学知识传授:“动物被区分为跳的、飞的和爬的。蟋蟀能够跳和飞,就站在最高位;其次是虾蟆。鸟类被它们用了种种愤激的表示,说成最大的祸害和危险。最末也讲到人类。那是一种大的,无用而有害的动物,是站在进化的很低的阶级上的,因为这既不能跳,也不能飞,但幸而还少见。一个小蟋蟀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误将人类数在无害的动物里面了,就得了草秆子的三下责打。”(望·蔼覃10)火萤们也对人类表示出类似的态度:“只有一种动物,是一切中最低级的那个,搜寻我们,还捉了我们去。那就是人,是造物的最蛮横的出产。”(16)在此作品中,人类成为快乐动物世界的最低等却又最大的威胁。
“准中期”鲁迅的创作中,对《小约翰》既有借鉴,又有翻转。《兔和猫》中恰恰呈现出造物主的滥造,而弱肉强食自有其合理性(为了维持种族的合理存在结构),但却是人类保护弱小(不管兔子们是否超生)打击强权(黑猫?)的爱心泛滥,和《小约翰》中人类的自私残忍形成张力;《鸭的喜剧》亦然,这是纪念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作品,人类尊重自然的美好和谐,却没有料到动物自然规律的残酷性——长大后的鸭子吃掉了蛤蟆的儿子蝌蚪们,听不见预想中的万籁齐鸣的美声了。
(二) 丰富涵容与鲁迅转换
《小约翰》毕竟是以人的视角、用梦幻的方式进入别有洞天的自然世界,而其美好也屡遭威胁,尤其是来自人类的威胁。而反观自然世界,不同动物在无知有畏、天真烂漫之余也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偏执,它们往往以自我种族为最优等,但显然鲁迅先生对此有其人文关怀和功能(尤其是启蒙)指向:“由此推断,《小约翰》之所以能够吸引鲁迅,显然不在于它是一篇写给儿童看的童话,而在于他深受辛亥革命前期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致力以‘新文艺’来改革国民的精神,实现‘新政治’的目的。”(李玮42)北京鲁迅就职于教育部的经历让他对中华民国早期政治的波诡云谲深有体会,也从满怀希望到日益失望。
《小约翰》中的美好童话世界彰显出动物们相对合理而又和谐的新秩序,比如:“白头鸟这时飞上了最高的枝梢,用着简短的、亲密的音节,为落日歌唱——仿佛它要试一试,怎样的歌,才适宜于这严肃的晚静,和为下堕的水珠作温柔的同伴。”(望·蔼覃39)同时也部分反衬出人类存在的破坏性,相当经典的一幕则来自小约翰与小鬼菌的对话:“你们俩是毒的。”“你大概是人类罢?”(44)肥胖者讥笑地唠叨着。
《狗的驳诘》可以彰显出人兽之辨,尤其是涉及急功近利、人类世俗(文化)等指向,最终人类“我”落荒而逃,该文是对奴化和物质化丑恶文明的双重反讽,其中一重指向了制度反讽,而另一重则是对自我的解剖。其中,“我”的身份的犹疑性和作为“中间物”的劣根性也是一种值得警醒的存在。(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199)而《失掉的好地狱》又借了鬼王批判人类:“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214)和《小约翰》如出一辙,都对人类充满了不信任和嘲讽:魔鬼去追寻“野兽和恶鬼”,是进行身份的区隔,并非赞扬人类,言外之意是——和人类相比,魔鬼和野兽才更是他的同类,远比“人”好。
值得注意的是,“准中期”鲁迅的创作还有更多与《小约翰》的契合之处,比如创作手法和文字风格等,其中包括梦幻手法的使用,创作《野草》的鲁迅其实也是被《小约翰》萦绕着,诗性气质亦然,而“准中期”鲁迅的诗学抒情性则是鲁迅毕生中最为浓烈和集中的,在字句的雕琢、斟酌上更是如此。但无论怎样,对于《小约翰》的翻译和借重,本身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对“真善美”的戮力追求,乃至“最佳体现”。(骆贤凤89)
二、 阴暗人间及其回归
毫无疑问,鲁迅对《小约翰》的喜爱是发自内心、贯穿始终的,他甚至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向他人不吝推荐,如其所言:“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也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望·蔼覃132)显而易见,该书中富含了鲁迅所欣赏的理念与文学样式,而从内容上看,这个作品中涵容了自然、妖精、人类、鬼怪等不同层次的世界,它们有交叉,有对照,也有从小约翰视角呈现出的重要的抉择与担当。
(一) 晦暗人间
《小约翰》中的主人公小约翰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如果用幽暗意识作为关键词贯穿的话,他有相当繁复的精神阅历。
1. 鬼世界。小约翰在穿凿的带领下穿过蚯蚓的孔洞而看到了人的腐烂尸体:“他面前就出现两个深的黑洞,是陷下的眼睛,那淡蓝的光还照出瘦削的鼻子和那灰色的、因了怖人的僵硬的死笑而张开的唇吻。”(望·蔼覃99)而且还特别展开了某些人类生前华美、优雅与死后猥琐的比照:“来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脸带着狞视的圆眼,膨胀的黑的嘴唇和面庞。”(101)更关键的是,穿凿还带领约翰挖土穿越连蚯蚓都不愿继续深入的墓穴/地狱,并最终冲破了有形无形的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采取多种方式在多个层面回应鬼世界:有趣的欢快的层面来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其中的美女蛇显然不是常见的毒如蛇蝎的形象,而是令人有所期待的部分美好;其他还包括《阿长与〈山海经〉》里的书写,其充沛的想象力、战斗力往往令人叹为观止。鬼世界也有惊悚的一面,也包含了自我解剖,如《墓碣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只是恐怖,还包括对自我的惨烈挖掘;《死后》则是另类书写,鲁迅想象了人类劣根性对死人的骚扰,认为死后的世界并非人类所预设的清静/情境。
鲁迅对小约翰的鬼世界也有发展之处:《无常》中的鬼物让人们喜闻乐见,因其在有限范围内追求公正,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鲁迅毋宁借无常角色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新人,即有情有义、有同情心、有同理心。而《五猖会》则借非主流的神进行释放与民间建构:无论是抢别人男人的梅姑,还是看起来不守男尊女卑规矩的他者神祇。
2. 真人间。在现实中过得并不如意,经由梦境,小约翰进入了天真烂漫五彩缤纷的自然世界,但不满足的他也萌生求知之意,终究回归人间,自然也经历/遍览了人间的苦闷、忧愁与各色痛苦。穿凿先生向他灌输了做人的原则:“你应该,现在你在我的守护之下了,你须和我一同工作并思想。”(望·蔼覃82)而科学博士也告诫他要大气和坚强,“科学的人”“高于一切此外的人们。然而他也就应该将平常人的小感触,为了那大事业、科学,作为牺牲”(90)。而小约翰也看见了普通人的痛苦:“人们在那里蠢动着,他们互相挨挤,叫喊,喧笑,有时也还唱歌。房屋里是小屋子,这样小,这样黑暗而且昏沉,至使约翰不大敢呼吸。他看见赤地上爬着的相打的孩子,蓬着头发给消瘦的乳儿哼着小曲的年青姑娘。他听到争闹和呵斥,凡在他周围的一切面目,也显得疲乏,鲁钝,或漠不相关。”(92)当然,更大的人间震撼来自他被穿凿和博士带去看垂死的父亲,并最终目睹自己父亲无奈的死亡。以上种种,不止给小约翰,也给鲁迅带来不少冲击,如人所论:“将鲁迅创作与其童话译著进行创造性对话研究,可以发现它们在思想上存在深层次的关联性。在对物质文明和自然科学的批评性省思,对自然美的书写和生态遭受毁坏的忧思,以及对世间万物的同情与关爱等问题上,鲁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他翻译的童话作品之间找到了深切的共鸣点,并在对话中发展了自己的哲思。”(王家平 吴正阳89)
鲁迅对《小约翰》中人间的书写抱以高度的同情,从动物角度出发,人类侵占其利益、干扰了它们的清净乃至幸福生活自有可恨之处,但人类的痛苦需要安抚、精神需要启蒙、科学求知势在必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可圈可点且值得弘扬。鲁迅散文《父亲的病》中的场景,如果从小约翰角度比照阅读的话,则更易打动人心,而鲁迅文中的忏悔精神也与小约翰的离开又归来却无能为力的感受殊途同归,但鲁迅的情感显然更强烈,尤其是对于“父亲”的多次刻意强调与内心打扰溢于言表。当然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点,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小约翰》的单独影响:《父亲的病》也可能有更多外来影响,比如格非就认为:“‘父亲之死’这一情节,与《金瓶梅》中李瓶儿临终之前的病急乱投医,实在是遥相仿佛。在《金瓶梅》的写作年代,虽然还没有西医一说,但对中医批判之决绝、嘲讽之刻薄,《金瓶梅》相较于《父亲的病》亦不遑多让。”(格非284)
(二) 回归人间承担
论者指出小约翰终于在两种抉择中选择了人间,也实现了其勇于担当的使命:“《小约翰》则不然,在这其中,它展开了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大自然的诅咒;另一方面则来自人自身,人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困顿。到了最后,小约翰在面临着天堂般的永恒世界和人充满痛苦的人间时候选择了后者。”(张芬62)《小约翰》中,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人间,作者写道:“于是约翰慢慢地将眼睛从旋儿的招着的形相上移开。并且向那严正的人伸出手去。并且和他的同伴,他逆着凛烈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望·蔼覃128)当然,这条路实际上也是体验更丰富阅历的痛苦和救赎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约翰》可以理解为一部成长小说,作为人类之一的小约翰终于回归到了有缺陷、有大爱、有知识的人类中来,不乏担当意识。《铸剑》(原名《眉间尺》)中的眉间尺亦有此类追求,16岁的他原本无聊而好玩,后在母亲提醒下走上了为父报仇之路,历经奚落、欺诈,终于勇敢献身、牺牲自我,并在黑色人帮助下替父报仇成功。而《这样的战士》则更彰显了其坚定性,不管旗帜与干扰为何:“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鲁迅,第2卷219)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过客》。一方面,过客积极回应冥冥之中声音的呼唤,不辞辛苦,为了目标戮力向前,而不能停滞成止步不前的老者——从身份执着角度看,正是通过主客身份的流动与置换,鲁迅既强调要警惕堕落,又暗涉了“立人”乃至立国的可能路径。同样,在反抗绝望的补充与路向层面上,过客又呈现出迎拒的暧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修正过的西方现代性。(朱崇科,《执著与暧昧》37)另一方面,过客也彰显出决绝与担当感,对无法回报的爱加以婉拒,让小姑娘继续葆有美好的善意与幻想。
三、 神之凝视与反省
关于《小约翰》的理解也自有其多元关怀和哲学理路:“《小约翰》也如哲学底童话一般,有许多隐藏的自传。这小小寓言里面的人物:旋儿、将知、荣儿、穿凿,我们对于自然的诗,有着不自识的感觉,这些便是从这感觉中拔萃出来的被发见的人格化,而又是不可抵抗的求知欲,最初的可爱的梦,或是那真实的辛辣的反话,且以它们的使人丧气的回答,来对一切我们的问题: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望·蔼覃145—146)我们不妨从其中神的角色略加分析,同时也可参照鲁迅先生的有关文本实践。
(一) 人神对照
《小约翰》中出现过上首——妖的王,“围绕着一小群妖精的侍从,有几个轻蔑地俯视着周围。王本身是照着王模样,出格地和蔼,并且和各种来客亲睦地交谈。他是从东方旅行来的,穿一件奇特的衣服,用美观的,各色的花叶制成。这里并不生长这样的花,约翰想。他头上戴一个深蓝的花托,散出新鲜的香气,像新折一般。在手里他拿着莲花的一条花须,当作御杖”(望·蔼覃13)。也提到过人类的上帝崇拜及其排他性,旋儿反过来对人类亦然,他对约翰说:“那你就应该将人类忘却。生在人类里,是一个恶劣的开端,然而你还幼小——你必须将在你记忆上的先前的人间生活,一一除去;这些都会使你迷惑和错乱,纷争,零落。”(39)小约翰一开始并不信仰人类普遍信仰的上帝,“我对于上帝没有敬畏。上帝是一盏大煤油灯,由此成千的迷误了,毁灭了”(73),而最终经历父亲死痛的小约翰终于选择了追随神——真正的上帝/耶稣,神指着黑暗的东方说道:“那地方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那地方是我的路。并非你所熄灭了的迷光,倒是我将和你为伴。看哪,那么你就明白了。就选择罢!”(128)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中对神的敬畏并不虔诚,《铸剑》中帮助眉间尺复仇的黑色人发出的回应与《小约翰》如出一辙,黑色人回应眉间尺道:“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鲁迅,第2卷440)而神回应小约翰关于上帝与耶稣的尊敬称呼:“先前,它们是纯洁而神圣如教士的法衣,贵重如养人的粒食,然而它们变作傻子的呆衣饰了。不要称道它们,因为它们的意义成为迷惑,它的崇奉成为嘲笑。谁希望认识我,他从自己抛掉那名字,而且听着自己。”(望·蔼覃128)
《野草》中的书写则是另样境遇,《复仇(其二)》中的耶稣是被他欲救赎的人间出卖和羞辱的对象,“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鲁迅,第2卷179);《颓败线的颤动》中被羞辱的老妇人发出无词的言语,却有神的巨大召唤力,“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鲁迅,第2卷211);而《失掉的好地狱》既批判了散发着神性光辉的具有欺骗性的魔鬼,又批判了人类的等而下之。(朱崇科,《家国同构中的个体突围》7—12)
相较而言,鲁迅更喜欢具有反抗精神的神鬼,而不太喜欢神或神化的先贤。《补天》中的女娲因无聊而造人,终究被自己所造小人闯下的补天大祸而压垮赴死,死后却依然遭他们利用,其中也不乏对女神自作自受的批判,虽然主要矛头指向的是人类。《起死》中,鲁迅固然批判了庄子的无事生非,非要让司命大神帮忙复活了500年前的汉子骷髅,但鲁迅对人类的缺乏超越性、过分执着于物质性与具体性的短视也顺手一击。
(二) 超越神鬼:鲁迅的开宗立派
论者指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对《小约翰》进行中国化的实践:“鲁迅的文字,背后总有些怪异的东西,好似受到了西洋版画的影响,有着明暗对比中的张力,意绪是深广的。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似忆旧,其实乃翻译了《小约翰》时的副产品,文章的深处,就留有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影子。倘不是译了《小约翰》,鲁迅不会写了如此美妙的散文,那文章的意境、手法,都染有望·蔼覃的色彩,虽然先生将这一色彩中国化了。”(哈尔克80)其实岂止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和《小约翰》有关联的其他文学创制也打上了鲁迅自己的烙印,可谓“别立新宗”。
相较而言,鲁迅的有关书写和《小约翰》相比发生了如下变化:
1. 鲁迅在创作中往往把发生场景置换成中国语境,并形成了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立人”的期许。除少数作品外,如《复仇(其二)》《失掉的好地狱》等,鲁迅绝大多数书写的场景,都已换成中国境遇,这是和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的文学创制主题关涉一脉相承的。略举一例,在杂文中,鲁迅先生也有所展开,比如《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就借给中国人画像(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加以批判:“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是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鲁迅,第3卷133)此中可能包含了《小约翰》中的人兽对比,但鲁迅的落脚点还是中国。
2. 鲁迅强化了对自我的批判,以及对鬼与死的集中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分构成了鲁迅的幽暗意识或阴暗面(darkness),③和鲁迅一直以来的悲剧意识、批判意识、自剖意识不谋而合。《野草》尤其是集大成之作,《朝花夕拾》中不乏认真清理“情感结构”的实践操作,包括对父亲、衍太太、阿长、藤野先生、范爱农、孝道、无常等等,而以上人物往往既是个案,又是文化类型象征。
3. 鲁迅赞许《小约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卓越的想象力与推进策略,鲁迅对此有所借鉴,但终究无法与之媲美,主要原因在于除了“准中期”以外,之后的鲁迅几乎缺乏类似的现实生存语境——晚年身处半殖民地上海的鲁迅多灾多病、群狼环伺,主要的文体变成了杂文,甚至《故事新编》都有很强的“油滑”与杂文化特征(朱崇科,《张力的狂欢》244—253),此中既有生存需要,又是战斗所需,也是自己精神气质的反映。
综上所论,我们既要看到“准中期”鲁迅生成的多元性、立体性和复杂性,更要看到鲁迅先生的独特性。
结语
郜元宝指出:“《野草》并没有单独完成鲁迅的‘哲学’,《野草》只是较多将这些哲学和宗教神学话题引人鲁迅一如既往的文学性思索,尤其是以更加精致的散文诗形式加以表达,因此容易被识别,而在杂文和通信中联系更加具体的散文化语境道出,就不那么显目罢了。”(郜元宝14)他看到了鲁迅思想脉络的贯穿性和阶段侧重性特征,这对于“准中期”鲁迅亦然。在鲁迅生活中历时22年的《小约翰》中译本终于面世,但这部一直萦绕在侧的杰作对于鲁迅的影响显然不止于此。相较而言,鲁迅此时期的《野草》《朝花夕拾》和部分《故事新编》有直接的关联,不管是书写风格、主题关涉,还是场景再现与想象力。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小约翰》又各擅胜场,而鲁迅更是有自己的后发特色,彰显出“民族魂”的思想高度与诗学魅力。
注释:
① 相关使用可参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具体可参拙著:《鲁迅的广州转换》。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③ 有关论述可参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均,陈琦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以及齐宏伟:《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论述。
引用作品:
郜元宝:《破〈野草〉之“特异”》,《鲁迅研究月刊》4(2019):4—17。
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郭梦莹:《从童话色彩看〈秋夜〉的生命哲思》,《绍兴文理学院学报》6(2012):21—24。
哈尔克:《谈〈朝花夕拾〉》,《鲁迅研究月刊》11(2002):78—80。
贺琴:《论鲁迅创作与翻译的互动关系——以〈野草〉与〈小约翰〉为例》,《理论界》10(2019):94—101。
李玮:《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鲁迅研究月刊》11(2018):39—46。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骆贤凤:《鲁迅的翻译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孙郁:《鲁迅的暗功夫》,《文艺争鸣》5(2015):58—66。
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王家平 吴正阳:《鲁迅创作与童话译著对话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6):89—99。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984):3—16。
杨炀:《“过客”来时的路》,《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8):25—30。
张芬:《“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见神”——唐传奇、〈小约翰〉与〈铸剑〉之生成》,《现代中文学刊》2(2011):58—64。
——:《张力的狂欢》。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原乡的春梦:〈好的故事〉之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11(2014):100—104。
——:《执著与暧昧:〈过客〉重读》,《鲁迅研究月刊》7(2012):30—37。
——:《家国同构中的个体突围:〈颓败线的颤动〉重读》,《平顶山学院学报》3(2016):7—12。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