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巨变”原是在生活中点滴发生的
“新农村”建设得究竟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寻找和获取答案,也可以通过阅读以乡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来获得感性认知,而后者,或许因为呈现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更深刻的人性,而以一种虚构的方式逼近了现实。
看见乡村的复杂性,看见转型中的人与人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乡村。这是本刊开设“新乡土小说”系列访谈的初衷和归宿——让我们在“新乡土”的舞台上,看一出出城与乡、新与旧、情与利彼此冲突与交叠的戏码。
首篇为“70后”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的长篇新作《宝水》,它以诗意的表达,呈现一场回归乡土的旅程,记录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当然,在我们跟随乔叶真正走进“宝水村”,和她一起追寻“故事”与“故人”时,我们会发现,“巨变”可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日复一日间悄然发生的极细微的变化。只是,日子久了,“巨变”也就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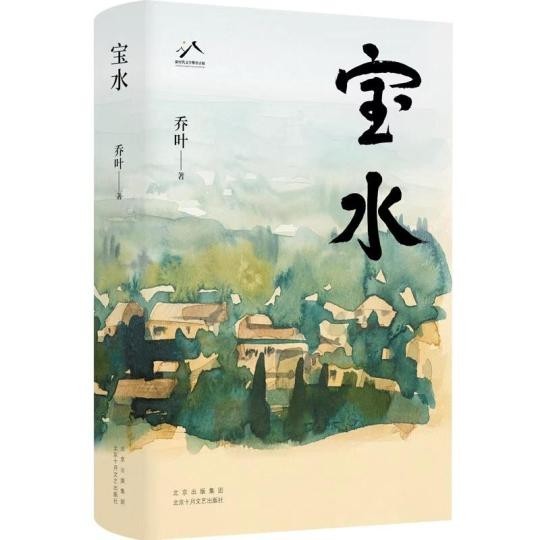
《宝水》,乔叶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离开才能拥有之地
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老家啊,就是很老很老的家,老得寸步难行的家,于是,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都只能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所谓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摘自《春》篇之“所谓老家”
上书房:《宝水》一经出版,就引发各方关注。这部小说的主题非常突出,甚至可以归入主题类创作,它写新农村建设,写乡村振兴。但它之所以如此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肯定,是因为它不是标签化的表达,它的文学性非常强,完成度非常高,在文学性和主题性之间,实现了非常好的平衡。而且就主题来说,它不是生硬和单薄的,而是呈现得相当丰富、相当圆润。不是一种想当然的主题写作。
有评论家认为,这是您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我发现,您最初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以乡村为书写对象,但您的成熟,似乎是从创作乡村题材开始的。这又似乎是当代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乡土写作的一种传统:从鲁迅开始,很多作家从乡村来到城市,然后在城市回首乡村、书写乡村。从您的切身体会出发,您认为形成这样的传统的原因是什么?
乔叶:我出生于河南的乡村,河南有很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我从2004年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写之前,通读了很多前辈作家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叛逆情绪——不愿意写乡土,反而想要清洗自己身上的乡村痕迹。但写着写着,我逐渐发现,书写乡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返程,从小流淌在我血脉里的乡土,带有一种精神的基因,是我所无法摆脱的。
我从小由奶奶带大,她去世后,我很想写一个作品来怀念她。我在《收获》上发表了《最慢的是活着》,写奶奶的生活,与《宝水》中的奶奶其实也有一个映照关系。那篇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虽然不能用获奖来说明问题,但至少提示我,乡村的生活和情感,对我有着根脉的意义。我写乡村时更顺手,更真挚,也更能打动读者。从那时起,我不断地从故乡汲取创作养分,虽然还不自知、不自觉。到了2011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首发非虚构作品《拆楼记》,写的是我姐姐家拆迁的故事,这类故事在今天很多乡村里上演。
写这些的时候,我和故乡已经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但似乎反而看得清楚了。我发现,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离开后,你才会不断回望它;通过回望,你才能从精神上真正获得它。
乔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认罪书》《拆楼记》《藏珠记》等,中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打火机》等多部,以及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庄重文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
上书房:虽然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但据说为了写这部小说,您回到农村,既“跑村”又“泡村”,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甚至发表一篇《跑村与泡村》来谈自己创作经历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大家了解到了您是如何“跑”“泡”结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生活,捕捉和积累鲜活素材的。这使得《宝水》做到了洞察世道人心,做到了深入生活的肌理,发现了乡村生活内在的规律和密码,最终成就了这么一部既有宏阔表达又有绵密细节的作品。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乡土文学似乎都胜都市文学一筹。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在前,以至于我有时怀疑,还会有新的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吗?《宝水》给了我信心。可见,只要眼睛向下,只要深扎生活沃土,只要有深邃的思考力,乡土有新变化,乡土文学也自然会有新作品的。
乔叶:对我来说,跑村和泡村肯定是必要的功课。创作不能是空中楼阁。
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农村一直在变,我也在长大,要创作,就必须去了解此时此刻的农村。一个人对农村的理解,和年龄、阅历是有关系的。经过了这几十年,农村随着时代潮流变化,青少年时期的经验经过漫长的发酵,我个人认知也有了拓宽与成长。
2014年,我去河南信阳一个村子参加一场和茶叶有关的活动。那里出产有名的信阳毛尖,山清水秀,和我老家特别不同,对我产生一种异质的吸引力,所以我特别想写。2013年,国家住建部评选了第一批“美丽宜居示范村”,我去的郝堂村就是其中一个,它还是农业部确定的首批“美丽乡村”。当时,村干部陪我们参观,他说自己的理念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我听了感觉好新鲜。那会儿,很多人的认知是要把农村建设得像城市。因为郝堂村村干部有这样的建设理念,所以,郝堂村村民大都留在了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也都回来做农家乐、做民宿了。这颠覆了我以往的农村经验,我就此写了二三十万字,但发现这二三十万字还是不行,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在写下这些文字前,我虽然跑了好几次村子,和村里很多人都认识、都能聊上天,但每次去的时候,他们像待客一样待我。就算我能猜到他们心里的弯弯绕,也还是一个“外人”。
只有当“外人”变成“内人”,我笔下的人物才活了。人情世故是小说创作的拐杖,没有这根拐杖,走不多远。
上书房:您是怎么把自己从“外人”变成“内人”的?
乔叶:我离开郝堂村后,恰好,老家南太行那边也在进行乡村转型,于是我就去了。虽然生疏,但祖辈、父母都葬在那里,我还算是“内人”,很容易就和村民熟络起来了。在那一刻,写一部长篇小说所需的人情世故的一口气,才算是贯通了。小说里,我老家是福田庄的原型,宝水村是正在转型的好几个乡村的结合体,其中还包含了我在信阳的体察,例如舞狮和做数九肉,还有“万物启蒙”活动,这活动是由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师们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做的。
上书房:宝水村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它像是一朵将开未开的花,有传统的一面,又处于文旅转型之中,不少年轻人离开宝水出去打工,也有很多人选择留下,还有很多游客来到宝水。宝水村像一个大舞台,不同人对乡村建设的观点,包括“地青萍”这个深入内部的外来者视角,在此碰撞,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有“功利”与“人情”的对撞,亦有人与乡土的联结。您如何看待村民与乡村的关系?
乔叶:村民在外打工时,是作为一个客体,但当他们回到自己家门口做生意,又变为一个主体。他们作为主体时被激发的骄傲感,其实很可爱。
从社会层面来说,很多农村人到城市打工,但等他们老去之后,还是会回到老家,城市往往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只有当他们回到农村,才能老有所居,地有所养。此外,国家也会给一些基本的保障,比如医疗保险,来保证他们回到乡村后的生活稳定。就个体来说,我关注很多打工人的生活情况,例如夫妻二人在城市送外卖,收入可观,但父母、孩子留在老家,他们内心还是希望最终回到老家,过一种街坊邻居都认识、在特定时间上坟祭祀、节奏缓慢的生活。农村有其特定的生活秩序,让人心有所安,身有所属。
与此同时,农村也有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全国约1/10的粮食、1/4的小麦都来自河南的土地。土地不像以前碎切后包产到户,而是大规模流转,所以很多人回老家后,要么种大片的地,要么不种地。不少人单纯是回乡养身、养心、养神、养魂,乡村是他们很重要的精神寄托,即便没有提供明确的显性价值,也依然具有情感价值,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文学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情感
大英其实对这位播音员的声音不是很满意,说他的声音力道不够,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比起来,那是差了可多意思。据说周边村的人听闻了闵县长在村史馆的发言后,也都不是很满意。他们说,宝水村的历史怎么能代表自己村的历史呢,根本不能。
——摘自《夏》篇之“新闻之闻”
上书房:《宝水》中的主角“地青萍”从城市到乡村,一方面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进入乡村,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在场性”,不断与村里人互动。因为身在其中,看待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无法再忽视农村的人情世故。这个角色能引发读者很强的代入感,您是如何做到的?
乔叶:代入感部分来自“我”这个第一人称。“我”对读者来说是具有欺骗性的,能给人一种同步的幻觉。小说第一段连主语都没有,读者就好像自家人一样,如影随形地跟着“我”走走看看。这是一个叙事策略问题,整个故事由“我”的限定视角,带来一种巨大的真实感。
当然,如果你想带给读者真实感,内容上的质感也要和人称匹配。书中有一段,“青萍”从山顶远眺,一直看到了黄河。“老原”就问她,是不是看到了福田庄?她说:“当然没有,但我不是一直能看见它吗?宝水如镜,让我总能从中看见福田庄。”事实上,福田庄已经被拆了一半,不具备完整的乡村形态了。对于“青萍”,故乡福田庄承载了她的创伤记忆,如同一个噩梦般的存在。宝水则是一剂良药,带给“青萍”宝贵的治愈感。“青萍”年少时,不理解村里人为何值得她奶奶付出,而她十几岁时的困惑,直至四十几岁时才在宝水村得到了解答。整部小说可以看到,她在一步步地重新走近乡村,她和乡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胜过年少时生活其中的那种亲近,是一种深刻的亲近。
上书房:通过文学写作这种方式,您想要保留怎样的乡村、塑造怎样的乡民?
乔叶:我希望小说呈现的内容有真实的质感,为此,我不得不迂回呈现一个乡村的“切片”。但我希望乡村“切片”的面积尽可能大一些,在片段之中呈现一种丰富性。即便在宝水这样一个小乡村,也有漫长的前史,我只能展现局部的真实。奥地利作家布洛赫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们不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更不是政府官员,读者也不需要我们提供详尽、精准的专业知识。文学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情感,在引发读者共鸣的基础上,社会问题自然会得以呈现。这就好了,因为我解决不了问题,而问题能被大家关注到,就是解决的第一步。这是我个人的小小理想。
大地的孕育、乡村的包容,具有一种天然的混沌。我一直警告自己,在表现人与乡村的关系时,不要太“知识分子气”,而要尽量调动角度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我”在村里看到“香梅”挨打,会哭,却讲不出“你不能家暴”的法理,而是在乡村的环境下,“我”感受到了无助和无力。难道把她老公抓起来,他们家就好了吗?家里的营生怎么办?孩子怎么办?“香梅”悄悄跟“我”说,她也会报复,于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报复,而非知识分子式的维权。小说展现了乡村自有的那套独特的伦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自洽的平衡,但这是否就是合理的?这是我借“我”提出的问题。
上书房:谈到家暴问题,确实,这部小说看似笔调温和,其实触及了农村一些非常重大的主题,比如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留守儿童的困境、大学生村官的适应性问题等等。但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左右迂回、腾挪,以一种真实但不尖锐的方式呈现,这恰恰也符合农村问题带给我们的感受——温和圆润的人情世故掩盖了部分尖锐的现实问题。
乔叶:我很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对我来说,不论写作什么题材,都要遵从所见所闻,遵从内心感受。我所见的乡村,就是这样丰富复杂的。尽管我们现在说乡村凋敝了,说她孱弱,但她依然是“母亲”,这名母亲依然能提供极其丰富的文学资源。
上书房:小说情节一点都不复杂,但每个人的心里,各有各的波涛汹涌。
乔叶:我很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本身对心理学也感兴趣。心理对写作来说是人物内部的逻辑支撑,就像骨头一样,如果缺钙的话,人就很难行走。
写出内心的“城乡接合部”
城乡之间,就是有这么多难以厘清的东西,这一池水,有多少人或深或浅地蹚过?正如那位种树莓的老板,我推断,他最初和村里人打交道时,村里人送这送那时,他肯定很享受这种额外的亲密,却很可能没想到,既是额外的,也必是突破了边界感的。他既然此时不说啥,在村民心里这种模式就应该是被默许了的。那么摘你的树莓时咋就不行了呢?你咋就觉得他们应该有边界感了呢?这边界感你觉得应该有时就有,你觉得应该没有时就没有,凭啥呢?某些时刻你享受着他们无边界感的热情,某些时刻你希望他们表现出有边界感的理性,这可能吗?你咋就这么双标呢?
——摘自《冬》篇之“极小事”
上书房:如您所言,《宝水》并非牧歌式的、悲歌式的、审判式的作品。那么,您如何秉承诚实的写作道德,去建构一种新的农村特质和农村形象呢?
乔叶:乡村在新时代背景下有许多兴变,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会对乡村民俗、乡民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常常说巨变,但巨变其实都是在一点一滴中发生的。比如,小说中写到乡里庆贺时贴了“收礼不待客”的通告。比如,原来你家没菜了,到邻居家地里薅一把很正常,你只需在门口喊一声,“我薅你们家菜啦”,对方可能根本不在家,但不管对方听没听见,你可是昭告过了,就符合乡村礼节了,就不算偷。现在,村里搞了文旅,你以前随便抓的一把“上海青”,炒一炒,装盘,卖给客人,就是20元钱。家门口地里的一把青菜,从没那么直接地变现过。于是你就有了微妙的商业衡量,你就不会去薅别人的了,你也不允许别人来薅你的了。又比如说,有的游客偷摘村民家门口的香椿。你不让他摘,他觉得“你怎么不淳朴了呢”,难免有些“我们给你们扶贫来了,摘棵香椿又如何”的优越感。但他对提供食宿的村民的要求,又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要求。所有这些,都是商业进入乡村后,对人的心理、规则意识产生了影响。宝水村需要建立全新的体系,以便应对外来的商业冲击。
上书房:您曾说过,“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这种“强韧”来自哪里?
乔叶:尽管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得很快,但费孝通先生写在《乡土中国》中的很多东西至今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的对撞和糅杂,甚于以往任何时代。一些学者写批判文章,说乡村衰败了、凋敝了、破碎了,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这样的。但国家这么多年对乡村的投入,真的都没有效果吗?或者说,大家认认真真去看有没有效果了吗?写《宝水》之前,我决定,我什么论断都不要听,我要让感官充分张开,凭借“眼耳鼻舌身意”,去看我能看到什么、我能听到什么、我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些所见所闻所感,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最终生产出一个文本。
我感受到的乡村,在变,但也有非常传统、顽固不变的部分。小说中有个情节,是我采集到的真实的故事。邻村有个家庭,母亲去世,孩子只停灵一天,就把母亲草草葬了,以免影响家里的民宿生意,村人就评价“这孩子薄情”。但在宝水,大家一起抬棺安葬九奶,人们就会评价说“你们村还是仁义的”。可见,虽然商业带来不少冲击,但村民依然保持着朴素的同理心,道德衡量标准是很传统的。
巨变需要砸碎很多东西,假如两三年就发生一次巨变,那么,砸掉的可惜,建立起来的也不结实。
你不深入乡村,很容易袖手旁观,随意指点江山,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可是,沉浸在乡村的氛围里,你更容易感受到它的复杂性。很多人过年回乡,都百感交集。一个人可能在上海过得很洋气,回到江苏或者河南的农村则是另一种状态,城市的伦理、清晰的边界,回到乡村,都被打成混沌的一片。所以,“老家”的存在特别有意思。
通过《宝水》,我想写出很多中国人内心的“城乡接合部”。
- 写出当下中国山村的生动图景作家乔叶谈她的长篇小说《宝水》[2023-03-03]
- 乔叶长篇小说《宝水》:一个乡村的重新生长[2023-02-10]
- 乔叶:领生活之命[2023-02-07]
- 乔叶:领生活之命[2023-02-02]
- 乔叶:以文学为掌,向岁月、生活和家乡捧献出一颗赤子之心[2023-01-17]
- 乔叶:永远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2022-12-30]
- 乔叶: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2022-12-27]
- 回到基本的生活中去——评乔叶《宝水》[2022-12-19]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