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我写作的灯塔 ——傅菲访谈录
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21年12月推出了傅菲最新散文集《元灯长歌》,该书以饶北河上游的郑坊盆地为叙述背景,描写人民坚韧不拔的生命景象,被誉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引起散文界瞩目。傅菲是当下重要的散文家之一,扎根赣东北,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写作20年,著述20余种,在题材开掘和文本探索方面,具有时代精神气象的深度和对文本开疆拓土的广度。本访谈以作家的写作观念建构过程,漫谈时代价值观、人民与土地、文本特质、难度写作、地域书写,及自然与生命意识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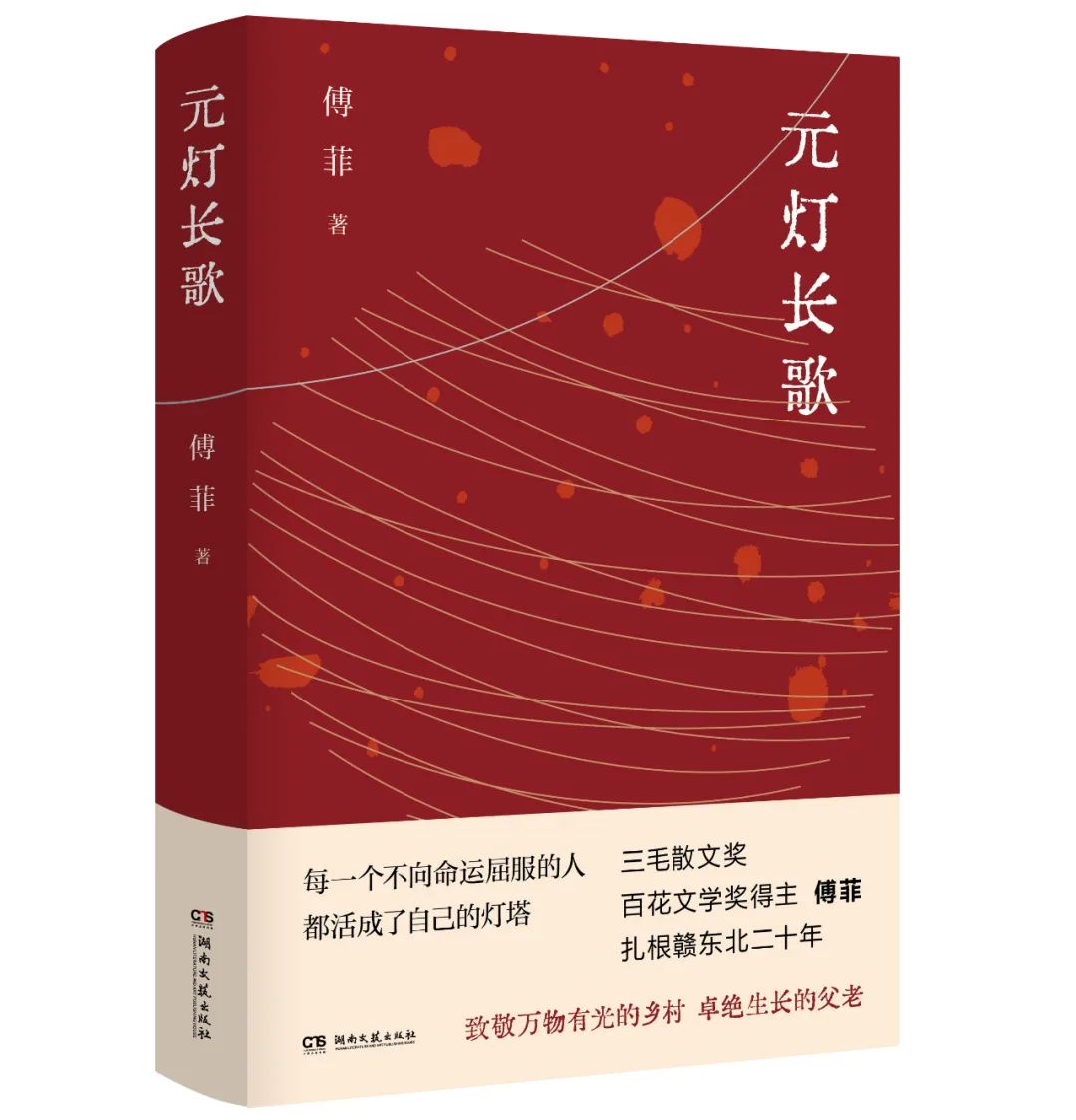
《元灯长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菲 著
杨晓澜(以下简称杨):傅老师好。很开心进行一次深度的访谈。作为一名期刊编辑,我关注您散文写作多年,我有很多问题,想得到您“解答”。
最先还是回到基本的问题:写作是寂寞的,也是快乐的,或者说是五味陈杂的。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前瞻和回顾,傅老师写作20年,出书20余部,能否从时间、地域、风格等角度对自我创作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这期间经过了哪些变化?哪个阶段让您辗转难眠、难以忘怀?
傅菲(以下简称傅):晓澜,您好。很荣幸接受您的访谈。
有一种天牛,孵卵时,把卵注入云实木质,在翌年春天发育为幼虫、蛹,然后孵化为成虫,即云实天牛,俗称锯木郎。写作的寂寞就相当于天牛全变态的发育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身是快乐的。写作的快乐,来自于自我对话、对自我的认知,并以此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为什么写作?是因为我们需要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此表述时代特征和个体心灵。
我是单一文体的写作者,只写散文。2002年4月,写下第一组散文,已然过去了20年。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坚持写这么久。我曾几度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写下去:持续开掘题材,需要写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2002年~2003年,我写了数万字的乡村抒情散文,讲究语言唯美、张力,质朴且高蹈。这是一种耗才华、虚空化的写作。我发现,我不能这样写下去,否则会直接写死自己。我搁笔了。我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写作,或者说,我找不到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因为当时对散文这个文学样式,缺乏深层次的认知。要在某个文体上有所发力,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深刻认识所写作的文体。没有深刻认知,不可能有高难度的艺术构架。认知的深度伴随阅读广度和写作难度而推进。
2004年初夏,因为生活及环境的改变,我患上重度失眠症,大部分时间通宵无眠。我把这个经历,写了下来,取了篇名《一个疾病的夏天》。这篇谈不上佳作的散文,却是我写作坐标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因此走向了叙事化写作。我从具体的生活中,直接检索素材,藉此表达人的生活、精神、困境等。在此阶段,我写下了较有影响的《米语》《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等篇什。2006年,我的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3年之前,我写作的体量也不大,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规划。简而言之,我是一个以随性而为的业余写作者。2013年元月4日,大雪夜,我坐绿皮火车从宁波返回安徽枞阳县,雪光和灯光交织,哐当哐当的火车声使得旅途异样虚幻。看着窗外茫茫大雪,我心绪难平,潮水汹涌。我决意写一本有关身体、生命意识、精神世界的散文集。
我居住在枞阳县渡津宾馆,每天写6000~8000字。我无法控制自己,激情潮涌,我在键盘上每敲下一个字,手指都是颤抖的。寒冷的冬天,我藏身酒店,自14:30分开写,至22:30分结束。冬天没结束,我就完成了散文集《饥饿的身体》书稿。这是我第一本有规划写作的散文集。在落笔之前,我就构建书的框架,定调了文本风格、特质、精神向度。
2013年7月18日,我前往福建省浦城县荣华山下生活,至2014年11月24日离开。我走遍荣华山的每一个山谷、南浦溪的每一个荒滩,对山中四季无比熟悉,我以叙述自己收拾院子为开篇,写自己的山居生活。断断续续写了6年,写了18万字,精选了12.6万字,以书名《深山已晚》结集。这是我的第一本自然文学作品集。
离开荣华山,我反思并梳理了自己的写作,规划了自己的乡村写作。我将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汲取写作的养分。我再次走向自己的出生地——上饶市北部小镇郑坊。一年之中,我必须坚持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村中生活,和村民一起散步、一起议事。在村中,我不是生活的观察者,也不是田野考察者,而是以村民身份长居的生活者。我走遍村中(面积约20平方公里)角角落落,调查野生动物生存状态,访问了以百计的手艺人、重症患者、鳏夫、离异者、嗜赌者、嗜酒者、创业者、退伍军人,收集散轶民间的地方典籍。等等。
这是我写作以来,发生最重大的转变——从书房走向大地、走向人民。
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动的江东父老。
我分体系去写这个南方普通的乡村,我试图构建自己的“清明上河图”。我写出了散文集《故物永生》《木与刀》《河边生起炊烟》《风过溪野》《元灯长歌》《远去的河畔》等多部乡村散文集。
您说的“风格”,我在此不说。否则访谈太长了。2013年以来,我写的每本书都不一样。与自己不一样,与别人也不一样。我的散文有我的腔调、句式、节奏和脾性。我的散文来自我脚下的土地,来自江东父老的呼吸。我的写作,是对自己安逸生活的一种“暴动”,也是对生养之地的一种礼敬。
在这期间,经过了变化。但没有哪个阶段让我辗转难眠。前期,是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后期,是深思熟虑。深思熟虑,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要素之一。我不再是散文写作的业余爱好者。
杨:散文写作,看似人人可写,可写好其实很难。一般作家都深扎一个题材,一辈子都在挖一口井,从您的写作历程看,却乡村、自然、风物、动物等多个系列,丰富辽阔,斑斓多姿,是如何做到的?有什么自我修炼和要求?
傅:散文是一种越写越让人敬畏的文体。散文的难度体现在思想的难度、变革的难度、题材开掘的难度、表现时代的难度等。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对于写作个体来说,像缓生树,很缓慢地、很艰难地生长——需要大量的积累。
乡村写作贯穿了我写作生涯。我出生于乡村、热爱乡村、长期研究乡村。我的出生地枫林村是我眺望世界、审视世界的一个哨卡。我把枫林村当作南方乡村变迁的标本去研究。
至于写自然、风物、动物,是我兴趣自然。我热爱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我差不多花费了7年的时间,自学博物学知识。我在多处国家森林公园暂居多年。我注重野外实践。但我的博物学素养比较低,所以很难写出优秀之作。
杨:散文界看似热闹,好作品却很少。甚至好的散文作家也极不稳定,很难出一批质量整齐的作品,尤其像您说的在思想上、题材开掘上、文本创新上有突破的很难。您对当前散文的整体印象是?造成这种境况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您的散文写作和审美主张是?优秀的散文应该具备哪几个特质?
傅:热闹,是因为散文写作门槛较低。散文队伍浪潮化,三五年一个小浪潮,十年二十年一个大浪潮。每一个大浪潮涌来,绝大部分写作者被淹没,少部分写作者在苦苦苦挣扎,极少数写作者劈立潮头。其实吧,其他文体的写作队伍也是如此,诗歌更甚。
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好作品稀缺。但有一些作家,在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内,一直为我们贡献好作品。某个文体领域的写作精英,都是极少数的。这是正常现象。
说到底,写作是个人的事。有人改弦更张,有人写不下去,有人坚持到底,有人以命相搏。我的散文写作是内心的需要。在一张写字桌前坐下来,我无比安静。写作和烧饭是唯二可以让我专注的事。我的散文气息就是安静、细腻、生动。
我的审美主张因题材不一而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淳朴、深邃、诗意、灵动、洁净、精准。散文最重要的品质是真诚、个性、价值观、美学、元气。
杨:最近读了您的散文新著《元灯长歌》,震撼,惊喜,深刻,这部作品绝对是您近几年的力作,可以说是倾注了您的心血。为何取名“元灯长歌”,这本书想向读者表达什么?
傅:谢谢您的喜欢。这是您对我最好的鼓励。
元:周而复始之始、初心。灯:光明之源。元灯:渊源;希望之灯;初始之灯。元灯是我祖父的名字,也是书中一篇散文的篇名。长歌是放声高歌、长声歌咏。长调式的歌咏给人盛世之感。
这本书以百年之大视角,写郑坊盆地的生活变迁,每个单篇均以人物为主体,以扇形叙事,以人民为中心,以诗性细腻的语言、独特创新的文本、充沛真挚的情感、悲悯温暖的格调、生动丰富的细节、饱满厚实的人文色彩,全景呈现当下乡村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为人民塑像,为乡村写志,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刻名,讴歌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
每一个不向命运屈服的人,都活成了自己的灯塔,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生命史诗。我重疏乡村生活伦理,再绘乡村鲜活场景,以拳拳之心铸就乡村魂魄,以朴素之语尽写乡村之美,致敬泪汗泡透、万物有光的土地,致敬卑微顽强、卓绝生长的父老。人民是我写作的灯塔。这是一部致敬父老、致敬土地之书。
杨:“每一个不向命运屈服的人,都活成了自己的灯塔,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生命史诗。”您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元灯长歌》这本书,从整体看是一个乡村的百年生命史,从《元灯》《大悲旦》《似斯兰馨》《浮灯》《焚泥结炉》《画师》等单篇文章看,又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个人史。您的散文好像一直非常重视“史”和“诗”的书写?为什么?这种史的使命和为小人物立传的担当和您的家庭教育、工作生活有无关联?
傅:个人史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大历史由个人史组成。没有个人史的书写,大历史的书写就失重。这是我的观点。《史记》写了很多贩夫走卒,让普通人物进入大历史。
在《元灯》《大悲旦》《似斯兰馨》,我写到一个共同的地方:葛源。这是先烈方志敏战斗的地方,革命时期,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的机关部驻扎在这里。葛源与郑坊只隔了一座山。郑坊人民也积极投身革命,与国民党政府作坚决的斗争。这段辉煌的历史,深深地塑造了郑坊人民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伟大品格。我父辈、祖辈的生命史融入了大历史。
我为小人物立传,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是不忘过去,也是我的职责。铭记过去,方可展望未来。美好的生活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人施舍。
杨:随着城市化进城加快,乡土文学越来越“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老一辈作家空有儿时记忆,徒有怀念乡愁,大都是凭吊式文章,年轻作家更是没有乡土经验,闭门造车。在这种两难之际,您却花大笔力聚焦乡土,底气和勇气从何而来?新时代背景下,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有了什么变化?乡土散文写作该如何发力?尤其是如何结合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的“山乡巨变”现象发力。
傅:这个命题很庞大。我简略回答。
还乡式、怀乡式的乡村散文,大多出自情绪、单纯的情感,缺乏长期的酝酿。我不说这类散文是否失真,至少忽视了现实。作家还是需要有逼视当下生活的勇气或素质。有人认为:乡村已死亡,或一去不复返。我不这样认为。“故乡已无法返回”是一种表象。乡村的体现方式多种:民间文化、情感伦理、人居环境、建筑样式、生活和劳动方式、思维方式。等等。
我厌恶幻像化的乡村写作。我不能忍受作家以“贵族式”的架势,居高临下地对待笔下人物。我必须与笔下的人物、草木、动物融为一体。所以,我必须以村民身份在村中生活、走动。我不能忽视他们和它们的生存状态、不能忽视他们的气象和精神面貌。假如我忽视,我就是麻木不仁,我不配写我的生养之地。
假如把时代比作一个人,那么文学就是珍贵的精血。一个作家,必须与时代面对面,正视、逼视、凝视、透视所处的时代。我们需了解过去、现在,还需瞭望未来。这就是大视野。
我写乡村散文,发力点在于写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不凡之处,讴歌温暖的人性,讴歌普通人的坚韧精神,同时给予丑陋的人性以批判。我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和土地。所以,我必须深入最底层的人群,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我的写作素材大部分来自生活的第一现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当下的现实生活主题,也是我当下写作的主题之一。这是个时代主题,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我写这类散文,更注重精神层面。我的发力点是深入生活的细部,藉此发现时代的精神脉络,写出时代的气血。本书中的《黑马之吻》《环形的河流》《焚泥结庐》《骑鱼而去》等篇什,就是这类散文。
杨:您确实非常注重精神层面,《元灯长歌》里,涉及山川大地、自然万物、乡村艺人、历史沉浮,除了日常生活形态和经验,您特别注重生命体验和人文精神探寻,外延和内切兼顾,写出了现在一般乡土散文难以抵达的高度和深度。
傅:谢谢兄这么高的评价。这是对我莫大的鞭策。
我所能做的,是深入、深入、再深入。我对郑坊盆地的一切,都无比入迷。我始终抱有孩童般的好奇心、惊喜心、悲欢心,对待我脚下的土地,对待我的乡人。在我心中,阅读土地与阅读书籍,同等重要。
杨:深入、深入、再深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您每年坚持三分之一的时间以村民的身份在村中长居生活,而不只是生活的观察者和田野的考察者。乡村生活很枯燥,这其实非常需要身体的承受力和精神层面的抵制各种诱惑,您怎么保持这种定力和活力?我也很好奇,现在的村庄和过去比到底有什么巨大变化?物质的也好,精神的也好,有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和故事?
傅: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人,觉得乡村生活很枯燥。其实不是。我很喜欢和村民聊天,去田野、山冈走走。我领头组织村民做公益。2019年正月,我个人捐资为村民建引水入户的水缸。2021年正月,我和另两位在外工作的邻居,带头捐资,在山中(老人散步的)峡谷,建了一个两层的石凉亭。建石凉亭,耗资比较巨大,村民积极响应,出工出力出钱。2022年正月,我和另一位在外工作的邻居捐资,为峡谷2华里山道栽树绿化。
我自然村的邻居有就读困难找我,有就医困难也找我。我是值得邻居信赖的人。我常常被邻居请去“主持公道”,调解纠纷。村里有大树被砍了,河里被人毒鱼了,村里马上有人给我打电话。乡政府做文旅规划,也来请我参加。我就是一个“好事”的人。邻居很隐秘的事(包括存款),也会和我说。他们知道我是个收集“故事”的人。我的散文现场描写,很细致很入微,来自于此。
杨:《元灯长歌》里,文章时空反复交错,题材反复交织,多声部,全景式,宏大叙事,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乡村立志;又细微化、个人史,书写个人命运,描绘动物生存,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宏大与细微的?
傅:我喜欢抽丝剥茧式写作。
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身体外部(脸部、眼睛、手部、脚部)和内部(心灵、思维)会留下时代的印痕。我需要花费极大的耐心,找出这些印痕。人是时代具象之一。笔下人物的生成,建立在熟悉度的基础上,建立在眼力、思考力的基础上。对地域文化与历史,我有较强的溯源能力。我熟悉脚下的每一块土地。
至于书写和架构,属于技法层面。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懂得方法论的写作者。在写散文之前,我对自己的写作,有过长达4年的严格训练。
杨:“抽丝剥茧式写作”说明您自我要求很高。可否透露一下这四年严格训练的秘密?都要做哪些功课?您觉得散文创作可以教出来或者训练出来吗?现在很多高校办了创意写作班。个人觉得天赋和勤奋的训练缺一不可,天赋不够,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一流的大师。
傅:在1988~1992年,我每天写3000字,写在大开的会议记录本上。我写的内容有这么几个部分:景色描写、人物肖像描写、生活现场描写、动物描写。我写了十几本。当时,我想写小说。要写好小说,必须要过白描、叙述这一关。神使鬼差的是,我跟几个诗人玩得很深,放弃了写小说,而是写诗歌了。
1998年,我放弃了诗歌。我彻底放弃了写作,去了很多地方游玩。我就想自由自在地玩。2002年,因为工作过于无聊,写了散文,就再也没停下来。
4年训练,给我很大裨益。我客观地说,我的描写能力比较强。
一般的写作水平,是可以教出来的。写作天才不是教出来的。我没读过写作训练班或写作学习班之类的培训班,对写作教学我没发言权。
我认为,自我的写作训练是必须的。训练的时间越长,写作的续航能力越强。
杨:不管写什么题材,怎么写,都是写人,人才是写作的核心。您的生态系列、动物系列、乡土系列,其实都是写“人民”,写“时代和人民”“土地和人民”,写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您说的“写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这种理解对吗?
傅:我赞同您的理解。
我理解生命、尊重生命。简而言之,我书写的主题是生命之美。个体生命具有唯一性。
杨:“致敬万物有光的乡村、卓绝生长的父老”,您写的这些人物都形象分明,真实现实朴实,饱满真诚,鲜活动人,在场感十足。如何让散文“在场”,带着血肉、温度,仿佛双脚踩在大地上?这种“人民史诗”般的书写,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又该如何更好把握?
傅:散文“在场”就是写作者在场。我融入了大地上的人,融入了故土的山川草木。我与脚下的土地,建立了血肉关系。我的身上带有他们的体温、气息、脾性。这样说,绝对不矫情。这种互融,不仅仅是因为与生俱来,还因为是我与他们内心世界的通达。
我的艺术立场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人民史诗”般的书写,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是写出时代的精神气象,为时代立心、为人民立言。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象是一个时代的生机,也是我们国家的生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
把握好这个主题写作,是贴近、贴紧、贴心,放眼时代,着眼于人。
杨:散文写作的同质化严重,体现在题材、文本、技法等各个层次,而您的写作却别开生面,写作手法千变万化,写作题材不断拓新,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等多角度介入,情感、审美、思想等立体性呈现,融合散文、小说、诗歌等技法,这种跨文体和多个向度的表达,让人耳目一新,为中国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这种创新上,您企图做到什么?又如何更好展示?有信心走多远?
傅:兄这样高看我,真是不敢当。这是真心话。
散文写作的理想之境,是无我之境、无法之境。无“我”不是没有“我”,是指在大我中确认小我,在小我中找到大我。无“法”不是没有“法”,“法”是方法、法度。无我、无法,是指自由。散文的一切限制,都是自我限制。散文应该是没有限制的文体。没有限制是建立在纯熟表达之上的。写作手法要做到千变万化,确实很难,需要很纯熟地掌控语言、架构、人物。
我的散文写作谈不上企图。我唯一的野心是把郑坊盆地写得充沛丰盈,写得无涯无际。所以,我属于长卷式写作。我以不同的系列去展示这片土地丰饶。
走多远?我很难说。假如我对散文一直保持热爱,我就会一直写下去,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去开掘。
杨:“把郑坊盆地写得充沛丰盈,写得无涯无际。”这已经非常了不起,《元灯长歌》也做到了,更难的是写出了与读者的共鸣共情,看《大悲旦》《刀与猴》《红嘴山鸦之死》《落叶堂》等篇章,不少人都说看得掉眼泪。在这本书里,有没有哪篇文章让您费尽心力?自己最满意哪篇文章?
傅:《元灯》《大悲旦》《盆地的深度》《画师》《墨离师傅》《似斯兰馨》《环形的河流》《焚泥结庐》等,都是我费尽心力之作。《画师》构思一年之久,《似斯兰馨》5易其稿,《环形的河流》历时3年完稿。《焚泥结庐》这个标题,想了半年之多。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画师》《盆地的深度》,对人性有深度勘探。
我表哥水银年长我一岁。2005年,他孙子2岁时,检查出患有法洛氏四联症。这是必死之症。死亡率高于肝癌晚期。水银跑到我这里,说,孙子要不要治疗,治疗费很高额,即使动了手术,也活不了几年。我说,这是活生生的人,当然要治疗,哪怕多活一个月。水银说,全家人支持放弃治疗,费用太大。我借了钱给水银,送孙子去上海治疗。孙子在2017年冬病逝。喷血而死。我和水银无比心痛。这个故事就是《落叶堂》。生命多么珍贵。
《大悲旦》《红嘴山鸦之死》《落叶堂》《盆地的深度》等篇什,在写作过程中,我均数度落泪。
杨:当前,散文的非虚构大行其道,但在重视生活的真实再现时,却忽略了散文的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一味做生活简单的记录员,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从《元灯长歌》可以看出,您非常注重语言的打磨,把每一行文字、每一个字词都放得非常妥切、精到,张力十足,大有境界。更难得的是,透过您的语言和故事的背后,有着犀利的时代洞察,深邃的人文思考,丰厚的情感表达。
傅:非虚构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事实就是力量。
非虚构作品确实大行其道,但好作品凤毛麟角。非虚构的作品,我关注度不是很高。说到底,实实在在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一切艺术都注入了想像。采访手记归类于新闻,更适合。
《元灯长歌》来自我的生活、土地、情怀和思想。语言来自我多年的诗歌写作。更主要是,我为这本书积累了20年。
杨:20年的积累,20年的乡村生活,才厚积薄发写就这本书,可谓字字辛酸泪。有的非虚构作品,实地调查走访可能就只花了几天时间。散文虽然注入想象,但很多作者忘记了散文的常识性问题,那就是“修辞立其诚”,要有真的素材,真的感情,真的创作态度,而不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追逐某些名利。
傅:别人如何写,我不知道。
我不为任务写作。“修辞立其诚”,诚就是诚实、真诚、诚挚、诚恳。作家血液在墨水中的比重,就是“诚”的浓度。
杨:当下太多的散文结构松散、精神涣散,境界和品位缺乏,我们该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接续《古文观止》等的中国散文文脉,打造我们的现代散文经典?我们都在讲散文的革命,但连散文最核心的“情感性、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都缺乏了,未来的散文如何革命?如何才更有深度、广度和高度?
傅:您说的“境界和品位缺乏”,我换个角度说吧。我觉得还是写作者缺乏“聚精会神”的专注度。
写作者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每一篇新作问世,都应该是对自己的一次文学变革。对我自己而言,每写一个系列,都是对自己的一次颠覆。我必须深思熟虑,谨慎而行。我们的中华文脉,有两条路:延绵的思想,经典的语言。语言的容器容纳思想。
未来的散文如何革命是个大命题。在没变革之前,又是个伪命题。但确实值得探讨。窃以为,散文要发展,需引入其他文体的写作元素,从广阔的真实生活汲取营养。唯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丰足的文化底蕴,才可以支撑起散文的深度、广度,建立起散文的高度。散文所表达的一切,离不开对生命的认知。对生命的认知深度,是建立在生活、阅历、知识、价值观之上的。这是一个系统。对生命有足够的认知,才谈得上散文的品质如何。
杨:是的,要有对生命的认知,也要有写作者“悠远”的追求。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素材很多,舞台广阔,我们是否该有更多写大作品的雄心和野心?您的写作野心是什么?
傅:写出大作品,需要文学之外的因素。
何谓大作品?经得起任何时代的人阅读,才是大作品。
有雄心和野心的写作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诗人和小说家。现实层面又是另一回事。
我知道这个基本事实:我对任何事情不适合有野心。我只有老老实实写,扎扎实实写。我还没有让读者不遗忘我的能力。
杨:老老实实写的作家会有很多读者青睐,读者虽然没有过目不忘,但据我所知,您有一批忠实的“菲粉”,《读者》《意林》等畅销类刊物经常转您的散文。写书最终还是要有读者看,新媒体时代,散文创作如何吸引更多读者?您觉得《元灯长歌》这本书或者您的理想读者是什么样子?
傅:我从事媒体工作近30年,知道传播是什么一回事。
文学是很难有外溢的。大众读者超过1000字,便懒得阅读了。有图有视频最好。文学仅仅是圈内的少数人阅读。高端读者很少阅读当代书籍,除非是工作性阅读。但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根脉之一。从这个角度说,书籍选择读者,读者选择书籍,而非吸引。
《元灯长歌》适合有思想深度的中年人阅读,适合对近代史、现当代史有思考的人阅读,适合探究散文写作的人阅读。从文本角度说,非常适合爱好散文、研究散文、写作散文的人阅读,因为这本书,确实有可贵的散文探索。当然,热爱乡村的人,研究乡村的人,是我的理想读者。
杨:您被称为“刊物收割机”,在近10年,以量丰质优的创作实力,频繁在《人民文学》《钟山》《天涯》《花城》等各大文学类核心期刊发表重头作品,很多刊物给您开专栏。比如最近《长江文艺》就给开了一个新专栏,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怎么样?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傅:我确实写得很专注很丰沛。我放弃了高薪工作,专事写作。我想写出自己想写的作品、有自己高度的作品。
2022年,《长江文艺》给我开了“灵兽录”专栏,写哺乳动物的,每期一篇,每篇写一种哺乳动物。写人与动物的故事。专栏作品,在2021年5月,就已完稿了。2021年9月~2022年3月,在写大茅山山脉。我居住在大茅山脚下已有半年之余。目前已完成了《鸣山》(暂定书名)。
2022年,《黄河》杂志还给我开了一个专栏,得把这个专栏完成好。
下一步写什么,我还没想好。暂时打算休息半年。在2021年冬,我想写一本乡村正常死亡的书,素材积累得差不多了。
谢谢兄在繁忙的编务中抽身,完成这个访谈,我非常感动。我唯有努力写作,才不辜负兄的鼓励和鞭策。
受访者简介:
傅菲,江西上饶人,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20年。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发表作品近600万字,收入200余种选本,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故物永生》《风过溪野》《大地理想》等20余部,曾获三毛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奖及多家刊物年度散文奖。《元灯长歌》为其最新散文集。
杨晓澜,中国作协会员,《芙蓉》杂志编辑部主任。
- 刘琼:写作都有瓶颈期,我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2022-05-20]
- 傅菲:“抵抗遗忘”是对写作者的最高要求 [2022-05-19]
- 凌春杰:生命与情感的表达式[2022-05-12]
- 对话名家 | 刘 琼:让记忆和文化在字里行间交融[2022-04-26]
- 调色板上的颜色——文学、绘画与舞蹈的灵魂旋律[2022-04-20]
- 傅菲新作《元灯长歌》出版,致敬万物有光的乡村[2022-04-18]
- 我有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2022-04-08]
- 吴佳骏:先看到生活本身,再去好好生活[2022-04-01]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