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铸剑》:复仇与志爱
《铸剑》有一大疑点:明摆着的文不对题。贯穿《铸剑》的情节是复仇,而非铸剑,后者仅作为故事前提稍作交代而已。八篇《故事新编》里,唯“铸剑”一题所寓之事早已完成于过去且退入背景,而其他七篇的篇名则一律是内文所述当时之事的旨钩。
如果说“铸剑”是这篇作品的原始题目,那还好说,因为标题吧,有时无非“沿用”。然而这篇不是。1927年4月25日,此文首发于《莽原》时,鲁迅用的题称是《眉间尺》—这个无论如何都是看着更对文的题。要到1932年鲁迅出《自选集》时,我们才看到原题改为“铸剑”。如此改,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是为了将来1935年出《故事新编》八篇时,所有标题一律二字排开吗?鲁迅应该不至于在成书还稍无眉目之时,为了一个虚讲究,而如此“超前部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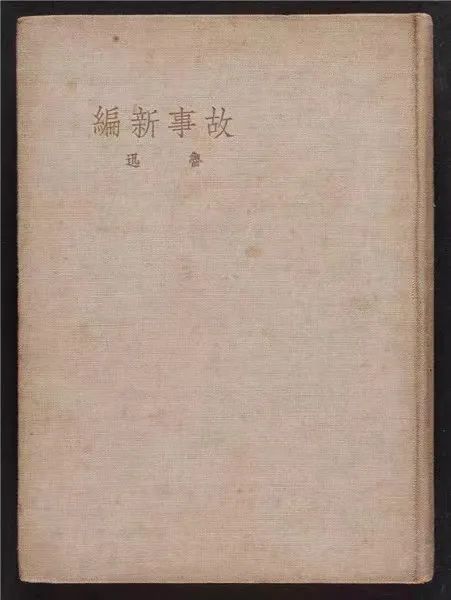
《故事新编》1936年初版本
关于“铸剑”这个题目的讨论,相信历来应有不少。在细读文本、思量作者用心之后,我把这一问题拉高到理解《铸剑》的关键位置。改题,是鲁迅的一个非常慎重、有点促狭的决定,让“题”既更精确提摄创作旨归,又同时下了一个稍许恶戏的路标。正由于此“铸剑”非(读者我等一向直观设定的)彼“铸剑”,那如何理解“铸剑”就成为掌握这篇小说的关键了。
先厘清《铸剑》在《故事新编》里的特殊性,或许对即将展开的探索有些帮助。如果暂且不论写于《呐喊》时期的《补天》,《故事新编》的其他七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欲在古代中国传统中寻找尊重客观现实与主体实干精神的思想资源。这些篇率皆扬墨抑儒损道,凡《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皆属之。在形式上,写于鲁迅逝世前两三年的这几篇还共有一特征:文字中难捕作者身影。另一类则是鲁迅1926年底到1927年初流寓厦门与广州之际所写的《奔月》与《铸剑》。与前一类对照,这两篇首先是不直接涉及思想流派的重估,其次则是屡屡展露作者侧影。小说不仅借古喻今,更借古喻己。或许由于作者“自我”的“投入”,一般认为这两篇有较高的“文学性”,从而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是《铸剑》。如果这个分类成立,那么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对《故事新编》所下的定位—“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至少对《奔月》与《铸剑》而言,就不是完全妥帖了,因为作者形象在其中有强势伸张。
既然细读文本、知人论世以解“铸剑”之意,是阅读《铸剑》的一个法门,那么以下就是我的展开。
一、青与黑合
《铸剑》说的是小伙子眉间尺伙同一位神秘“黑色人”,为其父—一位剑成献于王,反遭杀人灭口的铸剑名工—复仇的故事。小说强调三种颜色:以眉间尺为青,黑色人,当然啦,为黑,而王则是金—呆滞无聊而残暴的王发噱的名言是“金龙?我是的。金鼎,我有”2。小说以“青”始,而后“黑”现,而后,青黑二代人齐头断“金”,完成复仇。
如果黑色人不曾出现,眉间尺大概率是复不了仇的。小说开始于鼠辈横行的远古一夜,为之不能寐的少年眉间尺起身除害,但却只是一味优柔寡断,无能于“痛打落水鼠”。这一切都看在他母亲眼里,很是痛心,问他是“杀它呢,还是在救它?”眉间尺除了优柔外,还带着点儿青春期的自我厌倦。眉间尺又名眉间赤,红鼻子也,而小说里说眉间尺“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哈姆雷特者,吾国古已有之。
“不冷不热的”、青涩的眉间尺在答应母亲一定会把他“优柔的性情”改掉后,就穿上青衣,背着青剑,走上复仇之路。这把青剑是当初承造者预感不测,匀出委托者的好铁料偷偷多铸的一把,其性属雄,而交出去的那把则属雌。古之大匠作,都通阴阳术数,晓得复仇为一纯阳之事,而根据雄主动雌主静,留下雄剑送出雌剑也算是“良有以也”。鸡鸣声起,眉间尺正好十六岁。目送的母亲想必神伤自责;为了不违复仇大义、实现亡夫遗志,她把孩子—一个无望于复仇的青年—送上了几乎就是败亡之路的复仇之路。她并不如读者我们这般幸运,马上就知道有一个黑色人会跳出来帮她的孩子。
年青也会限制想象。眉间尺所能想象的复仇方式就只是伏击行刺之属,但这根本就是无谓的牺牲,无法越王的雷池一步。嫩青一枚又如何是专业杀人与保防者的对手呢?后来的沸鼎人头大战不就证明了孩子是完全招架不住王的毒辣手段的吗?黑色人深知眉间尺“报不成”,于是他曾果断阻止眉间尺的飞蛾扑火。小说交代“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脚”—那个人能是别人吗?黑色人阻断眉间尺的热血暴冲,不止是因为总还是“一冷一热”的他徒将送命,更是因为即便谋刺成功,也不见得就会改变权力定势,反而可能更加巩固反动。唯有能辨别统治集团的脆弱环节,才能准确投枪,也才能在复仇的同时带来真正的改变。鲁迅写到此处,不知脑际曾否突现一念:要是能拉住更多青年的脚使他们免于流血该多好!
眉间尺起初所怀抱的仅仅是以血偿血的复仇,而黑色人所怀抱者则大于此。他是一个复仇者也是一个反抗者。反抗不能徒恃勇气,还得有沉着与辨别的能力。小说里,黑色人就是凭借他“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3的能耐,突破了复仇闷局,将疑心满满的王赚到鼎边,而后剑起头落。黑色人看什么看得较分明呢?—他知道如果对王声称那颗青头“正在鼎底作最神奇的团圆舞”,则王必定奔来。为何“团圆舞”是王所无法拒绝的?因为至少自《阿Q正传》以来,鲁迅就认定“团圆”是旧社会取消一切可能变革的一条无上指令,是让一切“热”为之变“冷”的机转,而因此也同时是王的统治基础—“凡事总要‘团圆’”4。“王”,在作为狭义的复仇对象之外,更是“旧”的核心象征,体现了烦闷、无聊、只想看热闹、看“新鲜”、看杀,是老百姓看客大群的身体奴虐者,但也豪华地体现了他们的“末人的”精神。革王之命,因此不是刺杀行动,也不是狭义的政治行动,而是思想斗争、头与头的战争。
黑色人的素描:“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这几乎就是作者的炭笔自画像。在王之前,黑色人自报姓氏籍贯:“宴之敖者;生长汶汶乡。”“宴之敖者”(被家里的日本女人给赶出来的人)是鲁迅指向1923年兄弟绝交之事而取的自嘲之名。“黑色人”确实折射了作者身影,倾注了作者自我。这应无可疑。但是,鲁迅为何选“黑色人”之名呢?如果眉间尺的“青”象征了青春、希望与稚嫩,王的“金”象征了权势、欲望与腐败,那“黑”又象征什么呢?不能仅是“黑瘦”吧!
舍更顺口达意的“黑衣人”不用,而用“黑色人”,是为了凸显“黑”所象征的一种存有性。读鲁迅文章,常能感受到鲁迅有一种守黑而后知白、知旧而后择新、体无而后用有、沿绝望以索希望的精神特质。不能体会暗夜、虚无与绝望的人,对鲁迅而言,是不足以语希望、战斗或光明的,因为你将为白光所盲、为实有所囚、为希望所愚。这是鲁迅与“新青年”“新月派”乃至“创造社”“太阳社”等左右无论的团体或个人的最根本差异。在文学上,这样的一种精神与思想状态常表现为鲁迅对“黑”“暗”与“夜”的肯定,甚至礼赞。一反俗见,鲁迅认为真正的光明与群性反而是以在黑暗与孤独状态中的体察觉悟为前提。这一种为了有别于西方启蒙而我暂名之为“内光启蒙论”的立场,几乎贯穿了鲁迅一生。早在《破恶声论》里,他就提出了“内曜心声”5。而后,在《野草·影的告别》里,鲁迅捏了一个要与“我”告别的“影”,因为后者不能忍受前者总是有一个外在的实有的黄金世界的设想,然而它又不欲屈服于“黑暗与虚无”,于是只好“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6又例如在《夜颂》里,鲁迅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从而“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7又例如,临终之际,鲁迅一感病势稍缓,也要打起精神,在夜里感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8。
相对于“白”,“黑”代表了一种愿居下流、宁受物之汶汶的主体状态;以一种类苦行的方式领受所有杂色、所有能量、所有苦难,而非将它们反射、隔膜出去,以保自身的清凉、洁净与高尚—而那就是“白色人”的、“新月”般的主体状态了。我几乎想象鲁迅是透过“黑色人”表达出一种左翼的、革命的黑色观世音,听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黑色观世音神魔难辨,如一株参天古木一般“超越善恶”,接上了多少光明就意味着同时吸收了多少“地底下的”黑暗。黑色人的身与心必然永劫于明与暗之间。他是孤独的,却也亲证了“大群必独”。
存有性之外,“黑”也有历史的一面:“黑色人”不妨也就是墨者、墨侠。在一篇探索历史中“改革者”堕落历程的杂文《流氓的变迁》里,鲁迅快速翻阅历史的泥沙俱下,其中几乎只表扬了墨者,赞美他们是不知取巧的侠,是“爱”的苦行者,虽有时不免近于“傻子”,但绝非“伶俐人”。9《铸剑》与这样一种敬墨之心不悖,从而与《故事新编》里很多篇扬墨抑儒嘲道的小说可谓殊途同心。黑色人对眉间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这个“只不过”,意味了黑色人的“报仇”只不过是沛然的“由仁义行”,而非自伐其德的“行仁义”。报仇是行动而非请客吃饭做文章,因此无法避免“以武犯禁”。《铸剑》也不免折射了鲁迅对甘地或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的一种拒绝姿态。
唯有掌握鲁迅对“黑色”的一种存有性的、历史性的感受,我们才能以一种会意而非“考据”的感受方式,理解下面这段话。黑色人对眉间尺说: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他被杀就是我被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这是承受所有古今痛苦之人的世界之暗与世界之重的“黑色”状态,而其核心却又是一种超乎关系、超乎功利甚至超乎理由的,从而是无比的爱。
黑色人固然“沉着、勇猛,有辨别”10,但他也许如《野草·希望》里的主人公一般吧,自觉“大概老了”,必得找到“身外的青春”携手向前。11眉间尺应是黑色人找到的那个身外之“青春”。
二、以爱铸剑
前引的黑语于青那段文字是《铸剑》篇眼。眉间尺如是听说,心灵深处电击,随即砍落项上人头,于匍倒前将剑交与黑色人。能令眉间尺心灵颤动的,应就是黑色人所透露的闻所未闻的“无我的爱”12。黑色人夹杂着一抹近于父爱但却又远比父爱辽阔的爱,竟让那之前总还是“不冷不热”的眉间尺决绝杀身。黑色人于是“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后头的事,我们都知道,就是黑色人穿起那袭青衣,携着青剑与青年头,唱着满是“爱”字、愚智难辨的怪歌,或谓“爱歌”,向王城“扬长地走去”。黑色人穿起青衣,形象上落实了黑与青的合而为一。
眉间尺自去其首是一种观看法,另一种则是自去其身、魂从知己。我们应从后者。“自去其身”即是将凡属私的、我的,甚至“吾之有身”都一概取消,并与对象达到忘我乃至忘死的合而为一。黑色人爱歌里的“头换头兮”,难道不是“爱”的最纯粹体现吗?因此,黑与青合,既是两代人之合,更是“中间物”与“身外的青春”的革命之合,而合的基础则是爱。此处的爱,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爱情”,因为它有向上的目标、完全的信任,且稍无嫉妒。爱当然可以发生在两性之间,但这不等于只能“在异性中看见爱”13。于此,爱与革命初心无二,皆建立在那自恋的、所有格的自我的取消,以及,为他人而活。《铸剑》因此可说是对当时流行的“恋爱加革命”文学的现身说法的批判。半世纪后的台湾,陈映真在他的小说《贺大哥》里,透过主人公表达了抗拒虚无的唯一依仗即是“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14。陈映真也在同篇小说里表达了一种鲁迅式的小大辩证:人唯有将自身看做人类向上大潮中的一滴水珠,才能藉由与对象的一体而克服个人的虚无,于是,反而成其大。15
然而,以爱与信穷尽黑色人与眉间尺的关系内容,似乎又有些不足或“过于”—过于伟岸。文学不是宗教或哲学,毕竟还是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为关切对象。那么,我们可否问:这个爱,具体而言,是透过什么形式或介质展现的呢?
直接这么问吧—眉间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也许会说,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当然是男的,没看到代名词是“他”吗?作为原材料的“故事”里的眉间尺当然就是男的,例如《列异传》就说得很清楚,干将交代他妻子:“尔生男,以告知。”然而,在《铸剑》里,男孩儿,或是女孩儿,则成为问题了。铸剑者临别对妻说:“待生了孩子,好好地抚养。一到成人之后……给我报仇!”行文至此的鲁迅,选择以“待生了孩子”取代“若生了儿子”,用心应该是明显的:革(王之)命不分男女。作为作者,鲁迅先前已经让眉间尺的父亲留下雄剑了,他似乎很不情愿非得再让他的后生是男儿。是男,是女,都成。想象眉间尺也可以是一位女青年,应该就是鲁迅的“新编”之一。
这一新编,于小说逻辑并无妨碍,因为读者可以想象眉间尺之母就是以“若男”的方式抚养他,并要求他为父报仇。鲁迅笔下,眉间尺时露女儿眉目,例如在鼎里,眉间尺的头“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笑容;头发蓬松,正如青烟一阵”,“眼珠向着左右瞥视,十分秀媚”,而当王俯视沸鼎时,眉间尺的头“便嫣然一笑”。鲁迅为何执意勾画一抹女子相,甚至,为何黑色人要对眉间尺“接吻两次”,不是一个可以随手放行的疑问。
文学创作有属于它自己的规定,好比一个人是男是女,一般而言,你必得选择其一。作为一个作者,鲁迅在写作上似乎并不曾明白挑战传统的性别设定,以“他”代称眉间尺。但是,这个设定与好比设定后羿为“他”、嫦娥为“她”那般的确凿无疑,是不同的。《铸剑》里代表眉间尺的“他”,是表达“男或女”“他或她”的唯一可能。现代中文里,我们可以用“他们”涵盖“他与她”,但我们还没有一个适当的代名词表达“他或她”—这造就了今日政治正确论文里不胜其烦的“他或她”,以及网络字汇“ta”的出现。鲁迅当年为了要表达这个“他或她”,只能回到白话文运动前、用之千年的“他”。
《铸剑》有好几处不确定性,“剑”何所指是一个,结局为何是一个,而眉间尺是男还是女,更是其一。鲁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欲将这一问题权威定死,寄望读者既能以男孩意象近之,但也不妨以女孩近之。为何如此?可能原因有二,其一已如前述—革命不分男女;其二则是属于作者传记性质,后面将会谈到。
因此,在黑色人与眉间尺之间的,就不只是同哭者之间、两代人之间、男性革命者之间的爱,同时也可以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对男与女这一维度的浮现,我们应该避免立即掉入今日吾人,透过好莱坞及其他,所太熟知的西方浪漫爱意义下的“爱情”与“恋爱”套路,进而想象一种以男与女为形式、为中介所体现出的无我之爱、向上之爱—这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中其实并不稀有。因此,《铸剑》无关所谓“代别”或“性别”的身份政治,因为他俩不是以性以代为别为分,而是两代人的、男与女的,再说大点儿,也就是人民的,精神与意志的铸合,如一把利剑,刺向那个“金龙我是”的王。三头之战功成之时,黑与青“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庄子·大宗师》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们不妨称他俩为爱人同志。值得读者我们思考的或许有两点。首先,这一双头颅不是西方浪漫主义做派的向天拔升,而是一种悖论式的向上自沉。如此看,约略同时的《奔月》是对一种“爱情”的嘲弄,而《铸剑》则是一种大爱的庄严宣示。其次,如果对鲁迅而言剑有雌雄,那么头缘何独无男女?道理上,眉间尺可以为男可以为女,但我总觉得鲁迅私心慕其为女。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黑色人与眉间尺的复仇行动里,并不曾有过自以为义从而以他人为手段的想法:决绝而不嗜血。革王之命的行动中,他人的生命该怎么摆,始终是一个关切点。眉间尺的“优柔”,于是有两面性:一面是寡断,另一面则是常葆不忍人之心,总是怕伤及无辜。鲁迅对这个心肠是肯定的,因为他痛恨李逵之类的抡起板斧排头砍向看客的“反抗者”。在黑色人与眉间尺各自唱的“爱歌”里,都出现过这样一句:“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如果说黑色人有作者的浓厚身影,倒也不意味作者就不能将自身的某些质地投射到眉间尺身上。
因此,在表面的残酷荒诞下,《铸剑》的底色是爱与昂扬;即便在魂灵也都寂灭了的终极死亡时刻相值,他们也是“仰面向天”。在不轻“武器的批判”的同时,高举“头的斗争”,强调爱、信任、辨明与意志。于是,我们来到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黑与青的团结复仇最后“成功”了吗?比较悲观的读法是革命者虽革了王命,但自身却被整编到金盘金棺的体制与仪轨之中,太庙尚飨兮。而且,或许由于过于被鲁迅从“幻灯片事件”与《药》以来长期关注的“看客”意象所制约,小说终局也不免让读者油然而生一种志士牺牲无谓、世间麻木依旧的感觉。但这样一种阅读感觉,用在《铸剑》上,似乎理路虽通但感觉总是不对头,与整篇小说所透露的昂扬精神不对头。所幸,在一次小型讨论会里,江湄教授指出了惰性与麻木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三者同归于尽、骨发难分彼此,毕竟客观上造成了“王”与“逆贼”无法分清的效果,严重松动了礼法秩序,乱由是生。这个解读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小说的确结束于“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这一句。这意味了老百姓的看客热情开始降温了,而这将让他们对“巨变”的等待,更加焦躁而不可忍耐。杀王屠龙为的就是醒民。承认黑青“铸剑”所造成的颠覆效果是重要的,唯有如此,昂扬之气才不至于在结尾处给岔了气,变成不雅的打嗝。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不是行动所带来的“功效”,而是革命者主体状况的改变。经由黑青同心,眉间尺明显袪除了他原先的“哈姆雷特状态”,不再优柔寡断,不再“不冷不热”,而是敢于削下项上物、痛咬落水头。的确也不妨说,眉间尺这一把“剑”炼成了。黑色人也有变化,革命路上与子同行,不再彷徨孤愤。于是,我们看到鼎沸之战时,黑色人的颜色竟出现了类似铸造上的变化:“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此刻的他,应是不会再说:“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青色人与黑色人的改变是在同一铸造过程中完成的,有歌为证:“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两个复仇者头换头而为一,不再孤独。
“铸剑”是人民团结的象征,是一把情志之剑。眉间尺之父所铸的剑有两把,敌我各执其一;人民有,独夫也有。但眉间尺与黑色人“头换头”所铸的精神之剑则是独一的,为残忍无聊呆滞的王所无。对于实体之剑,鲁迅固然也不曾否定其重要,但他应是更认为唯有人民的主体炼成才有希望克服那以暴力、看客与礼法为营盘的独夫民贼。因此,“铸剑”的所指必然不是那块铁的所化之物,而是眉间尺与黑色人以爱与信任炼成的团结,并以两颗头颅相继跃入炼炉(“金鼎”)之刻,达到此一炼成的最高点。这个情节也让我们想起了传说中干将的师傅与师娘两口子纵身跃入炼炉才得铸成宝剑的故事。
标题“铸剑”所指并非兵器,还有一个理由,即是“王妃生下了一块铁”。如何解释这一句“荒唐言”?首先,我们应该都能接受一个前提:尽管“纯青透明”,这块由人所生下的铁毕竟还是一不祥之物。但如何引申这个不祥就将产生关键的分歧了。一种解读是:这是随后展现的整个荒诞世界的源起,一块铁生两把宝剑,两把宝剑生了三个仇人,而后……世界既以无意义始,也以无意义终,因此复仇无意义,而看客与惰性的世界依旧。另一种解读则是阶级的、反抗的解读。这块铁既是王妃生的,那么也就等于暗示了不祥源起于阶级社会里的统治集团内部。人民抗暴,虽不免也要举不祥之兵,但鲁迅想要说的可能是:徒兵不足以成事,因为那将是不断循环的“彼可取而代之”而已。必须要新民,爱与信的主体必须炼成。这也就是说,如果将“铸剑”以实体理解,那就要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若将它理解为主体的精神力量,那就指向了昂扬奋进。
总而言之,标题改为“铸剑”,应是因作者觉察到,“眉间尺”或是“复仇”之类的标题,都无法承担他所想要表达的情感与意义,因为它们所彰显的是个人主体或英雄主义,而非一种“交互主体性的”“相人偶的”情志交融。眉间尺与黑色人之间的爱、信任与团结,是对西方文学传统所常见的复仇者孤独主体的超越。因此,“眉间尺”虽然表面看似“对题”,但却严重碎义失情。
三、头换头兮
1926年末与1927年初正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经过各种磨练终成爱人同志的关键时期。几篇属于回忆性质的《朝花夕拾》散文之外,鲁迅在这时期也写了《奔月》与《铸剑》。这两篇的写作先后是有争议的。包括《两地书》的不少证据显示《奔月》的写作时间没有问题—写于1926年12月,但《铸剑》的写作时间就不确定了。鲁迅在1927年4月杂志初刊时没有标注时间,之后编《自选集》时,标记为1926年10月,比《奔月》还早两个月。然而,在鲁迅1927年4月3日的日记里又分明记录:“星期。雨。下午浴。作《眉间赤》讫。”16因此,最妥当的学术说法会是:早在1926年底鲁迅在厦门时就开始构思或动笔,到翌年四月广州居停时才完工。但这仅仅是一个考据家的安全陈述,毕竟回避了先后问题。我坚信《铸剑》必定后于《奔月》,而我的理由则是根据文本内容:作者的情感流向不可能相反。至于鲁迅为何在1932年将作品时间标志为1926年10月而非1927年4月,我认为较少可能是记忆之误—“厦门”与“广州”的时空记忆差距何其悬殊啊!如此记年,应与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有关。向来谨慎的鲁迅试图避免予人将这篇与1927年的残酷四月进行恶意联想的可乘之机。但这还只是猜想而已。
《奔月》与《铸剑》,是鲁迅挣扎于自疑自毁与自信自爱之间的关键时期的征候性写作。《奔月》写的是一个大龄末路英雄对自己能于爱的怀疑。这篇小说严格说来是鲁迅创作里的一个“败笔”,因为作者无法缰住自己长期自抑的奔腾情感,以公器泄私嗔,影射了一位文学青年高长虹—一个自以为鲁迅是他的情敌从而对鲁迅由敬转恨、从师变敌的小伙子。高曾在一首诗里,比喻自己是太阳,许广平是月亮,而鲁迅呢,则是老迈无光的黑夜。这就是为何《奔月》的主人公是射日的后羿,而在故事的结局,后羿打算“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罢”17。文章在“乌鸦炸酱面”的油滑中,也不免真心透露了后羿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不负嫦娥并给予她幸福的强烈焦虑自疑。用许广平的话,此时的鲁迅“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18。而《铸剑》则不同,它是鲁迅与许广平相互表白之后时日里的文学凝结。鲁迅对许广平表白:“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19于是,黑色人竟然对着眉间尺的嘴唇“接吻两次”—这当然是本人远远超出任何文本证据,需要加上一个大笑表情包的奇想,请读者不必考虑其效力。
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是鲁迅(当然也是许广平)生命中的一个节点。自此以后,鲁迅从死守旧社会留给他的痛苦的遗产(许广平语)走出;从“后五四”以来由于同志队伍的解体(“退隐的退隐,升官的升官”)所产生的慢性孤独感走出;从1923年兄弟绝交肺炎复发身心交疲的“宴之敖者”中走出;也从1926年年初的“三·一八惨案”的伤痛中走出。现在,他应该大致从“我已经憎恶我自己了”走出了,甚至感觉自己变成一个从冷黑到炽热红黑的“以一人任者”的志士任侠了—那个将鲁迅与其师章太炎平生心志相连的唯一形象、唯一线索。在鲁迅内心里,“眉间尺”具象言之是许广平,大而言之则是无量觉醒青年,而“仇人”则是所有的金龙金鼎一族、所有的吃人者、所有的不以暴力为耻的集团,其中当然更是尖锐地指向秋瑾与刘和珍等志士的杀害者。因此,读《铸剑》,不妨想象干将之于眉间尺,犹如刘和珍之于许广平。这样的想象让我们更能体肤理解黑色人所说的:“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他(被杀)也就是我(被杀)。”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他的《鲁迅传》里,也指出“《铸剑》的世界宣示了鲁迅凭借与许广平的爱情,走出单方面为了年轻一代的‘自我牺牲’……步入一条与他们相互联结的崭新道路。可以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意味着鲁迅的‘彷徨’已基本终结”20。与许广平的爱,既是鲁迅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铸剑》自然也不妨理解为鲁迅对这个“头换头”事件的一个文学呈现。头换头兮,自然也就是心换心兮。于是我们看到后来许广平对她与鲁迅的关系描述:“那里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21
“铸剑”这一篇名,既可表现鲁迅革命路上与子偕行的强烈情志,又同时能让这一大公与大私交缠的情志,找到一种含蓄曲致的形式,既能明情存诚同时免于情感裸奔。《铸剑》既是复仇也是志爱,那么下笔时就自然会更“诚敬”些。这或许说明了,排开《故事新编》八篇,固有文风一致之处,但还是数它最不“油滑”。
2022年6月5日于台中大度山
注释:
1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2 本文专论《铸剑》,引文均出自《鲁迅全集》第2卷,以下引用该文时不再注明页码。
3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
4 鲁迅:《论睁了眼看》,同上书,第238页。
5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3页。
6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
7 鲁迅:《夜颂》,《鲁迅全集》第5卷,第193页。
8 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01页。
9 鲁迅:《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4卷,第155页。
10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40页。
11 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77、178页。
1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
13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47页。
14 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全集》第3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
15 同上,第147页。
16 鲁迅:《日记十六(1927)四月》,《鲁迅全集》第14卷,第651页。
17 鲁迅:《奔月》,《鲁迅全集》第2卷,第368页。
18 鲁迅:《两地书·八十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220页。
19 鲁迅:《两地书·一一二》,同上书,第275页。
20 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陈青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页。
21 许广平:《为了爱》,《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 作为诗人的鲁迅:诗与思想的艺术[2022-11-01]
- 王锡荣:从手稿看夏衍怎样改编《祝福》[2022-10-31]
- “再三赐予援助” —— 也谈蔡元培与《鲁迅全集》[2022-10-27]
- 重读《风筝》:论宽恕的时间[2022-10-24]
- 《自由谈》杂文与鲁迅的“都会革命观”[2022-10-21]
- 鲁迅逝世86年,在这些书中阅读“大先生”[2022-10-20]
- 为什么说鲁迅个人史的秘密藏在这本书里[2022-10-18]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与瞿秋白[2022-10-17]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