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以人文情怀观照百年文史

孔范今,文学史家,1942年生于山东曲阜。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著有《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重构与对话》《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等,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读中国》《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等,合作主编有《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2021年3月,孔范今先生的两部新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老伴去世前嘱托他一定要完成的著作。如果不是客厅朝阳窗下的那几盆绿植渐抽新枝,如果不是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声声啼鸣,当时因腿疾数月未出门的孔范今,几乎没有注意到暮春时节已经到了。布谷鸟归来时,老人心中又惦记起远方的弟子们。4月23日,山东大学为孔老举行《人文言说》《舍下论学》新书发布暨孔范今文学史观学术研讨会,“孔门”弟子再次相聚,围坐在老师身边,就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那是他们学术之路启程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领域思潮跌宕。在每一个学术史书写者的笔下,这个大放异彩的时期总是绕不过“孔范今”这个名字,更绕不过这位文学史家的一系列具有奠基性的著述。比照之前的诸多“大部头”著述,孔老的这两部新著虽然是两本小书,却延续乃至深化了他一直以来关于现当代文学史的人文主义言说。“人文”两个字无疑是孔范今树立自己独特文学史观的方向标,而学术历程的起点却来自他对于人类生存与情感的深刻体验。
这一切,都要从孔范今成长的记忆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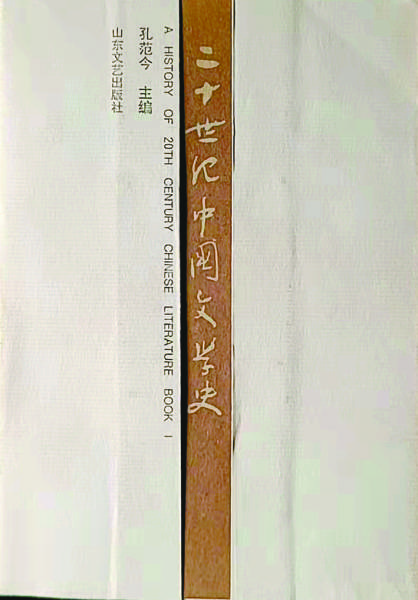


一、“一件小事”与“两个小人物”
出生于曲阜,又姓孔,记者难免好奇,孔老的身世与著名的孔氏家族是否相关。面对记者的疑问,孔范今坦言,“我是孔子74代孙,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家就挨着孔庙”。孔范今的父亲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画家,然而到他出生时,家道已日渐中落,乃至穷困无以继日。身在书香门第的孔范今本应受到良好的教育,却打小就不得不忍饥挨饿,备尝辛酸。6岁时的一次经历,不仅深深刻在了孔范今的记忆里,也刻在了他的生命里。
那年曲阜大旱,很多人家吃不上饭。对孔范今一家而言,同样是雪上加霜。无奈之下,孔父背着年幼的孔范今到临近村落讨饭求生。走过一户农家小院时,父亲试着叩了叩院门,除了小声念叨着“请您行行好吧”,这位老知识分子并不愿多说一个字。时隔多年后,当孔范今读到诗人陶渊明在类似处境下所写的那句——“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时,他对父亲当时的羞于启齿就更多了份理解,这是一个穷困书生无奈的窘迫,也是最后的矜持。
“给父亲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把我们迎进院子。院中三间北屋,一间小厨房,门里墙角砌了个小炉灶,架着铁锅。”这个画面在孔范今的记忆里是如此的清晰。“这时,铁锅的水烧开了,妇女往锅里撒着面粉。炉灶旁边站着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小女孩。”过了一会,面汤的香味飘了出来。妇女看看女儿,又看向孔父,接过他手中的碗,递回的碗里盛满了面汤。孔父连声道谢,而一边同样饥饿的女孩看着母亲的行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孔父刚准备将手中面汤喂给儿子,见此情形立时于心不安,转而要让还给女孩。妇女却赶紧拦住,对孔父说:“大哥,你不用管,我再想法子。你先顾好你家孩儿。”这次经历对孔范今而言,就如同鲁迅笔下的那“一件小事”,却是自己刻骨铭心的大事。尽管孔范今没能再遇到那位朴实善良的施予者,“这一辈子,她就像我人生中的灯塔,让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与人为善、心怀悲悯,就此被孔范今视为做人的第一准则。多年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他更加坚信,如果没有对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没有对生命的直观体验,是一定做不好人文研究的。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学费。小小年纪的孔范今懵懂却坚定地相信,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瞒着家人,每天到学堂“蹭课”,时间久了,老师们也被其感动,开了免收学费的先例。这个贫苦少年有了上学的资格,但没钱买课本。不过,孔范今自有办法,他利用每次课间休息的时间,借来同学的课本,快速阅览预习。“三年级之前我没有买过书。”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小学到高中,孔范今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数次动员他报考清华北大的理工科,孔范今其实早已下定决心要做人文研究。“我对人文研究的兴趣不光来自圣贤的教导,还有生命中那些触动我的人文精神。”
至于为何会认定报考山东大学,孔范今并不讳言,是受到20世纪50年代一战成名的“两个小人物”的巨大影响。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在《文史哲》杂志撰文,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并引发全国学界的大讨论。“‘走李希凡道路’在当时的学生中成为一面旗帜。”李希凡正是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那就干脆和他上一个母校吧。”事后想来,孔范今选择与其说是“明星效应”,不如说是当时青年哲学工作者对他产生的“思想效应”。从年轻时的穷且益坚,到晚年时的老当益壮,孔范今作为一个思想者对中国百年人文精神叩问的脚步从未停歇。
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孔范今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山东大学。20岁这年,他依然穿着一身补丁的衣服,背着母亲炒制的一小袋地瓜面,来到这座位于省城的高等学府。“我叫孔范今。”一口“曲阜普通话”,吸引来同学们的目光。时隔50年,1962级山大中文系毕业周年重聚,老同学一眼认出了已是满头白发的他,笑说:“孔范今,你这口音没变,还穿补丁衣服吗?”
被同学们记住的,不仅是孔范今特别的口音,更因为他大学期间的锋芒毕露。一次,古典文学大家萧涤非讲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时,孔范今大胆提出自己另一种理解:“这里的‘士’可能不是普通的穷人,而特指知识分子阶层。”萧先生便停下讲说,让大家来讨论,到了第二节课,他又专门给予了回应:“恐怕孔范今的意见是对的。”孔范今感慨道,“表面上萧先生是颇有傲气的人,其实内心柔软,对学生格外有容让之心”。文艺理论课的考试采取轮流口试方式,孔范今每次都自告奋勇做无人愿领的“1号选手”。“以主考官孙昌熙教授为首的三位老师对我提问,我回答之后,又会反过来向老师提出我的思考,几个轮回下来,把老师也问倒了。”最后,老师们给出“优秀”,才“撵”走这个较真的好学生。
多少个周末,孔范今和三五好友相邀畅谈,千佛山下、大明湖畔、趵突泉旁都曾留下了这群年轻人朝气蓬勃的身影。老茶馆里,一毛钱的茶叶可以喝上一整天,茶水越添越淡,大家的谈兴却越聊越浓。“别看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却个个潇洒得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谈古论今,好不快意。谈起理想,有人要当批评家,有人要做文学史家,还有人要做山水诗人……每个人心中都是大有一番作为的未来。聊到此处,孔老兴致高昂,弹一下指间夹着的长长烟灰,在烟雾悠然中,仿佛又回到了与同学们青春抒怀的半个世纪前。“我大学时还没有明确的志向,不过,心中已经笃定,以后要在学术上有所创造。”
到了毕业之际,“我们就像一捧种子,被撒到了祖国各地的最基层”。孔范今先是被分配到位于即墨海边的一处农场,不久后回家乡曲阜当了中学教师。这份工作对孔范今来说当然是不在话下,可是,大学时的理想抱负就自此束之高阁了吗?这个时期,学术界普遍陷入低谷,一些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当时任教于山东大学的牟世金,与孔范今交往深厚,亦师亦友。当孔范今听说老师一度无心学术,还干起了木匠活,就劝慰说,“那些能够在泰山之顶最先看到日出的,都是在黑夜中坚持攀登的人”。其实,这也是孔范今对自己的鼓励。他一生坚信,“人类离不开知识,生命也离不开知识”。这份信念与他的人文情怀感染也帮助了很多人。1979年,曲阜开设教师进修学校,孔范今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学校初建时连教室都没有。为了不耽误教学,他每天骑车几十里路主动上门给学员讲课。遇到学习兴趣不高的学生,孔范今总是耐心劝导。“那些坚持下来的学员拿到了专科函授学历。不久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专科学历的民办教师全部转成正式教师,他们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业余时间,孔范今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大学期间,由于条件有限,就中文系教育来说,“大家普遍阅读量少,眼界窄,感受浅。对文学史的了解也是一鳞半爪”。孔范今迫切意识到,自己还需要再“补课”。于是,他白天给学生上完课,晚上回到家点起煤油灯,从四书五经到现代文学,边读边做笔记。“这样从头仔细捋,就对中国文学史有了整体把握。”孔范今坦言,毕业后,他在那间茅草屋里度过的十年夜晚,特别充实。那段时期的枕典席文、勤学苦读,为孔范今此后能够纵横捭阖于几千年中国文学史打下了基础。
孔范今与牟世金,二人是莫逆之交。在艰难时期,他们相互鼓励,也确实成为最先看到日出的登山者。潜心研究《文心雕龙》多年的牟世金,自20世纪70年代末,接连出版论著,成为“龙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为老师高兴的同时,孔范今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蓄势待发。1985年,孔范今回到母校山大中文系工作后,很快成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更新迭代的重要推动者。
三、“复原”中国现代文学世界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迅速升温。那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是蹉跎了十年光阴后的中年学者,此刻登上学坛并成为主力。作为其中一分子,孔范今称之为“以‘自省’为群体特征的第三代”。
20世纪80年代初始,这批新锐的中青年学者,展示出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意识,过去被褒贬的作家、流派乃至理论主张得到重新解读。“对象是大家久已熟悉的,但意义却是崭新的。”孔范今回忆说,“那个时候,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就可以名噪天下,因为其中常常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我几乎是每篇必读”。彼时的孔范今还在曲阜从事教师培训工作,沉潜多年的他备受学术界这一新局面的鼓舞。“那时的自己还处在‘边缘区’,也没写什么像样的文章。”这是孔老的自谦之词。事实上,从1978年,孔范今就频频撰文,从文学理论到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展现了他的理论旨趣,比如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多篇分析人民文学家柳青作品的文章,堪称学界最早对柳青创作展开系统研究的论述。
回到高校工作的孔范今得以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多年的读书、思考,却让他陷入了更多的困惑,“当时,困扰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才能算是回复到或者说把握住了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二是为什么近百年内在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的历史发展中,会数次发生自我否定性的反复回旋的现象”。他翻阅了已有的相关文学史著述,但没能找到答案,“甚至不自量力萌生了重新建构和撰写现当代文学史的想法”。孔范今笑着说。然而,真正做起来,却发现无处着手。“首先是对对象世界的了解问题。”谈到并不遥远的现代文学(1919—1949),当时大多数人或许熟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以及左翼作家等,而对于更多曾经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作家,却鲜有了解;即便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也只是他们少数几篇作品。孔范今举例说,“像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梅娘等这些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那时连许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知为何人,更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孔范今意识到,首要工作是将眼前“残缺不全”的现代文学世界,尽可能“复原”完整。关于研究材料具有多大重要性,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道破,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然而,在学界热衷于理论与方法的80年代,孔范今选择的无疑是一项“冷门”的大工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孔范今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行,开启了他称之为“知识考古”的艰难求索。“有些过去私下看过的,要一一找出来重新审定;有些只是知道作家作品名目的,要千方百计地去搜求;而有些连名目也不知道的,就要翻检旧时的报章杂志,从中发现线索,再按图索骥到各方寻找。”孔范今带领的五六人小团队,北到东北三省,南到福建、广东,大家奔波于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有的资料还是托朋友从境外觅来。孔范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间需要收集杨绛先生的一篇作品,却苦于找不到原文。“杨先生得知后,竟将自己的手稿借出,以供抄录,让我们很是感动。”尽管辛苦,但当残缺的文学世界被逐渐“复原”,大家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竟是如此色彩丰富和天地广阔。“我们像打开了一座富矿,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1990年,孔范今等人花了五年多时间收集整理的现代文学“遗珠”《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以下简称《书系》)出版,全集四卷十四册、八百余万字,可谓鸿篇巨制。尽管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收录仍有不少遗漏,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书的问世在学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如平地一声惊雷,其中不少作家作品得以再现,极大刷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认知,学界誉其“功德无量”。比如,其中收录了曾经红极一时却湮没尘封近半个世纪的作家徐訏的四篇作品。一位同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读后,叹为佳作,却将作家名字里的“訏”念错,“可见,当时学界长期以来对研究对象的认知缺漏”。孔范今为该书系撰写的“总序”《面对历史的沉思》长达25页,开篇就鲜明地指出:“富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学术研究,命定地摆脱不了困境,又命定地必须超越困境。”“有人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回到文学本体,而我则以为尤为迫切的提倡却是回到对象本体,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包含双重的本体要求:文学审美特性和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承载与制约关系。同时,这一‘对象’含有对对象世界的整体要求,它要求呈现的是在科学意义上反映整个现代文学历史景观的全貌。”孔范今举起了“回到对象本体”研究的理论旗帜。

孔范今与青年学者交流研讨
时至新世纪之交,人们对那些此前鲜少问津的现代作家作品早已不再陌生,甚至趋之若鹜,却将一些曾经光耀史册的名家名作弃如敝屣。对此,孔范今多次发声批评这一现象,否定一味标新立异。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所谓的“大师文库”,“作为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重要一翼、创作成绩也不宜小觑的茅盾竟然落选,从前‘末座’的诗人一跃而为‘大师’,岂不令人目瞪口呆?”孔范今认为,文学史的“经典化”,其“意义”范围和内涵应是“史识”与文学鉴赏批评的科学融合。
四、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理想统一
《书系》总序开篇就已申明的两个“命定”,道出了孔范今作为一个求索不止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困厄与超越交替而朝向真理的行进。
解决了史料问题,文学史“大厦”就有了基石。孔范今便打算着手重建符合“对象本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如何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建构起这部文学史来,这其中,既有从纵的方面对过程完整性的把握和阶段分期问题,又有从横的方面对各种关系的处理与评价问题,纵横交错,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这时孔范今意识到,史学观念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构是密不可分的。
从孔范今身上可以看到一代学人的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领域持续升温。然而,令研究者们不满的,不仅是以往研究对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疏漏,更指向了导致这种疏漏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旨在倡导以整体思维与现代性意识考量现代文学变迁;1986年,金克木提出“立体研究”的概念;1988年,陈思和等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一方面,孔范今对同行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文学史时段概念产生共鸣;另一方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一指称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契合了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是中国文学转型发展的一个世纪,以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据此,孔范今独树一帜地提出,以梁启超倡导三界(诗、文、小说)“革命”作为这一文学对象的起点。“中国文学自此开始,在基质方面与传统文学形成对抗。”带着强烈的历史感,孔范今撰写多篇文章,探讨亟待重建的新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观。正如他为1992年出版的专著所拟书名——《悖论与选择》,孔范今倡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这种悖论性表现为这一时期历史的否定式发展的回旋图式,救亡与启蒙构成了二十世纪悖论性历史结构和现代转型进程的两大支点”。
从大量文献的广泛搜集,到每一个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再到总揽全局的史观驾驭,1997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意味着经过近十年的筹划、构思,孔范今理想的文学史“大厦”终于落成。在整整160页、12万字的“导论”中,他专门分析了经济、政治、文化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论证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现代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文学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通俗文学等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架构之中进行阐述。有学者认为,这部新文学史“使得许多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事相得以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意义”。
孔范今的思考在与一个时代学术思潮产生共鸣的同时,又常常以超脱的思维做历史的理性审视者。就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所论,“孔老常在别人研究停滞的地方,开始他独具特色的‘接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的延伸和超越”。看到有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由否定“革命”范式而单向度选择“启蒙”为落脚点,为否定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倡导将历史剥离出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孔范今警觉地指出,“文学价值观与文学史观的重建不是‘翻烙饼’,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文学有其独特性和独立性,但不能忽略历史的结构与动力作用对它所形成的影响。既然是‘史’,就应该有史的动势方面的揭示,不能等同于作家作品评论的堆积”。2001年,孔范今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商榷文章《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认为,否定简单化的“历史进步论”,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事实,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那么,如何确证文学自身独特的价值范畴呢?孔范今恰恰是在对文学的时代性因素考察中,确证文学既在历史之中,受到历史共时性的多种力量影响,又以文学自身的方式穿行于“历史的峡谷”,完成人文文化对历史的补偿,以及对某些永恒价值的追求。2004年,孔范今再次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以现代文学史上“祛魅”与“返魅”的张力来探讨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这一老话题,并肯定五四运动时期历史的补偿在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祛魅”向一定程度上“返魅”的蜕变,以及科学至上的启蒙观向人文文化的回归。自世纪之交,孔范今在多篇文章中论证多元现代转型中“新人文主义”的彰显。他认为,人文文化是“以生命、人性为基点所构成的生命意识、信念伦理及其以想象和通悟与世界(自然、社会)进行沟通与对话的独特能力和方式”,“文学最能体现人文文化”。
后记
从20世纪80年代的积淀,到90年代的喷涌而出,再到21世纪以来的沉淀,史料、史论、史编,孔范今以过于常人的精力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思考架构。“一直到退休前,我没有一天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也没有一天中午睡过午觉。”然而,在孔范今与几位同好们一起编写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面世后不久的2013年,他就因突发严重的眼疾无法再执笔写作。此时,他虽已退休,“依然满脑子思想迭出,却苦于无法诉诸文字”。孔范今一度因此心生苦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些昔日的老学生、老朋友前来探望,与孔范今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帮助他走出了困境。这些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提出建议,让老师在家中给他们分章宣讲,由他们负责全程录音,并整理成文字。新出版的《舍下论学》这部述学体的演讲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参加该书出版座谈会的魏建虽不是孔范今门下弟子,却感佩于以另一种“会下论学”的方式多次得到孔老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前每次和孔老师一同去外地开会,同行、同住、同游期间都是我近距离接受孔老言传身教的机会。”而当年还是一名青年学者的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桂妹,也是听了一场孔老的“会下论学”,当即决定报考孔范今的博士生。孔老对后辈学者更是极尽爱护,从给这些年轻作者亲手所作的十多篇序言中,即可见微知著。每一次收到作序的邀请,孔范今毫无前辈学者的架子,总是认真读完后给予客观评述,而且多以肯定学术价值为先。人文主义不仅是孔范今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思想基石,也是他毕生与人相处的精神基石。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007年的初春,适逢孔范今执教40年,即将退休的他与弟子们重聚曲阜。师生同游舞雩古台,那一刻,“孔门”有弟子道:“智者、仁者,吾师也。”
(感谢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教授在记者采访期间提供帮助)
- “九十年代文学”:需要重视的一个“年代”研究[2022-02-15]
- 从话语生存论到现代汉语诗学:回归新文学本位研究[2022-02-05]
- 程金城 邱田:文学的半径与跨界的可能[2022-01-27]
- 开放搞活里的人心、世界[2021-12-28]
- 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2021-12-28]
- 李汉秋:行进中的“儒林学”[2021-12-27]
- 李国华:“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严家炎全集》读札[2021-12-20]
- 田仲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2021-12-10]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