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典有识”—— 一桩事实的诸多谜团——鲁迅与陈赓
讨论如上这一题目所涉话题,对我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之前所述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发现并强调,他们之间多以神交为主。但这种“神”性的认知或许正好为自己寻找到一种理由,我探寻的主要是鲁迅与相关人物文字上的往来以及精神上的联系。这既为言说打开了空间,又为探寻话题之上的意义找到了理由。不过,将这种方式和诉求放到鲁迅与陈赓时,我却忽然觉得失效了。因为陈赓本人是一位军事人物,在文学上并没有什么专门追求,与鲁迅也没有什么文字上的往来。可是,他们却有一个传奇式的见面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只是,由此展开的分歧却构成一个个谜团,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我很想把这个只在专家之间讨论的故事讲述给更多读者。于是,就想对这些分歧、争论进行梳理,以获得对故事主体的了解。
关于鲁迅与陈赓,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曾经在上海见过面。
但不能肯定的是:
他们见面的次数是一次还是两次?
见面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
他们见面时究竟有谁陪同?
即使陈赓本人有回忆文字,即使陪同者纷纷拿出证据,却仍然不能有一个服众的定说,反而使故事裂变成为一个歧义丛生的谜团。

版画鲁迅与陈赓
一、关于起因:究竟为什么要见面
鲁迅与陈赓见面的大概轮廓是,时在1932年,肯定是下半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四川的转移途中,陈赓因为腿部受伤,不能带领部队继续前行,历经曲折到上海治疗。在上海期间,因为讲述红军在前线英勇战斗的故事而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请一位作家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以激励更多人。鲁迅被公认为是首选。经冯雪峰之手,鲁迅读到了记录这些讲述的油印材料,也觉得可以尝试来写成小说。为此,他提出要与陈赓见面,以获得更多感性材料。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神奇的见面故事。这个故事是由当事人之一、被誉为鲁迅研究“通人”的冯雪峰最早透露而被确认的。冯雪峰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写道: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约夏秋之间,陈赓同志(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陈赓将军)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方面来到上海,谈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听到的人都认为要超过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写的。大家都认为如果有一个作家把它写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鲁迅先生了。那时候朱镜我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给我送去请鲁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谈;……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任务,虽然没有立刻接受,也并没有拒绝,说道:“看罢。”几天之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的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鲁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酝酿过一个时候,因为那以后不久曾经几次谈起,他都好像准备要写似的。……但后来时过境迁,他既没有动笔,我们也没有再去催他了。不过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的时候。
这个最早的披露与故事的发生之间,其实也已经有了二十年的距离。冯雪峰的描述或许还是孤证,但相关证据很快到来。一是故事的主角陈赓的回忆。那是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陈赓接待了对此故事产生深厚兴趣的来访者张佳邻。他的回忆同冯雪峰的讲述基本一致:
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大约夏秋之间,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当时我的腿负伤了,不能再行军,党便让我到上海去医治。
到上海后,我住在一个私人开设的医院里,这个医生很同情我们,他收留了我,愿意替我医治。当时我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我曾给他们讲了一些我们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时的战斗故事。那些战斗的艰苦和剧烈,我们红军所表现的忠诚和勇敢,真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要是比起当代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里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了。我们当时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和红军所经受的这一切艰难和困苦。
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同志,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后来他们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到他家去谈谈。我们党也很希望鲁迅先生能把苏区的斗争反映出来,以他的才能、修养,一定可以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会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党同意我去见鲁迅先生。
到访者和陪同者都有一致的说法。故事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了。更不用说,除了人证之外又发现了物证。

《回忆鲁迅》 冯雪峰
就在冯雪峰《回忆鲁迅》出版之后不久,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理鲁迅遗物时,偶然发现一张从一本杂志中掉下的纸片。这张纸片是用铅笔画出的草图,还有一些地名的标注。辨认过程中,“有人想起,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谈到陈赓曾经到鲁迅家里来谈过苏区的事情,再对照图上的地名,都是安徽、河南、湖北一带地名,怀疑与此有关。于是,就拿去请陈赓将军辨认。陈赓将军看到这张纸片,当即表示,这是当年他在鲁迅家里跟鲁迅介绍红军在战争中的情况时,为了便于说明而画的一张鄂豫皖根据地示意图。”(王锡荣《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见《鲁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证物证齐全,这个传奇的故事就由一个传说定性为历史故事了。然而分歧也正由此产生。这是后话。我想先探讨一下,鲁迅为什么要见陈赓?
按照冯雪峰和陈赓的回忆,鲁迅是见到了陈赓的讲述材料后,决定接受冯雪峰等人的建议,创作一篇反映红军战斗的小说,与陈赓见面的原因,就是准备接受这一任务以获得感性材料和丰富素材。“鲁迅先生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任务”,“鲁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酝酿过一个时候”,“他都好像要写似的”,“但后来时过境迁,他既没有动笔,我们也没有再去催他了。”也就是说,鲁迅要写一篇以红军为题材的小说,是因为陈赓在上海的出现而起的想法,直接地说,是他准备接受的一个任务。学者包子衍也曾以鲁迅书信为旁证确证这一点。即鲁迅1933年3月1日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去年底,我本想在今年二月以前写出一个中篇或短篇,但现已是三月,还一字未写。”而学者陈漱渝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因为鲁迅不是见陈赓之后才有写这小说的想法,而是在会见之前就有了写的想法,他与陈赓见面,‘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创作素材。’”(王锡荣《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见《鲁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里涉及到至少三个问题: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决定写红军题材小说的?他见陈赓的目的是为了补充素材,还是决定是否动笔?鲁迅所说的打算1932年底前要写的小说一定是红军题材吗?之所以有第三个问题,是因为鲁迅在1933年3月1日同一天还给另一日本友人增田涉写了一封信,信末都是“三月一日 夜”的标记。而在这封信里,鲁迅则写道:“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以中国现状看来,无法写。”这个表达与红军题材看上去并不直接关联。但至少说明鲁迅那一时期真的在想创作小说。据冯雪峰回忆,关于红军题材,鲁迅说过“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而鲁迅最终未写出的原因,冯雪峰认为,并不是鲁迅没有想写的心思,应该是对红军了解不深入的原因。也反映出鲁迅对待创作的严谨态度。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苏区进行围剿,对文化界也相当严厉,都是造成鲁迅没有动笔的原因。就此而言,他对增田涉所说的“但以中国现状看来,无法写”,或许正是指这一创作。
可以说,鲁迅与陈赓见面的起因,一定是与创作小说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只在于,鲁迅是事先决定要写,再去读陈赓的材料,进而约陈赓见面以求丰富素材,还是读了陈赓的材料,进而接受冯雪峰等人的建议要写,再请陈赓来谈话。总之,这是一次文学家与军事家的会面,是一次创作行动的前奏,尽管这个创作最终没有完成。“不过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的时候;我记得一直以后他还问过我:‘那些东西要不要还给你?’我说:‘不要,你藏着如不方便,就烧毁了罢。’在他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有一次还谈起过,说鲁迅先生曾经把那些材料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冯雪峰《鲁迅回忆》,见《冯雪峰全集》第4卷第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相信,鲁迅是把那些材料既当作红军战斗的史料珍藏,也是当作创作素材保存。我们更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小说真的写成了,那又是一个何等热烈的文学史讨论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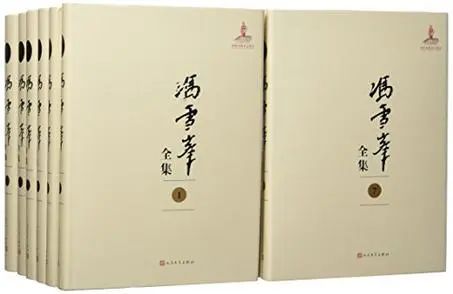
《冯雪峰全集》
二、关于见面:一张草图引发的见面次数之争
在冯雪峰和朱镜我的陪同下,陈赓与鲁迅在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见面了。这是为了一次“主题创作”而促成的会面。他们谈了一个下午,并且一起吃了晚饭,夜很深了才告别。许广平没有参与谈话,她整个下午都在忙着做晚饭。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和陈赓谈话的时间很长,我记得那天许广平同志还做了一锅牛肉。”(《与冯雪峰的三次谈话记录》,见《冯雪峰全集》第9卷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如此,冯雪峰和陈赓在20年后的回忆都坦承无法复原诸种细节。陈赓说,“可惜时间相隔太久,许多细节和谈话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追忆了。”但这种记忆的模糊并不影响事实本身的存在。分歧的起因倒是证据的进一步增加。这就是那张从鲁迅遗物中发现的小纸片。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去向陈赓求证时,得到了陈赓的确认,这张绘图正是陈赓向鲁迅描述有关红军战斗或根据地形势所画。(参见王锡荣《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见《鲁迅生平疑案》第2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情节里略有遗憾的是,没有再及时得到冯雪峰同志的确认。这为故事留下了伏笔。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差不多又过了20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楼适夷提出了新说。那是因为楼适夷在参观鲁迅纪念馆陈列时看到了这张草图,才恍然大悟,那张草图正是自己当年在鲁迅家中亲眼见过的。他也才意识到,当年他陪同的一位共产党“负责同志”原来正是赫赫有名的陈赓。1978年5月,楼适夷发表了《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提出了鲁迅与陈赓“第二次见面的事实”。也就是说,楼适夷认为,除了冯雪峰所说的见面之外,还有自己陪同的一次。于是,鲁迅与陈赓见面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成为公开的分歧点。
其实,见面是一次还是两次的分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而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变出来的。我查阅了《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可知,楼适夷早在1973年就在同黄源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此事。由此可知,两次见面是随着讨论的进展而增加出来的。1973年6月7日,楼适夷第一次谈到此事:“我在28年认识先生,31—33年一段,与先生有接触,但不多,记忆力也很坏,如32年陪陈赓同志去见鲁迅,实际是我不是雪峰,谈话约六七小时,可是具体的话,能记清的就不多了。”11月24日,黄源致信楼适夷试图帮助其考证:“兄和陈赓同志去会见鲁迅先生,是1932年7月12日,日记上:‘十二日晴,上午伊赛克君来(美国人伊赛克)。下午明之来。’确否?”这是黄源根据鲁迅日记做出的推测。此说很快就被楼适夷本人否认。他在次日即11月25日的复信中(那时京杭之间的信件居然次日即到,神速!)谈道:
所问陪陈赓同志见鲁迅事,我在《日记》上也早已查过,一直查不出来,你说的32年7月12日显然不对,我记得很清楚,天气有点凉意,陈赓同志穿的是一件灰色长袍,应该是已在九十月之间,但查《日记》,那一天也不像,一般先生对于这种与地下党有关接触,是不作记载的,所以就没法查了。年代是不会错的,是“一二·八”之后,搬居大陆新村之前,在北川公寓。楼窗上有一块玻璃被子弹打穿,先生还指着给我们看。这一点记清楚的。还有一点是模糊了,先生曾拿一张北京师大广场上讲话的照片给我们看,如果就在这次,那应当在十一月去北京以后的事了(不过看照片也许不是这一次)。我还有一个记忆,是先由朱镜我同志(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宣传部长)陪着陈赓同志到我住处,那地方是北四川路公益坊,我可能四五月间还住过那儿,但四五月《日记》上也找不出痕迹(不过后来还常去,也可能是约了在此处见面的,故在九十月之前可能为大)。现在只能记的时间是下午二三时,这天先生专在家中等待,别无外人,连许广平也没有出来接客,到吃晚饭才在一起,晚饭是在厨房边一个小房里吃的,先生打开了一瓶藏了多年的三星白兰地。不在当书房的大屋吃饭,可能是怕惊动海婴,海婴好像有点闹病。说了半天,明确的日子还是说不上来。不过你说的7月12日,是不对的。我只能说明这一点。下次见到周建老,我还可以问问。《日记》上所记人名,出版社编辑部都有查考,你疑心“明之”也许是个代号,可问问孙用,请他查一查看。
这个时候,楼适夷强调的是自己陪同过陈赓去见过鲁迅。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陪同的是什么人。他之所以确证是陈赓,“是解放后参与筹设纪念馆时,因在遗物中发现那张解放区地形草图,我是亲眼见他画的,才突然记了起来,明确日子现在无法查考,但大致时间是不会错的。”(12月9日致黄源信)。至此,我们知道,楼适夷坚信自己陪同去见鲁迅的陌生人正是陈赓。他的证据就是那张画着鄂豫晥根据地的草图,因为自己是亲见者。
到了1976年,楼适夷方知自己也许是第二次陪同者。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又放弃了否认冯雪峰陪同说。那就只能得出陈赓与鲁迅有两次见面的结论了。楼适夷4月8日致黄源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陪同时的情景,应该就是1978年公开发表文章的底本。除了见面场景的描述外,信中特别的地方,是楼适夷此时方知冯雪峰早在1952年的《回忆鲁迅》里,已经讲述过陪同陈赓与鲁迅见面的事实。他说:
鲁迅先生会见陈赓同志事,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参与过,是鲁迅纪念馆展出了一张小小的铅笔地图,一见似曾相识,才豁然记起32年秋间某日下午,曾陪同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去见鲁迅先生,这位同志原来就是陈赓。1953年出版的雪兄《回忆鲁迅》可能我当时也看过,并未想起,以后也再未重翻。早已忘掉。雪兄虽多年一起工作,日常相见,我们照例不谈往事。在纪念馆发觉后,过后也忘记跟他谈了。现在他已去世,当然来不及了。我自己曾经参与这事情,只在偶然谈往事,和家人及一二老友谈过。现在见了雪兄给包子衍同志的信,知道有那么多人关心此事,我应该把亲与其事的一节尽追忆所及提供出来,也是后死者的责任。
楼适夷做此说明,前提是黄源将冯雪峰致鲁迅研究者包子衍的一封回信内容转给了楼适夷。冯雪峰那封信回复于1974年4月26日。冯雪峰直接说道:“陈赓和鲁迅先生谈话的具体日子问题,我以为就不必再费力考证(事实上也考证不出来),而且这是没有什么重要关系的问题。1932年秋夏之间——或夏末——的一天,有过这件事,这是主要的。”他进一步指出从任何当事人的日记是不可能查证出具体时间的。同时,冯雪峰更对第二次见面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再约第二次见面事,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但我想,鲁迅先生如要再找陈赓谈话是以后随时可以约的。当天谈得很久,也似乎没有未谈完而须续谈的事情。这时鲁迅先生并未决定要写以所谈的事情为素材的小说或报告文学。”
当楼适夷知道冯雪峰早在50年代就已讲过陪同见面时,他意识到自己陪同的是另一次。也就是鲁迅与陈赓有二次见面的情形。但冯雪峰对此并不认同。这件事因此进入一个纷争点,引来不少专家的深入考证和反复讨论。我们先分析一下基本事实。冯、楼二人的声明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楼适夷认为是自己一人陪同陈赓去见鲁迅,冯雪峰的回忆则是只有朱镜我一起陪同,不存在二人同去而其中一人事后否定的情形。关键在于是否有二次见面即楼适夷陪同的可能。冯雪峰曾在1972年接受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访谈,其中写道:“那天是由朱镜我陪陈赓到一个约定的地方(冯忘记了具体地名),然后由冯带领他们二人到鲁迅家里。在场只有鲁迅、陈赓、朱镜我和我,根本没有楼适夷。(注:在1962年前后楼曾自称是他带陈赓到鲁迅家的。这次我们向冯谈起此事,冯情绪很为激动,他说楼适夷这个人太不高明了,许多事情都拉在自己身上,我那时没有发言权,随便他怎么说。)”因为是1972年,二次说还未出现,所以谁陪同成为非此即彼的状况。二人各持己见也属正常。而且我们看,楼适夷对冯雪峰对于自己的态度是有自我意识的。在与黄源的通信中,他就表达过冯对自己有误会的说法,而且还提醒黄源,跟冯雪峰通信时不要提到自己的名字。
以冯雪峰同鲁迅的往来密切程度,以冯雪峰在党内的身份,以冯雪峰早在50年代初就讲述陪同的事实,以陈赓对此事的相同回忆,楼适夷很难在此事上与冯雪峰掰手腕。更何况,在楼适夷的回忆里,冯雪峰还是介绍人,他说是冯雪峰让朱镜我陪同陈赓去约见楼适夷,再由楼适夷陪同这位自己并不知道名字的人物去见鲁迅。如今,冯雪峰断然否认了,自己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陈赓1956年的回忆里说过,“他本来想起以前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见《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鲁迅回忆录》
这时,那张用铅笔绘出的草图又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本来是陈赓与鲁迅见面的直接证据,到后来更变成了二次见面的最有力证据。
事情根源在于,在冯雪峰的表述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草图这个情节。陈赓本人则又指认草图是他为鲁迅所绘。楼适夷的回忆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当他看到陈列中的草图时,不但眼熟,而且恍然大悟到自己当年陪同的人正是陈赓。他还尽可能搜罗记忆,描述了陈赓与鲁迅的座位及描图时的情景。也就是说,绘图发生在陈赓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时。从逻辑上推理,此说是有道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陈赓都说自己只与鲁迅见过一面,而二次说还不能完全推翻的原因。
二次见面的证据还不仅仅是草图存在而冯雪峰很可能不知道这一条。因为在证明是楼适夷而不是其他人陪同这一点上,楼适夷也是见到了草图而回忆进而讲述。理论上,仍然存在是否属实的疑点。能为楼适夷提供新证据的是他早年写过的一篇散文。那是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仅仅4天之后的23日,楼适夷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为《深渊下的哭声》。文章写道:
对地下工作的意义先生从来不吝啬给与最高评价。尤其对于血火中的新中国的创造,先生的关心是无限的。每次有人从那些遥远偏僻的战地中来,先生常常请来打听真实的情形,整几个小时倾听着,不觉有丝毫的疲倦。有时要求讲的人画出详细的地图,有时叫旁边的人替他记录下来。
这里分明描述了绘画地图的情景。这是比冯雪峰的回忆更早十年以上的回忆,也比发现草图早了十几年。楼适夷的夫人黄炜,正是依据这一关键证据,发表了《关于鲁迅与陈赓有无二次会见的我见》一文。根据冯雪峰本人的说法,在他的印象中,除了陈赓,“没有其他红军战士和鲁迅见过面”。(《与冯雪峰的三次谈话记录》,见《冯雪峰全集》第9卷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表述,恰恰为楼适夷的散文作了旁证,楼适夷当年陪同去见鲁迅的,正是陈赓,只能是陈赓。
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陈赓自己说只见过鲁迅一次,难道陪同者还能驳倒主角吗?有趣的是,关于陈赓的回忆,后来者也有各种分说。一是陈赓的回忆基本上同冯雪峰的完全吻合,除了曾向鲁迅讲述苏区房屋四面开窗,从而引起鲁迅兴趣,并没有提供更多新鲜细节。原来,正如冯雪峰所说,“1956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许多人去问陈赓,陈赓又跑到我家来问我,他说连经过都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过这件事罢了。他后来是把同我谈后所记起来的去回答人的。”(冯雪峰《致包子衍》,见《冯雪峰全集》第7卷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来是劝人少去作烦琐考证的,倒又印证了一点,陈赓是依靠冯雪峰的回忆去给来访者讲述的。
事实上,当年跟随陈赓一起战斗的部下,就有人写过文章,说陈赓讲过,他与鲁迅有过两次会面。一位叫戴其萼的部下就曾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山西屯留长子间鲍店镇、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山西洪洞东之原上村,我先后两次听陈赓首长讲述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两次会见鲁迅及其被捕、脱险的情形。”“在河南方城,一次深夜值班时,作战科长陈彪、侦察科副科长程锐甲同志也听过首长讲述在上海两次会见鲁迅的情形。”(转引自王锡荣文章)1956年曾经就此采访过陈赓的张佳邻,于次年再次访问陈赓,并问到这个问题。陈赓的回答是:
冯雪峰的回忆录早已公开发表了,他坚持说是见过一次,我如果说见了两次,群众会说,‘两个老共产党员都声称如何尊重鲁迅,如何受鲁迅思想的影响,可是连见过鲁迅一次还是两次都记不清,真不象话!’我只好也说见过一次了。不过我也没作原则让步,说了鲁迅还要我再去讲一次,我也立即答应了。这表达了鲁迅对了解苏区红军英勇斗争情况的渴望和我立即答应的态度。两次会见的内容是一样的,第二次只是补充了一些事例。改说见了一次,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于鲁迅、于我们党的真诚均无影响。但不能说未见成是由于一方失约,只好说由于被捕未见成,让群众骂国民党反动派去罢。(转引自王锡荣文章)
这个回答真是有趣。但不管怎么说,以上这些都指向一个答案:鲁迅与陈赓应该有过两次见面。
三、延展说明:一个考验学术考据与推理能力的案例
其实,去除对细节的追求,我本人很赞同冯雪峰和陈赓两位的一个基本观点,讨论见面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就陈赓与鲁迅见面这个事实本身的真实存在而言,这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他们强调了人们更应该关心这个故事的核心,即鲁迅对于红军及其战斗的关心、关注,以及以此进行创作的愿望。但对楼适夷来说,究竟有没有二次见面并非一件小事。因为连冯雪峰都认为楼坚持说自己陪同过陈赓的说法,是想把这种佳话“拉到自己身上”。这已经不是见面次数的问题了。我们当然能理解冯雪峰的坚持,因为他亲历过,而且事情都是由他安排协调的。但也能理解楼适夷的另一种坚持,从起初的以为只是自己陪同,到后来的坚持二次见面说。
发生在鲁迅身上的故事总是这样纷纭不定。在我的理解里,这就是一位经典作家的魅力所在,其生平中的所有故事及其细节都值得挖掘、追究、追问,所有的故事又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创作有关。我对鲁迅与陈赓见面故事的完整了解,最主要得益于王锡荣的著作《鲁迅生平疑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中的文章《鲁迅与陈赓见过几次面》。鲁迅研究界对此有多人进行过回忆、考证、判断和评说,王锡荣的文章差不多将各家说法都归纳其中,我写作此文,也是通过他的引用,而逐渐打开阅读的视野,阅读了多位研究者的文章,努力做出自己的梳理。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其实又非常烧脑。比如说吧,尽管我们把结论引向了两次见面说,但不管是一次还是两次,鲁迅与陈赓究竟在何时见面,至今是个没有结论的话题。而且让人奇怪的是,两人见面要么一次,即使两次也肯定在时间上非常相近。但究竟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见面的呢?莫衷一是!仅从季节上说,就涉及到春夏秋冬四季。冯雪峰说是夏秋之际,最早可能是7月。学者常亚文指出,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向四川的转移是1932年10月,陈赓在此途中受伤,后艰难辗转至上海。所以他与鲁迅的见面,不用说7月,连夏秋之交都不大可能。见面的时间应该在11月。学者陈漱渝则认为,不用说夏秋不可能,连11月都不可能。因为陈赓受的是腿部重伤,恢复需要过程。既然楼适夷说自己陪同的这位同志并“无负伤的样子,步履甚健”,而鲁迅于11月11月即已北上北京,到月底才返沪,所以11月见面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到底是何时呢?学者朱正、倪墨炎也介入考证当中,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鲁迅陈赓见面应在1933年3月,即次年的初春时节。陈赓于3月24日被捕,见面只能在3月初或中旬了。
但疑点却越来越多。因为11月初才负重伤到上海,又能独立行走,鲁迅又于11日北上至月底,鲁陈见面的时间就应该在12月以后了。可我们知道,鲁迅从北京回到上海是11月的最后一天,那时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正在鲁迅家中避居,一直到12月20日左右才离开,鲁迅此时会即刻答应见陈赓吗?且没有一位当事者提到瞿秋白夫妇的出现。如果说在冬季,可仅从服装上说,与楼适夷记忆中陈赓身着单层灰色长袍这一印象也不相符。
1933年春季倒似乎确实更能让种种矛盾元素缓冲。但我们想象一下吧,说成1933年3月见面,一是与冯雪峰说的夏秋之际相去太远,冯也完全没有“自选”一个时间用以回忆的必要。陈赓、楼适夷的回忆也都确认是1932年。二是,如果是次年3月见面的话,那是经历了新年,又经历了春节这两大节日的,难道当事者连如此跨年的节点都记不得吗?即使记不住准确时间,年前年后还不至于都忘记吧。
王锡荣在自己的文章结尾也提出了好几点疑惑,这些疑惑让人感觉,这个话题仍然处于开放状态。比如,楼适夷没有参与第一次见面,又提出“两次见面”说,是不是出于不推翻冯雪峰陪同见面为前提?还有,楼适夷说自己通过观察认为,鲁迅和陈赓见面并没有陌生和询问的环节,可见两人已经有过见面,但问题是朱镜我为什么不自己再次陪同,而要把如此秘密的任务交给第一次并未参与的楼呢?再者,出于安全考虑和要求,陈赓大白天出行需要有人护送,到深夜分手,却为何倒是一个人独自离开呢?从倪墨炎的文章《鲁迅何时会见陈赓和会见几次》(见《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考据中,不但有一次说和两次说之争,还有两次见面里楼适夷陪同在前,以及一次见面只有楼适夷陪同之说。
这真是个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配角大都登场,史料专家纷纷出动,却仍然得不出非一即二这么个问题,春夏秋冬占满都确定不了见面时间。形成这种局面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鲁迅本人的日记、书信对此没有任何记录,无法查证,失去了大家都可信任的依据。另一关键人物朱镜我如果出场,那又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些,因为毕竟他是冯雪峰和楼适夷都提到参与其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朱镜我在1941年皖南事变战斗中牺牲。故事很重要的一条线索过早中断,令人唏嘘。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文学史、革命史上的佳话,故事的主题从不因细节的枝生、歧义的纷呈而改变。其中那些众说纷纭,无论互相之间有多少矛盾,一家之言是否可以周圆,一个共同点却都指向故事的真实存在,以及追求其中真相的强烈诉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个考验学术考证和推理能力的案例,值得后来者继续去追寻。
阎晶明“读典有识”专栏:
- 金波:难忘那声音里的暖——怀念葛翠琳大姐[2023-01-04]
- 刘进才:亦严亦慈的恩师刘增杰先生[2023-01-04]
- 罗雪村:画忆柳鸣九先生[2023-01-04]
- 慕津锋:我记忆中的济生先生[2022-12-31]
- 简平:两封书信,一般遗憾[2022-12-29]
- “互联网鲁迅”:现代经典的后现代命运及其启示[2022-12-28]
- 拉摩斯公寓,灯光长明[2022-12-26]
- 李国文:“弥勒肚里尽神思”[2022-12-26]
 更多
更多
星辰与家园: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与守护
科幻文学不仅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世界、与自我对话的途径。愿同一星空下的我们,可以乘科幻长风,去探索星辰大海,去洞察自我的秘密。













